《地圖集》-建立在虛幻與真實間的香港城市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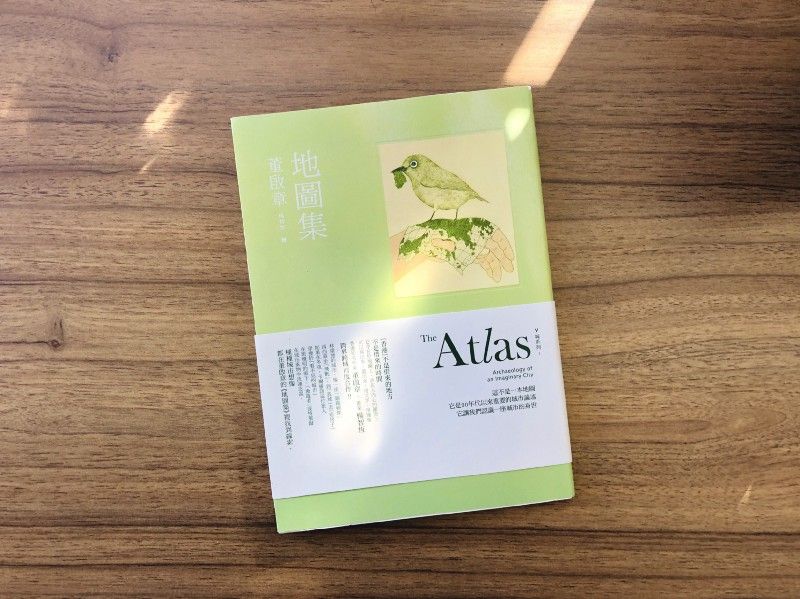
在我還是小學生時,那時的房間掛起了一幅世界地圖。那個子不高,還未有肚腩的我對於地圖這回事還是有一點摸不著頭腦的熱衷。每朝起身,就站在床上,仔細打量地圖的每一角落。城市的位置﹑海岸線的形狀﹑虛無的國界,彷彿世界盡收眼中 — 美好的前智能電話年代。
要紀錄一個曾經存在於世上的地方,最宏觀而簡潔的保存方法莫過於一紙地圖。房裡的世界地圖客觀記錄了地球不同的地勢特徵。可是,我對於地圖上的符號有不少疑問,例如為甚麼大部份國界都用實線劃上,卻有部份如加沙走廊和克什米爾的界線用了虛線來劃上?而地圖上的界線﹑地方的名字會否在某個時間上轉變?當然這些問題對於一個成人來說不分幼稚,但這些孩童問題背後隱含著的,是我對「地圖」這東東的熱誠。只是在不久的後來,這種「熱誠」很快便被其他青春期所面對的成長樂與怒所淹沒,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董啟章的《地圖集》是一本小說,並非嚴謹的地理書籍。但裡面的內容的確提供了更多角度思考和認識到底「地圖」是一個怎樣理解的概念。書裡不少篇幅亦對我小時提出的疑問作出了回響。董啟章給予成年的我一個機會去重新連繫房間還掛著世界地圖﹑仍在小學上課那個從前的我。
「界限不但不是實存世界的摹描,它本身就是實存世界的虛構性塑造方式。在界限的製定和實行中,世界在抄襲地圖。而在地圖上訂立界限的先決條件,是掌控虛構的權力。」
地圖反映了人類之間對權力的追求和競爭。它形象化了肉眼不能看見的力量。對於何時使用實線與虛線畫上國界,就是取決於那個地方勢力掌握了多少「虛構的權力」。一張地圖不只藏著客觀的地理科學資料,還記載著人類的權力﹑慾望與利益的紛爭(我們通常叫這做政治)。看過《地圖集》後,若要回答我小時候提出的問題,我想我會對這位小朋友說:「也許實線與虛線的分別沒有想像上那麼大呢,反正它們也是人類文明在權力鬥爭中一種虛構出來的副產品吧。」
「地圖作為空間的呈現這一既定觀念產生了根本性的震撼。在一切地圖製作的背後,也假設了一個凝定的時間,在這永恆現在式的假設上,描畫出地表在某一時刻下的狀況和面貌。」
雖然在我的小學的那個時代,世界似乎剛好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年代,至少在香港及附近地圖如是吧。地圖印刷就算過了幾年,上面畫上的國界和當時世界的情況還真的沒有甚變改。或者也正因這樣,我在小時候一直以為地球已經進入了一個大致和平的小時代,基本上國家的界限已不會有重大變動,爺爺口中回憶起的世界大戰不會再次發生了。當然,這一切一切也都是一位小朋友微小而美麗的暇想,當這小朋友一天一天地長大,他所身處的世界跟他想像中的世界就像兩張沒對準的描圖紙一樣,一點一點地錯開了(借村上伯伯的名句)。
只是我的小學年代剛好處於較安穩的時代空檔,在宏觀上較難看到世界的變遷,而世界還是每分每秒地變化。地圖的符號原則上也應不停改變,只是印在紙上的地圖不是 Google Map。所以地圖成為了世界那一刻的烙印,而我們便會因時間的流逝與地圖漸行漸遠。
「我們處於時間流動的世界,坐上了「時間的火車」一直往前駛去。而牆上的地圖,只有望著牆上的地圖,則停留了在列車背後的某個時間之軌跡上。」
值得一提的是,地圖除了讓某個時空的地世靜止在一張紙上,以及作為航行和科學之工具外,比較古老但精美的地圖也蘊含著不少人文資訊。董啟章便在書中提出了「圖例之墮落」這概念。從前製作地圖時還未有精準的地圖繪畫和格式,地圖製作者卻會加入大量繪畫精美的圖例,例如有特色的「要塞」﹑「驛站」插畫圖案供人「參考」。這些不夠精準的古地圖卻正因地圖格式還未制度化和科學化,令讀者從豐富的資訊線索能夠得知不少關於地理以外的其他訊息,也像童話故事一般保留了更多空間讓地圖的讀者去幻想和創作。有見及此,可能小時的我更需要的是一幅五顏六色的古地圖多於一幅已被現代主義僵化了的地圖呢。
關於本書,董啟章的《地圖集》書寫在1997年,一個美好年代的終結。董啟章嘗試以文字繪出一幅香港的「地圖」,參考了《看不見的城市》的風格,以模仿一位考古學家的學術文體,寫出這本風格特別的小說,立體地紀錄一個仍在變化的香港:
「『城市』作為一巨大的人為物,及其中的物的總體呈現, 又必然通過人的生存其中才能確立及延續其存在及其價值意義。」
《地圖集》每個短篇章節內容疑幻似真。每篇文章總會引用大量學術名稱以及歷史文獻,讓地理行外人看得目瞪口呆,可是每篇文章後面所訴說的典故和傳說總是顯得滑稽好笑。事實上,這就是董啟章寫這本小書時感到趣味的地方。他利用「偽考古學」方以大量的史實資料作基礎,以想像力延伸虛構出更豐富的「偽史料」。書裡面的內容亦真亦假,但透過文字所表達出的城市氣息,卻與現實一致。董啟章在《地圖集》裡確切地表達出香港這地方的精神氣質,令嘗試去分辨書中內容真假這個舉動已無甚價值了。
「為甚麼沒有一幅摹描聲音﹑質感和氣味的地圖?為什麼我們無法捕捉事物最為易逝的表相,並因而無從參透事物的本質?而我只能記憶起另一幅地圖。那是兒時跟同學們炫示自己家居環境的地圖,上面有以稚嫩的筆跡擬畫的植滿柏樹的林蔭大道和寬敞疏落的低矮房子……」
這是書上「柏樹街」章節的節錄。聽說董啟章兒時正是在柏樹街長大。傳統的地圖紀錄不了易逝的東西以及一個人內心的情感,反而是董啟章小朋友的一幅手作地圖,裝載了一個小朋友內心的幻想和情感,紀錄了一個人的本質。也紀錄了當年的香港情懷。而地圖這東西對於我來說,也喚起了我小學的回憶,以及我曾存在過的一個年代 - 那個介乎董建華與梁振英之間,曾有片刻寧靜,也令人差點就相信了一國兩制的曾氏香港。
世界上無法反映在一張地圖上的事物還實在太多,至少地圖上那個旁邊寫上「香港」的一小點,能引發董啟章寫了一本似真若假的地理和考古小說,豐富了香港的城市論述,也令我們深深知道:
「香港不是借來的地方,不是借來的時間。它存在於地圖上,活在人內心的圖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