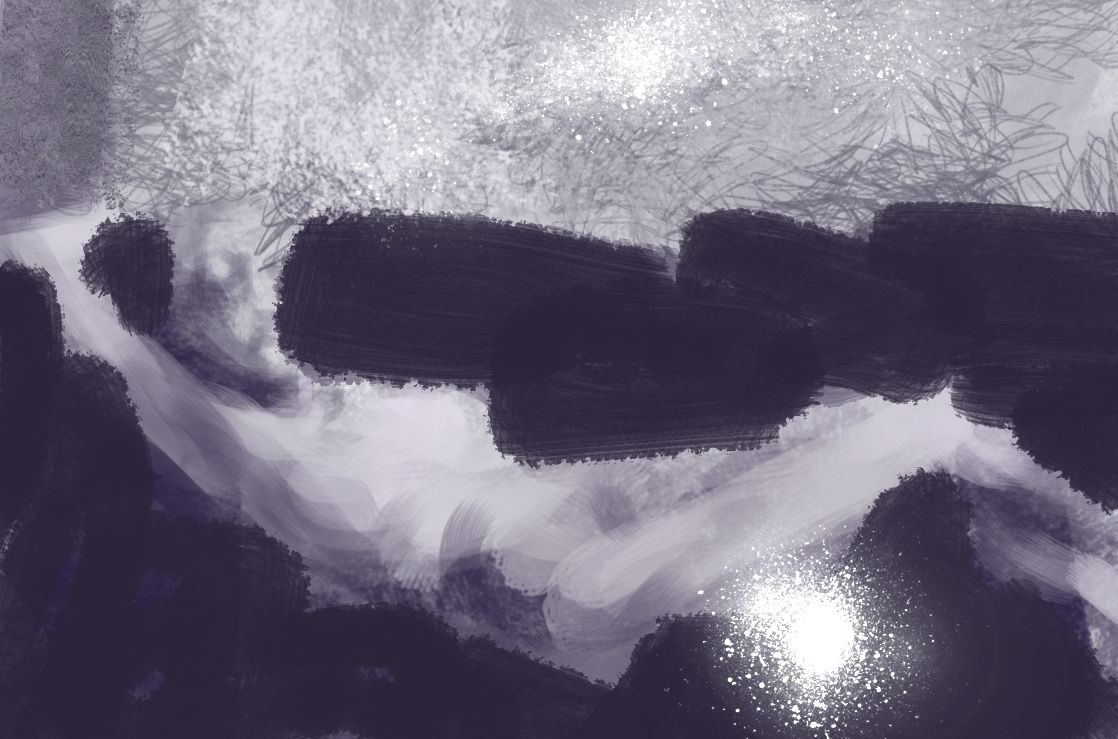【讓愛發電】以母系社会为透镜,翻看父权话语 (四)|听一听,停一停
第四章
拉康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在现在的一些动物测验中也常常测验动物照镜子,看看它能不能知道镜像就是它自己。我们知道,小婴儿出生后还好几个月不能动,也不会转头,还要好几个月才能坐起来,控制一点自己的身体。这段时间称为幼态持续。这时候抱着孩子照镜子,母亲跟ta说:“宝宝,看这是谁?”,在语言的引导下,孩子认出了自己。这时候ta才知道自己是整全的,而不是自己感受到的那样碎裂。ta会欣喜不已,知道自己将能长大,不会永远处于碎裂之中。这时,孩子对身体的想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从碎裂、到整全。或许是因为人与镜像身体的间隙,人才会说“我有一个身体”,而不说自己就是身体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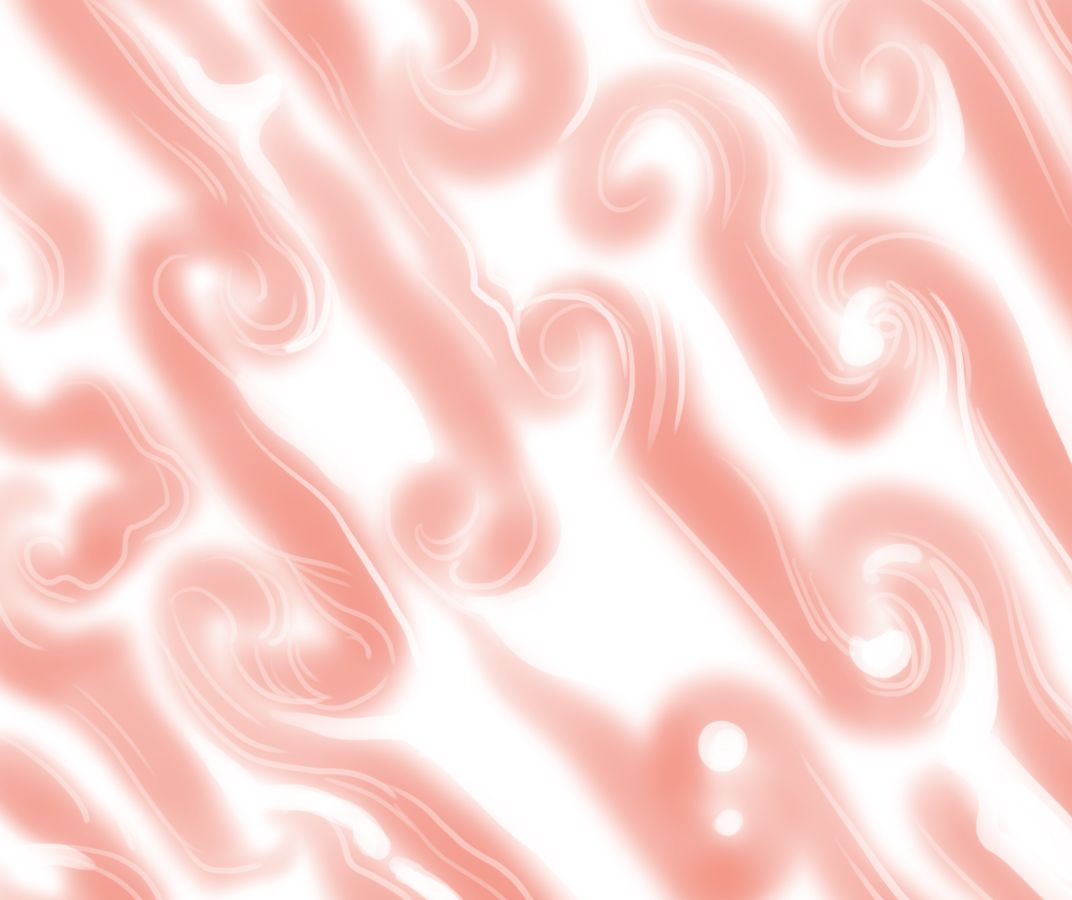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镜子并不多见,人也不常能见自己的倒影,而且婴儿的视角受限,也很难看到一个整全的人的形象,那ta靠什么来想象自己的身体呢?是母亲这一原初大他者的目光的注视使孩子能知晓自己的存在、学会分辨人类的样貌,是他人的存在使孩子知道自己将如ta所见的他人一样。目光对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母亲在哺乳时候不看孩子,孩子的创伤将会是巨大的,甚至会拒绝吃奶。母亲给孩子的抚摸也非常重要,抚摸与心理皮肤的长成有重要关系,抚摸的刺激,能使ta知晓自己的身体。以及,对孩子的期盼,会在孩子出生前为ta命名,编织故事,言说ta的存在。并在抚养的过程中与ta说话,让ta进入语言的世界。拉康说,人是言在。如果在言说上否认、忽视孩子的存在,对ta的创伤也将是巨大的。
可以说,来自原初大他者的最基础的这些爱的目光、抚摸、言说,构成了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想象、理解,而这些并不在意识层面。不幸的是,就如我们前文所说的父权母亲的状况,使得孩子能得到的爱总伴随着创伤、扭结……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如果头胎生下了女儿,原本用于给儿子编织的未来就统统作废,当她承受着“生不出儿子”的压力时,她对女儿的目光也难免带着失望与痛苦。有许多母亲,需要独力持家,丧偶式育儿使她没有余力去照顾孩子;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或者由于艰难与焦虑,她要紧紧地控制孩子,希望ta“赢在起跑线上”,或者总以“别人家的孩子”来讥讽、比较……到最后,也是对大部分人来说,ta的无意识与一生的行动常是在不断回应自己婴幼儿时与原初大他者的关系,回应这些扭结与创伤。
是言说使人存在。也因此,语言暴力并不比肢体暴力更好,它带来的伤害、痛感,并不比肉体的伤更轻。在了解到的家暴中,孩子承受的语言暴力的折磨与东亚式教育(学校与家庭),常常将孩子逼上绝路—— 一边霸凌更弱的同学或者虐待动物,一边重度抑郁、时常想自杀。肉体暴力则常常伴随着失语,并没有语言来帮助暴力现场的所有人描述所遭遇的。因此,即便有些男孩长大后终于能揍回自己爸,但暴力的表达已经作为一种表达的语法写在他的身上,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觉知和训练,在亲密关系中也难免如此对待妻子和孩子,他已经是失语的了。(在这个层面上,人是非常需要语言帮助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困境的。是描述,而不是被教导。)
在这种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的无意识身体是什么样的呢?ta的身体又承受了什么?承担了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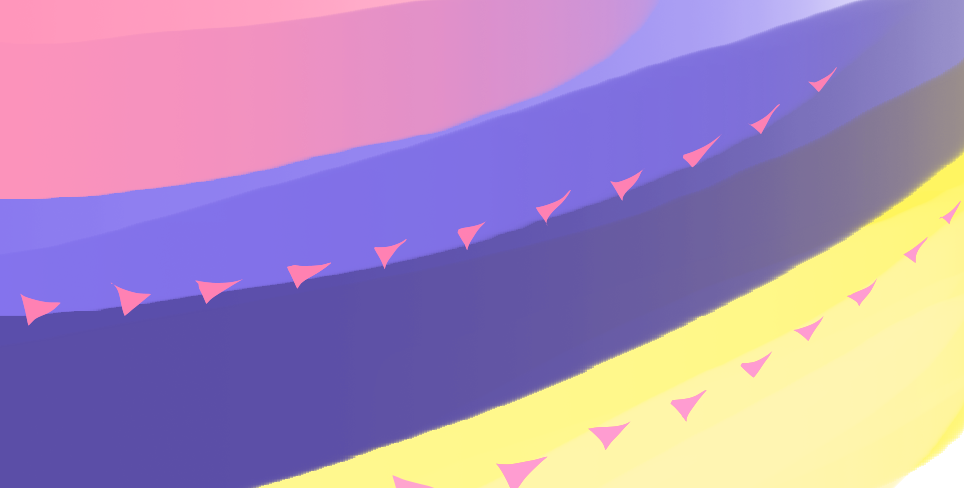
我在泰国北部山区的中国村(有许多是国民党军队的遗部,以无国籍的身份生活在泰北),看到了熟悉的景象:平房的院子铺满水泥,一棵草也没有,高高的铁门里,小孩子扒着铁门往外张望,看着我们开着摩托呼啸而过。在三公里外,另一个泰国人的山村,我们开过了陡峭的山坡,来到田边,泰国农民夫妇正在插秧,他们的孩子在旁边的吊脚草屋上玩耍,父母就在目光可及的地方。过了一会儿,爸爸休息,就跟孩子在田里玩。没有看手机,而是一起玩。
在国内,不分贫富,有许多人在孩提时代都有留守家中,或隔代抚养的经历。现在新世代的孩子,父母也常用手机镜头替代了自己的目光,不知道这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这样长大的人,在婴幼儿时期常陷入无回应(目光、触摸、语言)的境地,也就更不易获得安全感,更常要承受无意识身体不完整的感受,常常有“心好像缺了一块”的感觉。常年被独自锁在家中等待父母下班回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许会说“我从不打骂你”,但孤独是对人类伤害是最大的,人类是天生的社群动物,在没有他者的情况下难以存活。这长期的无回应的绝望之境,再加上是女孩的话,无意识的身体碎裂、穿孔也就更为严重,常有解体、恐惧的感受,严重的话便爆发精神分裂。
还有一种情况。想象的、认同的身体形象与真实的身体的差距突然被意识到的时候,可能撕裂无意识的身体,使得精神病发作或者内在冲突不断。而这样的情况多见于女性。

就如前文所说,phallus中心的话语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大写的女人),且只有这个大写的女人才在符号界有一席之地。而女性大多从小就被灌输与大写女人的形象认同,比如芭比娃娃一类的玩具,奇迹暖暖那样的公主换装游戏。这些东西无时无刻不告诉女孩,她将成为一个女人,而女人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完整的“新娘”才是女人,否则什么都不是,或者“只有成为这样的女人,才有价值”。这些话语被书写了在无意识之中,反而成了她的主人。但真实的女性却从来不是长这个样子的,真实的女性一定是各有特点的。自然的身体会有成长、时间、阳光的痕迹,会有各自的基因表达,绝不会是一个光滑的模子。因此,这种冲突也就成了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自己的腿粗细、胸小、为有肚腩,皮肤不光滑白皙(实为正常人类女性的体态)而烦恼到无法接受自己、自我厌弃,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自我形象的制作上,难以接受不完美的、复杂的形象。甚至,只要不符合完美的标准,就视乎为缺陷、瑕疵,甚至肮脏。

真实与想象层面的认同的撕裂,让大多女性身处于自我折磨、自我攻击的地狱之中,不自觉间也会如此对待其她女人。
“完美的女人才有价值”,除了导致女性日常的自我厌弃,也会引发严重的精神危机。有一些严重的被害妄想,迫害者常拥有大写女人的模样者出现。拉康的博士论文个案叫艾梅,艾梅就声称女演员Z夫人在迫害她,Z夫人当然不认识她。实际上,Z夫人正是艾梅的理想自我的形象,可她无法达到。艾梅对自己的厌弃,再加上精神病的发作,这厌弃的施行者就成了Z夫人。
可见,一个舒适、平常的女性形象的被言说、认可,对女性而言实在是太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画“我的奇迹暖暖”的缘故,实在是希望女性们能早日从这种完美标准的迫害中解放出来。

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遮蔽也同样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女性生殖器几乎不存在与phallus中心的话语之中。不像摩梭,女性生殖器有狮子山脚的神圣山洞,在象征界中处于高位,父权社会里的话语对女性生殖器系统,是切割的、是遮蔽的。
许多女孩都经历过这样的困惑:我下面到底有几个洞?也不止一个女性跟我表示过,对自己下面的长相是很困惑、很模糊的。在美国早期的女性运动中,其中有一样就是女性们人手一面镜子,用来看自己的生殖器的模样。
在大部分的语言中,阴门、阴道、子宫,并不被视为一体,并没有词语将这三者融为一体来表述。就如很多女性跟我表示过,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身体里是有子宫的。理论上当然知道有,但真正想这件事的时候,还是感到十分困惑。有些人可能会说:怀了孩子就知道咋回事了。但现实并非如此,人对自己身体在想象层的理解是离不开语言的编织的,而非“眼见为实”。有个案在生过孩子后,依然不知道自己的生殖器的构造,在一次偶然中知道了自己的下面居然有三个洞之后,精神解体导致自杀,幸而自杀未成。
正如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对女性来说很重要一样,接受自己无意识身体的形状,无论是碎裂的还是穿孔的,也是无意识层面工作的重要一环。可以试试绘画无意识身体,与自己对话,感受自己身体的声音,放松下来,理解风吹过自己时发出的呼啸声。

(关于绘画无意识身体的小故事请看: new gods中篇 )
回到拉康的镜子理论,回到前文被害妄想症的个案艾梅这里。我们说,艾梅的理想形象Z夫人与艾梅形成了镜像关系,拥有大写女人外貌的Z夫人被制作进艾梅的妄想之中,处在了艾梅的镜像的位置,也就遭到了艾梅的攻击(艾梅刺伤了Z夫人)。对镜像者的攻击性,在拉康理论中,叫侵凌性(aggressive)。
《白雪公主》中的皇后很好地解释了镜像与侵凌性的关系。在还没有白雪公主的时候,皇后每天都因自己的镜像中的美而喜悦,就如婴儿也因自己的镜像完整而欣喜一样。而白雪公主,这另一个完美女人的诞生,则占据了魔镜的目光,魔镜倒影出来的不再是皇后自己,而是白雪公主。皇后失去了位置,没有目光再看向她了,她十分愤恨。这个魔镜就如大他者的目光,最初,人在原初大他者的目光中才能映照出自己。皇后就如大他者欲望的对象,她也要让自己是大他者所期待的样子(“最美的女人”)。当另一个最美的女人的诞生占据了大他者的目光,皇后就丧失了映照自己的机会,成为了空无(nothing),失去目光的痛苦令她愤怒嫉妒。这样的恨便是侵凌性,常出现在妈妈有了新宝宝,但孩子还没长大到可以独立建构自我的存在的时候。这些感受,会因为年龄小,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最终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如果是传统摩梭,则不需要担心,因为孩子的原初大他者有好几个,而不是单一的、唯一的一个)。在长大后,大他者也已经从原初的母亲转移到了别处。phallus这个主能指是常见的大他者之一,人也就从欲望原初大他者母亲的欲望,转变成欲望着phallus的欲望,期待着phallus的目光,也会因为失去被这目光捕获的可能而愤怒、嫉妒、充满攻击性。
对男人来说,phallus欲望他像个“男人”,以完美男人(有钱有权有女人有权威)的标准要求他,才是个男人,在phallus的目光下,他“不能说不行”,由此他也才能证明自己是拥有phallus的、有价值的人。如果他总处在丧失phallus目光的位置上,或者有了这种危机,他就要将他的恨以暴力发泄出来。在淘宝大数据里,防身武器的购买者男性占大多数。家暴中,男性大多数是施暴者,但社会中的暴力事件,谋杀案,大部分受害者也是男性。再加上男性成长历程经常遭遇暴力,反而他们的生存更加紧张。
既然男性不像女性没有阳具,是先天被阉割的,那么在想象的身体层面,男性的身体会比女性的更完整吗?我认为未必,或许身体边界是更清晰的,但身体阳具之外的部分实则更被弱化,更被当工具了。
对女人来说,phallus期待她是被男人欲望的女人,要乖乖处在客体的位置上,甚至要约束、教育、谴责其她不符合标准的女人,才是个“好女人”。她需要花费无数心力去维持完美女人的形象,但支撑这形象的话语资源又过于单薄无力,因而也更加焦虑、脆弱。这个话语系统制造了追求“完美”的女人,也制造了她的悲剧遭遇,除了被其她女人置入镜像位置而遭排挤,还要承担祸害男人做不好事的罪名,红颜必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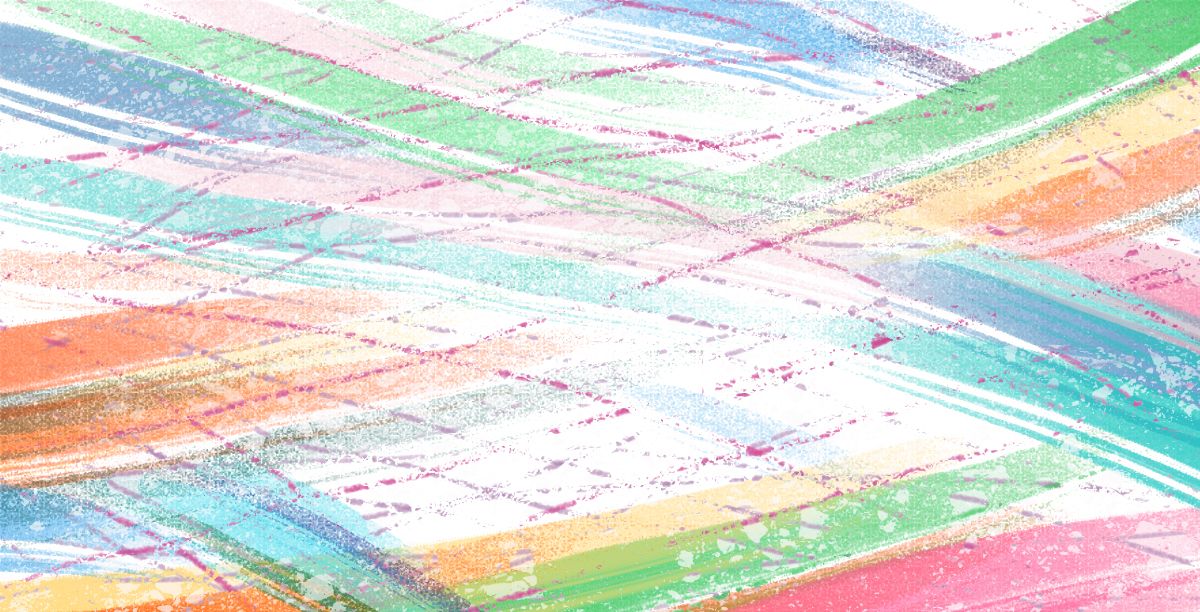
大部分女人在父权话语中是没有位置的,也不可能与完美女人的形象贴合。或许女人拥有的是一个看起来手脚健全,但不过是被自己忽视的、厌弃的一个肉身。但这不意味着身体便是消失的了,一旦心里有重担,身体常以疼痛(心痛、头痛)来表达。在女孩成为女性之后,不同的疼痛常伴随女性一生,红糖红枣也就早早的在女性间盛行了。可是,养身并不代表着对自己在承受者什么、对自己的遭遇的理解,女性的遭遇在男权话语下是真空一片,完全失语的,尽管姐妹间多有交流,但自己“不对劲”的感受却总似乎不合法的。有许多老年妇女的抑郁症,沉默得足以击倒任何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年轻一些的人里,脉轮说、灵修、冥想一类方法在女性中更盛行的原因,女性需要在这失语的世界,寻找新的话语去重新连接自己与自己身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