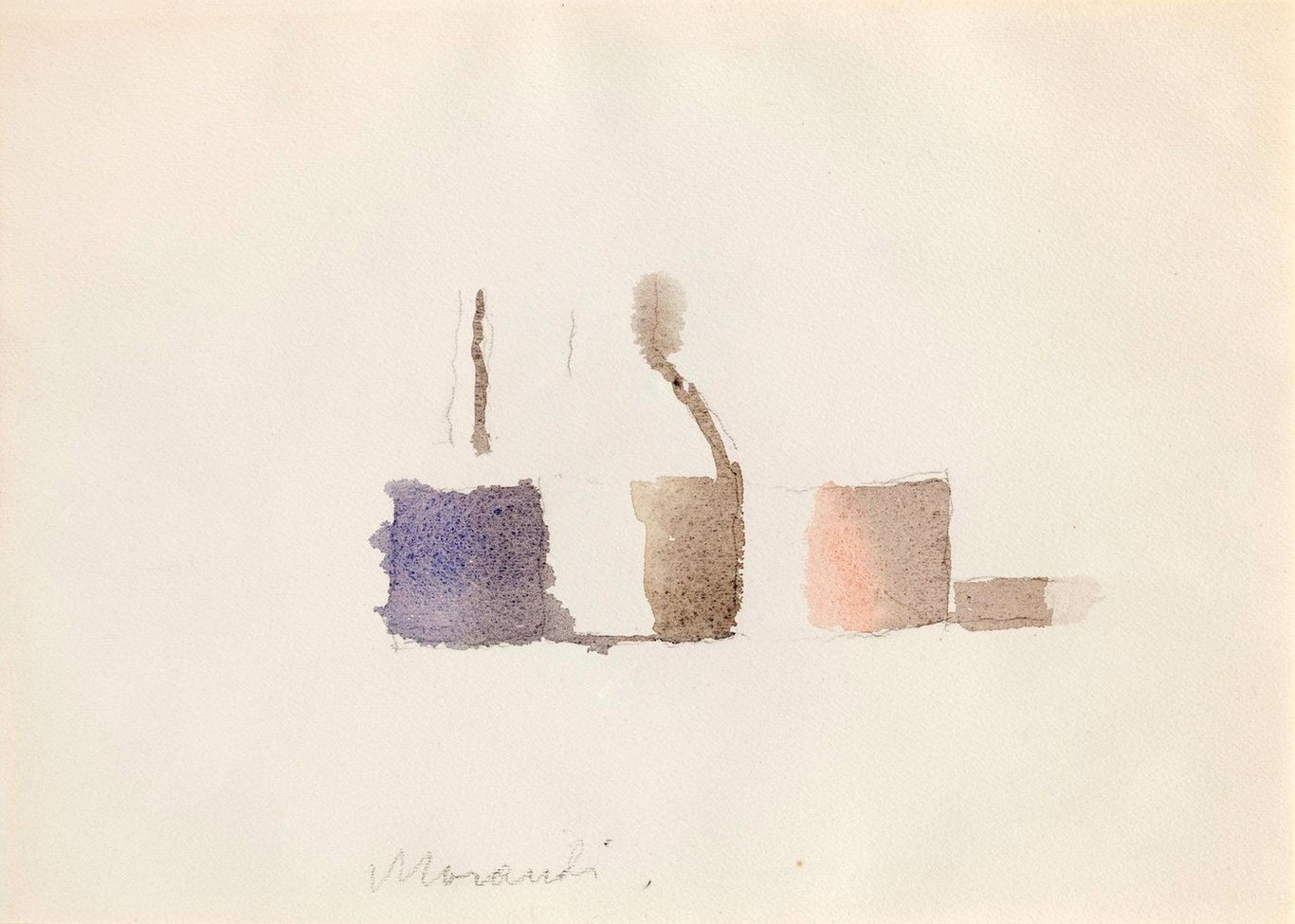《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作者/许立志
失语,我只能想到这个词来形容我现在的状态。我还能写出论文,心理学的,舞蹈学的,人类学的,但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却逃离了语言。
人类学课的期末演讲要求是利用三个这学期读过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来解读一个新闻,我用郑州富士康工人,马克思,埃里克·沃尔夫和《末日松茸》,论证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将其链条上的每个参与者变得更为野蛮而非更为文明。演讲的内容并没有多么精彩和缜密,它只是让我愈发意识到,每一秒,我都无法抑制地在乎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有时,我希望自己麻木以减轻痛苦,有时,我又唾弃这种麻木。我多么憎恶那些面对尖叫和泪水毫无表情,甚至嬉笑的脸,可我却无数次在我的家人,同学,朋友,以及我自己的面孔中看到。
当我在教室里谈论资本对人的异化时,有多少我的同龄人正在流水线上,有多少我的同龄人正在从大楼上往下跳,有多少我的同龄人正在被迫卖淫,有多少我的同龄人正在被警察找上门。而仅仅是害怕遭受政治迫害而无法回国又算是什么真正的苦难和牺牲。
在中国发生的街头抗议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但同时让我看到了更多的荒诞——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荒诞,还有各式各样民主人士的荒诞。哥伦比亚大学抗议中的打(错)人事件让我意识到,政治立场还是其次的问题,重新思考暴力之合法性与不合法性更加要紧,不然就落入消灭一切不同立场的窠臼。
有人用“文学必须一刻不停地干涉政治,直到政治不再一刻不停地干涉文学”来评价自杀逝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的诗歌。我想他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他不停地用诗歌反抗政治,不肯麻木地入世,最终燃尽了自己。当一切诗歌都无法抚慰被政治蹂躏的良知和尊严,我又要如何保持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我没法不绝望,可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我只觉得一盏盏灯在心中熄灭了。我安慰自己:痛苦至少好过麻木。
我的一位朋友喜欢电影《颐和园》,每年都要看一次。她说她出国之前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电影里李缇要在德国自杀,而一直活在中国的余虹却没有自杀。我能体会,身前事否决身后身的痛苦。
李缇仰头从天台倒下去的一幕,镜头从她的脸移到天上,此时刚好有一群白鸽飞过。李缇是最纯洁的,最理想主义的,或许正因此她才会在六四的运动中因一种真挚的热忱与激情爱上周伟。这场失败的政治运动也成为了她痛苦的来源,就像她和周伟都说不清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怎样发生的,她也不清楚那场运动究竟在她的生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直到她、周伟和若古三人若干年后在德国参与了一场街头游行,恰似当年她与周伟、余虹在天安门广场。回忆被唤起,而一种理想主义彻底失败的绝望降临在她的命运中。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能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到光明吗?
我写不出漂亮东西来,也不记得在四通桥之前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夏天绿色的山峦在记忆中是辽阔的,只是与我如今的生活已经相隔不止一个秋天。那些蜡烛,那些口号,那些白纸,那些被撕去的海报,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们;那些警察,那些水马,那些防护服,那些殴打谩骂,那些核酸测试,那些前后矛盾的喉舌;那些与我相距千里却无法远离的,纠缠着希望与绝望的,宣称只关乎正义的所有,成为了2022年我记忆的全部。
和所有人微不足道的人一样,我被时代的浪潮席卷并淹没。我希望我还有些笃定的力量,而非精疲力竭地倒在无尽的怀疑与叹息中。只好用《一代宗师》来勉励自己:有一口气,点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