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炳哲《精神政治學》書評:當自由不再是權利而是權力時
「今天,權力越來越呈現出一種自由的狀態。他以順從、友好的形式擯棄自己的否定性,將自己裝扮成自由。」
「他不允許我們沈默,相反地,要我們不斷地去傾訴、分享和參與,去交流我們的想法、需求、願望和愛好,講訴我們的生活……如今,自由的危機不在於我們面臨一種否定或著壓制自由的權力技術,而在於這種權力技術對自由敲骨吸髓般的利用。」— — 韓炳哲《精神政治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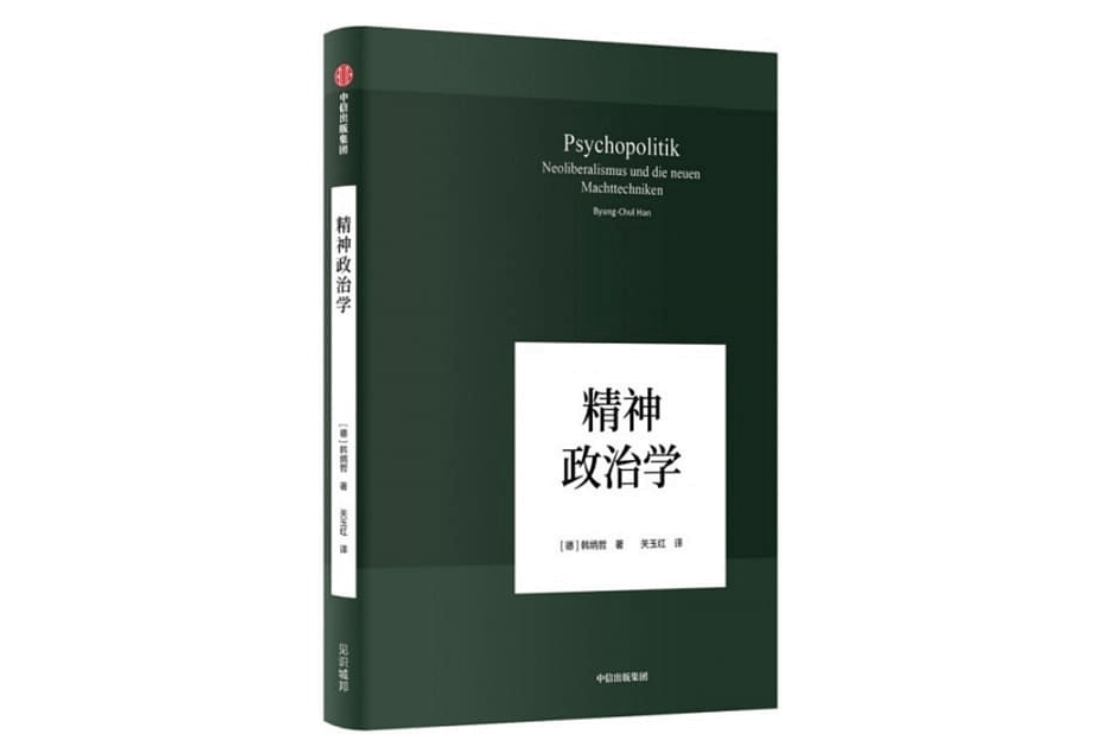
這個「權力技術」是什麼呢?正是現下很夯的大數據分析。而自由的危機,在韓炳哲的《精神政治學》中,除了是隱私的危機,更包含數據應用對人造成的控制與制約效應,進而導致對人的精神改造。
不過同時,讓我真正對此書有所感觸的,是在於我發現作者對於大數據思維的批判,可以放到對民主這一政治制度的省思。因為如果作者批判大數據主義將所有人複雜的資訊(不論外在、內在)都單單只是視為數字的作法,那麼以投票多數為政策、政務官產生依據的民主制度,同樣也有可能面臨相同將政治理念價值窄化成數字的威脅。進而讓政客不再重視自己的理念、政策是否對國家、人民是正確或良善的,而是只關注、在意自己的言語、行為是否為精彩的表演、演說。就算話語、理念、政策空洞、不具實際可能性,只要能對群眾產生很高的吸引力,那也無所謂。
大數據的思維,利用網際網路和現代日益發達的信息技術,搜羅人們在生活中所遺留下的各種資訊。你在網路上點了什麼網頁、看了什麼、看了多久、買了什麼、寫了什麼、偏好什麼類型的網站、訊息等等,通通透過數字記錄下來。換算成頻率、次數、持續時間、金額等形式成為圖表,供各種商業公司、政府單位研究、分析,形成市場調查、政策方向。甚至,也就是很多人最擔心的,大數據、量化的技術成為監控的獨裁工具,就像喬治.歐威爾的偉大著作《一九八四》或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所寫的那樣。
在現代,「信息已經成為一種商品」(出自Richard A.Spinello),被諸如Google、Facebook、Amazon等企業私下搜集並買賣。這種思維第一個可能影響到的就是人們的隱私權。因為對多數人來說,他們無法具體知道自己所遺留下的資訊會被如何處置、分析,拿去做何利用。更不確定自己到底有多少資訊被記錄,或被記錄地多詳細。
2019年初的時候,國外媒體The Verge報導全球最大的網際網路線上零售商 — — 亞馬遜公司 — — 設計了一個AI系統來記錄、追蹤員工工作的效率。例如以倉庫的揀貨工人來說,計算、監控的就是他們挑選和包裝物品的速度,一開始要求員工每小時包裝80個商品,後來增至120件。若不符合所規定的標準數值,AI將直接送出員工的解僱單。為了達到這項艱鉅的標準,許多員工承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他們不敢在工作時上廁所,因為廁所離倉庫有些距離,來回一趟所浪費的時間會降低他的工作效率,因此為了解決生理的新陳代謝,不得不在工作倉庫中用瓶子解決排泄。同樣地,配送員也有相同的困擾,排泄問題也是在車上直接解決來增加工作效率。儘管這些嚴苛的工作要求曾遭到員工、輿論的抗議與批評,不過亞馬遜公司的發言人否認AI解僱一事,說員工的上司可以推翻系統的決定,或者,公司內部員工有相應的申訴管道幫助員工辯解,拿回自己的工作。認為:「我們的系統是為了輔助員工改進效率,並提供額外的培訓,絕不會解僱員工。」
姑且不論究竟亞馬遜公司內部是否存在真正公正、客觀且體恤員工的解僱與申訴制度吧~我們把焦點集中在發言人的前兩句話上:「我們的系統是為了輔助員工改進效率,並提供額外的培訓。」
精神改造:量化自我
韓炳哲在《精神政治學》中提出了一個「量化自我」的觀點,在這裡面他提到,雖然數字和文字都是一種符號,但兩者對人有很大的差別及影響。「數字不能敘述自我。算數不是講述。我之為我,要感謝的是敘事。是敘事,而不是計數,引發了自我找尋,或說自我認知……(換言之)自我書寫致力於追求真相。把自己記錄下來,有助於形成個人倫理。」但「量化自我的座右銘是『通過數字認識自己』……數據主義……淪為自我控制的技術。收集來的數據也會被公布出去,並且被用於互相交換。因此自我定位越來越像自我監控。今天的主體,是自己剝削自己的企業主,是自己監控自己的監視器。」換言之,當人被數據監控、督促自己習慣的時候,「數字化的生命就失去了生命力。」
亞馬遜公司「輔助員工」的「培訓」完全就是量化自我的寫照。他使工作中的人漸漸變得像規格化的機器,或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找不到自己工作、甚至生活、賺錢的意義。
「我們生活的時代雖然充滿了越來越多的信息,但它卻給我們越來越少的意義。」一位法國哲學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又譯:讓.鮑德里亞)曾這麼說道。因為當任何東西被以數字進行量化時,就慢慢變成只是單純的資訊和數據,雖然可能促成有用的商業判斷,可是通常就不會關注形成這些數據在每個個體自身的內涵。
要適應這樣的現代社會,一開始人們通常只想到兩種方式。一是就像前面所說的,量化自己,符合那些工作要求。另外一個,則是想辦法建構、表現、追求自己生命的「意義」,通常是被俗稱的「獨特性」。然而,兩者都潛藏著隱憂。因為這個時代諷刺的地方正是在於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們就像規格化的機器一樣工作,一方面又強調、歌頌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獨特性,只有這個方式才能突破自己被數據化的危險,被視為平均值的威脅。在這狀況下,人被迫地必須想辦法表達自己,想辦法壓榨自己的靈魂,擠出一點點能讓自己散發看起來和別人「不一樣」的靈光。我們開始討厭沒有特色的自己,覺得平凡是一種罪惡,會讓人覺得自己很頹廢。只要沒有在做「有意義」的事情時,就感到倦怠、自卑和沒有價值。這些觀點在《精神政治學》並沒有太多描述,不過在作者的另一本書《倦怠社會》倒有不少剖析:「(在這時代)所謂的正常,就是要求每個人採取自動自發的行為:每個人都有義務,去成為他自己……憂鬱症患者並不全然地過著地獄般的苦難生活,他只是拼命努力地成為自己,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憂鬱、失落、價值感低弱遂成了現代人經常產生的心理問題。因為我們被要求成為「積極」、「獨立」、「充滿熱忱、夢想」的個體,而被困在逞強又膽怯害怕、孤單與各種渴望交織的心理絕境。
政治上的量化:「平等」
類似的投射也出現在政治的領域。我們希望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實際上我們又很清楚,真正的平等並不存在,或著,在現代社會,根本很難成立,只能依靠各自的努力想辦法成為「平等」的個體。
民主制度同大數據一樣,他使全體人民在參與政治上有同等的地位、權利,但同時,由於選票的關係,他也讓政治多了一項可以操控的技術。事實上,很多政客已經發現到,只要在適當的時刻說出一些剛好呼應多數群眾心聲的口號,自己便能當選,獲得執政權。因此他們不再在乎政治、人權、價值理念的訴求,轉而「努力製造積極情感並對其加以利用;循循善誘而不是處處禁止;不與主體對立,而是迎合對方」。
許多政治人物的「造神運動」不正是由此而來的嗎?那些狂熱的粉絲儘管打著愛國情操、經濟發展等等願景,但只要稍微詢問一下,就會發現他們對於當前情勢並沒有完整的認知,對於所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知道他具體的政策,只是一再強調對方的魅力,單方面認定其對待選民的態度十分真誠,道德清廉、良好等等,且無法接受與他認知相反的資訊。
如果大眾不認真關注政治事務,那麼民主自由會被政客的口號利用。而人人參與政治的民主真諦則灰飛煙滅。
這點正是民主最恐怖的隱憂,你以為你和大家擁有各種自由,實際上你不知道的是,這種自由仍然相當脆弱,很容易就被政黨利用。
精神的政治學
所謂的政治不單只出現在選舉、造勢、政見發表、政策事務執行等這些明顯的場合中。因為還有一種政治,是直接作用在精神上的政治。就韓炳哲的觀點來看,他們潛伏在數字的紀錄、教育裡;作用在暗示你要不停表達的自由裡;並被整合在社會的結構裡,跟著你的一生偷偷不停塑造你的個性。
我沒有打算要說韓炳哲對量化、民主的批評完全是對的,是正確的。因為書中並沒有具體討論量化或者民主或者資本主義對人類的重要性,而我們都知道不論是量化,還是所謂的民主,都有太多的優點讓我們無法輕易捨去他們。也因此他們或許成為了往後時代必然的趨勢(對,我講「或許」,因為我們同樣要很小心「時代趨勢」這個詞,他同樣可能是一種刻意製造、引導的陰謀和權力手段)。
當我們注意到某些地方正因為沒有民主自由而產生眾多人權壓迫時,韓炳哲提醒了我們注意另外一種更隱微的政治精神壓迫同樣也在侵蝕我們的生活。強迫我們表態、公開自身的資訊,或著符合各種「標準」的要求等等不過是冰山一角。因為誠如書中在討論到法國哲學家 — — 米歇爾.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的想法:「十七世紀以來,權力不再是如同上帝的君主所行使的處決權力,而是規訓權力……它的功能不是去殺戮,而是去實現對生命的完全利用……讓步於一種對肉體的認真管理和對生命的精打細算……」
當自由不再是權利而是權力手段時,我們應該如何識破並矯正?換言之,要如何提防自由等人權議題成為被媒體、政客利用的手段?這將是以後所有人都得面對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