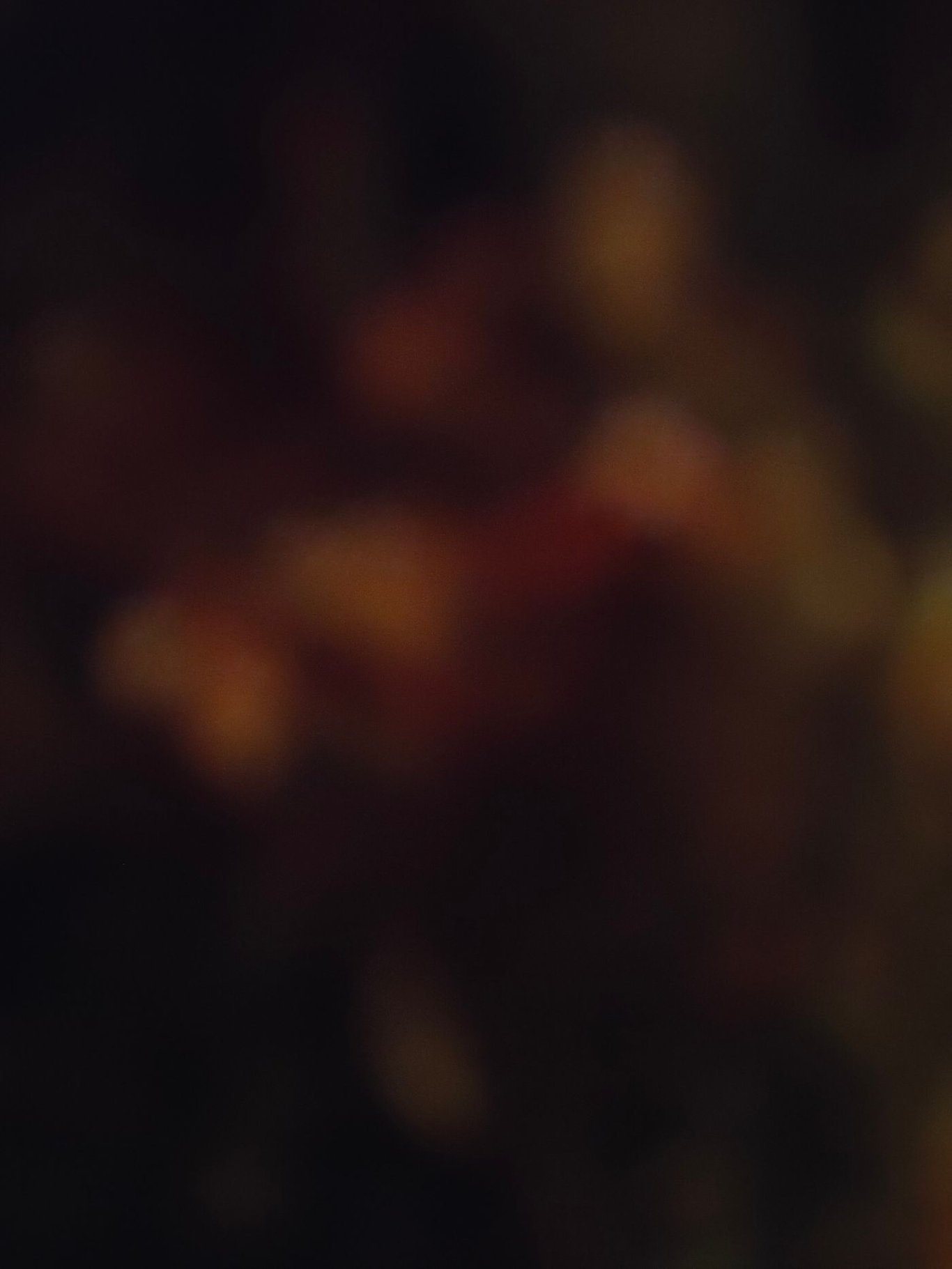朗西埃《政治艺术的悖论》阅读笔记
P59-61, 《Les Paradoxes de l'art politique》de《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Jacques Rancière, Éditeur : La Fabrique
朗西埃所举的例子:
莫里哀:
莫里哀的戏剧是宣扬道德,区分善恶,揭露虚伪的。这样具有教化意义的作品,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对于世界的特定解读,试图让观众进入到作者所营造的道德情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加于观众的。
在莫里哀的戏剧中,观众处于低位,被灌输意识形态,进入作者所营造的道德情境。
这样的戏剧被启蒙运动的人所使用,用于教化民众,变革人心。扩大了作品的政治属性和功能。
席勒:
席勒消解了将美德和邪恶简单区分的固有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艺术教化民众和启迪人心的崇高属性。席勒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平等的感性经验。
席勒不同于莫里哀那种强加于观众的教育属性(也不同于强加于人的法律或机制的形式),而是让观众平等地参与同一种感性经验。
不同于莫里哀对于上流社会虚伪邪恶的揭露,具有很强的阶级属性。席勒在《强盗》中体现的道德于善恶是可以沟通上流阶层和普通阶层的,一种普遍通用的感性经验。(体会这种感性经验是每个人共有的能力)
席勒消解了在旧的王权和宗教的教化下对于道德的划分。
卢梭:
但是,卢梭进一步消解了剧院或艺术的崇高属性。他认为,不应该建立剧院以用于教化和启蒙民众。我同意卢梭的观点,戏剧只是娱乐,绝不能改变人民的感情和社会风尚,只能顺应且增强他们。
他认为,不应该假设剧院里的表演与观众的思想以及他们离开剧院后的行为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剧院或艺术作品并不能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原因:
1.戏剧或艺术作品只是一种拟真:
剧场本身就是一种拟真,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例如观众们观看一出关于革命的戏剧,他们看到的是剧作家与演员在舞台上模拟出的革命场景,观众们既没有看到真实的革命场景,也没有真正参与到革命中。
所以,作为观众,观看是被动行为,观看本身是拒绝认知和行动的。
剧院只是一种把意识形态灌输给观众的场所,是一个中介,拒绝了真实且直接的感情和伦理,并不能让观众产生对于事物直接的感知和行动。
所以,观众在观看时对于受难者怜悯,对于暴政的愤慨,在我看来都是虚伪的。
悖论:没有观众的剧场并不存在,但是只要有观看,那就意味着拒绝了真实的认知与行动,也意味着不平等的产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适用于当代艺术中?没有观众的作品是不成立的吗?或者没有观众的作品(不能引起观众思考和讨论的作品)就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吗?
2.每个观众都有自己对于感情和道德的认知:
作者不应该预设自己要给观众带来什么,因为每个观众都有自己对于感情和道德的认知,这样的感情来源于每个人的心中,并不是来源于戏剧中。如果作者一味的想要启发或者教化观众,最后也只能达到让观众面对舞台上的表演流几滴眼泪,让观众在观看时产生短暂的激动,暂时让观众进入作者所预设的仁爱和美德的情境。
因为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道德认知,所以作者对于道德的呼唤和对于虚伪地抨击并不能教化观众。我见过无数次,在电影院中,前一刻对着银幕上的善良美好而感动落泪的观众,再下一刻电影散场时就在影厅出口为了争先恐后地离开而开始推搡和谩骂。
3.剧院没有资格承担教化与启迪民众的功能:
我同意卢梭的观点,剧院作为娱乐场所就足够了。邪恶的行为有法律约束,政治的辩论议会是更好的场所。剧院不应该把自己的功能看得过于崇高,剧作者也没有资格承担教化启蒙人民的职责。
另一方面,作者编写的剧目也只是对于真实生活场景的模拟。为了吸引观众,他们也要迎合观众,这样的行为并不那么崇高。所以作者想要让观众把模拟出的场景带入真实的生活,期许观众也认同作者所认为的崇高与美德,甚至作为自己生活的指导与启发,这成为了一个伪命题,因为对于那些考虑吸引观众的创作者来说,崇高其实早已不存在了,只剩下了媚俗。是创作者自愿为奴,将观众的意愿作为主体,指导或影响自己的创作,艺术的崇高在此过程中被创作者自己消解掉了,如果此时创作者仍高举着艺术或道德的崇高当作幌子,想要教化民众,这就显得尤其的虚伪且可笑。
对于平等:
朗西埃认为,在传统的剧院中,作者与观众是不平等的。例如在莫里哀的戏剧里,观众是被动的接收者。主动和被动同时也意味着有高与低的差别。观众在剧院中是处于低位,被灌输思想的角色。卢梭认为应该消除剧院中这种主动和被动的差别。所以,卢梭在《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反对在日内瓦建立剧院。
莫里哀或者启蒙者们想用教化的方式,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我不同意。
我认同朗西埃提出的,平等应该作为前提被事先声明,不能期待在过程中逐步实现平等。
但我不同意朗西埃所认为的,可以通过观看方式的改变,把观看变为一种积极的行动,让观众主动地认知,实现观众与作者的平等。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观看本身就是被动的,是背离于真实的行动与认知的。所以,只要观看这个行为产生了,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也就产生了,这一定不能达到平等。
我认为,如果将平等作为前提,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创作者只对艺术负责,不考虑观众,甚至拒绝被观看。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将观众解放,消除创作者与观众之间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这样才可以达到平等。
对于当代艺术:
现在的当代艺术,有很多作品试图让观众变得主动,让观众活跃起来,与观众更多的互动。甚至试图将艺术展览变成政治活动的场所。看似是实现了一种新的创作者与观众的关系,但是观众(观看)仍然存在,本质没变,仍然不平等。艺术家仍然手持着艺术的崇高试图证实自己的观点或向观众灌输些什么。看似有了更多的互动和参与,但还是把观众当作了接收者。我认为这是虚伪的。
也就是说,即使在当代艺术中,将观众也变成了戏剧的演出者,允许他们在舞台上参与互动,但是戏剧仍然存在,观看也就仍然存在。
一种反推的逻辑:我要创作一个作品让观众也可以参与到作品中平等地互动。那么我的作品就需要观众。那么我就需要吸引观众。那么我就要考虑观众需要什么,观众会被什么吸引。我就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创作我的作品。那么观众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主体。那么创作者就会失去一些自身的表达。就会变得媚俗。
这样的作品从本质上就有虚伪和媚俗的倾向。艺术家把作品变成了某种政治活动的场所,(以为具有了某种崇高的属性,将观众引入其中,试图实现平等地互动),那也只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拟象。实质上也是和古代戏剧一样的烂俗说教的景观。
这样的作品也只是试图营造某种拟真的景观,具有某种表演性质,是模仿真实生活的剧场。和传统剧场一样,创作者还是带着引导观众的意图,甚至参与或影响观众的生活。创作者仍是作为一个召集者的角色出现,试图以某种方式引领与规训观众。
我认为,艺术家不应试图将艺术带入生活,因为即使这样的话,艺术也只能是生活的拟象。
我认为,艺术可以是崇高的。但是这种崇高只对艺术家自己生效就够了。这种崇高是私人的。艺术家只对自己和艺术负责,并不需要对观众,政治,社会生活负责。艺术家不应该把自己所认为的崇高也当作对观众的期许,更不应该觉得自己手持崇高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影响或引导观众甚至社会生活。
在我看来,艺术家认为自己的作品需要观众,这就已经错了,而且有媚俗的嫌疑,创作应该只对自己负责。
这个问题不在于艺术家提前预设想要将观众引导到哪里。而是在于艺术家煞有介事地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观众些什么。即便是想要引发观众自主,自由地,不同的思考,不给观众设限。但是带着引发观众思考,让观众参与作品,这样的动机,就已经错了。因为在这之中,艺术家仍是一个召集者的形象,和观众是不平等的,观众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被教化和规训了。
当代艺术更虚伪的是,在以前,作者写作,启蒙者们使用这些剧目,试图赋予这些戏剧政治属性来教化民众。但是当代艺术家既想当作者又想当启蒙者。将自己的作品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
按照鲍德里亚:作者创作模拟真实生活的剧目 剧场上演对于真实生活拟真的剧目 观众将这样的拟真场景带入自己的真实生活 生活变成了一种脱离了真实的拟真生活 之后的作者将这种拟真的生活再次拟真成为下一个剧目让观众观看再带到自己的本就失去了真实的拟真生活中(多重的拟真,将宫斗剧情节带入生活也是一种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