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絮语 | The Atlantic

作者 / Te-Ping Chen
原标题 / Shanghai Murmur
一刻钟阅读
楼上的男的死掉了,其他的住户过了好一阵子才发觉,这几天里,带点甜的腐臭味越来越浓,居民们都尽量绕开他家那片走道,来往的时候手掌捂紧鼻子。最后终于有人通知了物业,物业的人叫来了他无业的表哥把锁砸开,又付了他一百块把尸体走楼梯抬下三楼。
那屋子旁边的住户吵来吵去,觉得死人触了霉头,要求减租。晓蕾立在一旁听着,直到物业的人抬高嗓门打断他们。她为过世的男人感到惋惜,记得他是个中年人,眼神疲惫、深陷,在当地邮局工作,还是个老烟枪。她估摸,如果她有一天夜里被人掐住脖子或者捅了一刀,那样抬出去的就是自己了。
那天晚上,她带回来一朵白色菊花,摸黑上楼,打算把花放在那人屋子外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爬楼梯时,看到那扇门敞开着。屋子里没有窗户,比走道里还要乌漆黑。她没等眼睛适应黑暗,就把花投进这虚空,不敢大口喘气,下楼梯跑了回去。
如果能经常多来来店里,永洁会立马发现有花儿不见了,南方女人的那种眼尖,她是有的。但大多数日子她都在外头,除开花店,她还要打理舅舅的家禽屠宰场,占掉了她多数辰光。自从她上班后,晓蕾大概可以顺走一整束花逃之夭夭:高腰、褶叶的金银花茎,一簇簇棒子似的丁香花。不过她觉得这些花单独摆放更加好看,所以那些偷来的花一支支地在她的窗台上摆了一排,每枝都装在单独的苏打水瓶里:一朵蓬头玫瑰,一朵电蓝色的百子莲。
她告别父母已有三年,三年前,她跟他们讲自己在上海南边的一家芯片工厂寻到了工作。很多小姑娘已经离开了村子,没人指望她们再去种地。其实呢,她不知道啥是芯片,不过在电台里听过一段讲芯片的节目。当时她十六岁,带着少年的残酷骄傲,跟她的爸妈讲述芯片的事情,“是家日本公司”,语气里带着权威,“产品出口到欧洲”,他们被说动了,让她去了。一直到上火车之前,她都在期待他们能拆穿她的谎言。他们没有。登上开往南方的列车,去往离家十四个小时的城市的那一刻,她感到失望,感到意外地悲伤。那里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只有一份虚假的工作在等待。
第二天早上,她来到花店的时候脾气很差。她没梳头,柜台后镜子里的倒影让她眉头紧皱。经年累月,上公交时她抢着在别人前头,人行道上张着胳膊肘给自己开道,眼睛半眯着要识破各路坑蒙拐骗之徒,嘴唇抿着,随时准备好回嘴自卫。这一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她还不到二十岁,却感觉到岁月已经潜伏在他的皮肤之下,仿佛上海往她的脸颊上移植了块钢板。她已经失去了小姑娘面孔上那种灵动的五官,目光的疲惫有迹可循。她随便遇到谁,都能讲出有个同乡在上海大展拳脚的故事。奇怪的是,她居然一次也没有亲眼遇见过故事里的那些人。
但不过,她还是觉得花店对自己有用场。她第一次打工,是在玻璃瓶厂里,感觉自己成了机器人,手指头僵硬,头脑麻木,心胸锁闭。以前村子里那些野猫,对靠近的人都会报以一通唾弃的嘶叫,晓蕾现在觉得自己理解了。同她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有时聚在院落,她碰到了会连忙转身撤退,像是突然记起忘了啥事没干,哪怕其中几个姑娘曾跟她打过友好的招呼。不奇怪,她告诉自己,野生动物都是怕人的。
手头上的活她已经做了半年,给玫瑰剥刺,售卖一捧捧花束,也算是个有点文化的工作了。她也因而寻到了管窥上海的渠道,观察这个她差点不抱希望有朝一日能看见的城市,胸中结郁也就有所释怀。她把花卖给格子间里的秘书,卖给从乌亮颜色的轿车下来的悲恸的寡妇,卖给向不同地址寄去同款花束的男人,想必那头既有发妻又有情人。她学会了压平自己说话的音调,在话语里注入一种打听似的柔软,这种腔调不像任何地方的方言,当然离上海话也相去甚远,而顾客们似乎很欢喜。
她最近心情起落很大,低潮的时候像平静的涡旋,涨潮起来能冲刷整片海滩。或许有天她能开爿自己的店。高楼大厦正在城市各个角落立起来,霓虹灯管的招牌在抛光的不锈钢板上缠绕生长。男人西装革履女人脚蹬高跟,磕磕咔咔击地有声。她可以把放走廊里那种陶盆绿植卖给城里人,打理起自己的一番生意。或者在电梯里遇到个贵人,找到个坐班的工作。这些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中午饭点到了,那个死掉的男的终于被她抛在了脑后,兴致也高昂了起来。外面,日头经由人行道的白条子反射,整条街几乎发着光。她早上卖掉了六束雏菊,又接了一门丧事的花圈订单。永洁知道了会很满意的。
今天礼拜三,所以她整天都存下最好的花,留给她最中意的那个回头客。先沽清的是那些行将枯黄的,花瓣头已经低了,即将松脱花萼,再过两日就七零八落不像样了。
五点钟了,他还没来,一种幽幽的伤感开始爬上手心脚背。她一边招待顾客,一边在窗外搜寻他的踪迹。外面的光线变成黄昏时那种苍灰颜色,蹑手蹑脚地沿着人行道上离去,甚至连对面那块喧嚣着成人保健用品的花花绿绿的红牌子也沉寂了下来。隔壁店里,电脑插线和管道配件乱七八糟地摆着。再往外是一家小餐馆肮脏邋遢的地板,上面是“鸭血粉丝”那菜店同名的招牌。还是不见他影子,她瞪着剩下的花儿,克制着把它们从桶里倒到人行道上去的冲动。
后天是礼拜五,也就是说,她凌晨三点就得起床,这样才能抢在其他人前头,赢过这帮从城里四面八方赶来对面批发市场的花贩,然后花几个小时把一捆捆沉甸甸、湿漉漉的花儿拖回店里。这也意味着,她今晚不得不在离店之前,洗掉那些因为装着腐烂的花茎而被弄臭的水桶。紫罗兰泡在水里太久,茎已经发软发糊,散发垂死的气味,她觉得简直比邻居的尸体还要难闻。
后来,突然间,那个人出现在商店外头,对她微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他钻进门的动作,好像是在躲避什么恶劣的天气,尽管天并未下雨。他向后背绕了绕肩膀,放松了下。她注意到他剪了头发,穿的是和往常一样的白领子衬衫;她能想象他家的衣橱里列着一整排这样标致的衬衫。
看到他,她觉得店里的东西又有了意义,脸也解冻了。"七朵红玫瑰,加三朵百合花?"她问道,不太能与他对视,而他点了点头。"那用好看的纸头包起来,谢谢。" 她感到胸中有一股暖流涌动。他身上轻松自在的气场就像给她端上了一碗热汤,尽管他其实不太多说话——实际上,她现在已经记住了他要什么,几乎没有必要再交谈。她走向装着花的水桶,这一刻花儿仿佛炸药桶的引线,她一边感谢它们振作的面貌,一边把头发塞到耳后。
轻轻地,她把花一朵朵从桶里提上来,一点点地在她左手中搓开,形成一片玫瑰头的星座,接着仔细地把百合花点缀在其间。完成后,她滑出一张粉红色的纸皮和一张紫色的纸巾,把它们温柔地放在工作台上。心里面,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于是动作愈加缓慢,单纯为了延长这幸福时光。
然后,她用一只不太稳的手,举起菜刀,落在花茎上。她把它们置于微颤的纸张之中心,把纸的边缘合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在花束的中间系上一条橙色丝带。花没有扎得特别好,不如她希望的那样利落齐整,她只希望他看不出来。永洁则总能把花束捆得很完美,顶部非常匀称,要是在花上面铺一块布,甚至可能把下面当做平坦的底座。
当她转身看他时,他正背对着站在柜台前,但仿佛感觉到了她的动作似的,他转过身来,心怀期待地看着她。各种念头一点一滴地涌现出来,她想同他分享,但她把花儿递过去的时候,还是把想说的话压了下去。他接过花时,她感受到了一下悸动,仿佛花儿是她指尖的延伸。这很傻,她明明清楚,这些花八成是给老婆的,或者给相好的。
所以,你是做什么的?”她匆匆地问话,试图掩盖自己的不好意思,边说边走回柜台背后的位置。“我见你常来,所以想问问。”这是轻描淡写了,在她心里她已经给他写好了细致的人生剧本——一位专攻大脑的医生,会拉小提琴,喜欢臭豆腐,常在公园散步,曾去过日本。
他看着她,微笑起来。衬衫干净的线条,乌黑杂乱的头发,这两者的对比让她上头。她想靠在柜台上,盯着他每一缕发丝,数着他下巴上的胡茬。"我卖东西,"他说。然后,打量了她一下,似乎在重新考虑之前的说法。"呃,我是做销售的,"他纠正道,然后又是那种微笑。他把花儿小心翼翼地交叉放在柜台上,开始翻找他的钱包。"来,给你我的名片。
晓蕾低头研究了一番,哑光的名片摸上去很厚实。公司是她从没听过的,她绝不会好意思去问公司做的是什么。
你总是可以通过街道上红色尾灯队伍长短来判断时间,此时黄昏正在逼近。沿着这条街往前一点,是一个价格不菲的住宅小区,四围有粗壮的灌木和高大的铁栅栏把守。这座名为凯旋大厦的楼房竣工已有六年,却还带着一种刚从远方移植过来的迷茫感;对于大厦的新业主们,周遭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配不上他们的消费能力。晓蕾现在朝这幢楼看去,似乎为了寻找线索。她不说话是不是不太礼貌?她应该说话吗?
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她身上,他摸索着,掏出口袋,寻找他的钱包。沉默已经持续了太久。"那边环境不错,"她最后犹豫地问。"你住在凯旋大厦吗?"
他又看了她一眼,这次停留更久,他的眉头微微弯起。"对的。"他点点头,递给她两张钞票。"你也是?" 当然,这么说完全是礼貌;她穿的是一身工装围裙,能看到他脸上因为若有所悟而掠过了尴尬,她摇摇头,试图想出再说点什么。"我住更远一点,"她答。他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看了看表。
绝望在她血管里涌动,过去两分钟内,她向他索要的,已经超过了过去两个月。再过一会儿他就会消失,又会有一个礼拜不见。她比往常更刻意地数着他的找零,希望他能问她点什么,任何问题都好,他没有。她停顿了一下。"呃,保重。"她说,无法掩藏声线中的遗憾。
他微笑着拿起花束 ,吸了口气。“谢谢”,他说,“再会。
他走了以后,她开始用报纸楔子掸掉桌上的杂碎枝叶,脸颊通红,生自己的气。他肯定觉得她有点古怪,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甚至可能他不会再来了。打听凯旋大厦的情况,在他听来一定是有点越界和奇怪;她太贪心了,应该把这问题留到下礼拜,每次一点点地拼凑她想知道的各个细节。但那样一来,就得几个月,甚至几年了,她可不想在这花店柜台干上那么久。
在招呼后面一位顾客时,她注意到柜台上落下了一支笔。黑色的笔身,腰很粗,中间镶了一条窄窄的银环,与之呼应的银色笔夹上,一条锯齿状的白线刻画出山脉的轮廓。她打开笔盖,在一张收据的背面画了长长一笔—— 墨水也是黑的,很浓稠,在她的手下流淌,如一条受指挥的小溪。一定是他落下的,她心想,并把它滑进兜里,落袋的那下份量十足。
在最后两位光看不买的来客之间的一个钟头里,她把最后那些还有救的花儿捆成花束,这样明天可能卖出去快一点。外面的车子已经越来越稀少,她把漂白剂同水混合,跪在人行道上擦洗水桶,这时只见一个女人从她身边大步走过,进到店里。晓蕾就一边在她的围裙上把手拍拍干,一边后脚跟进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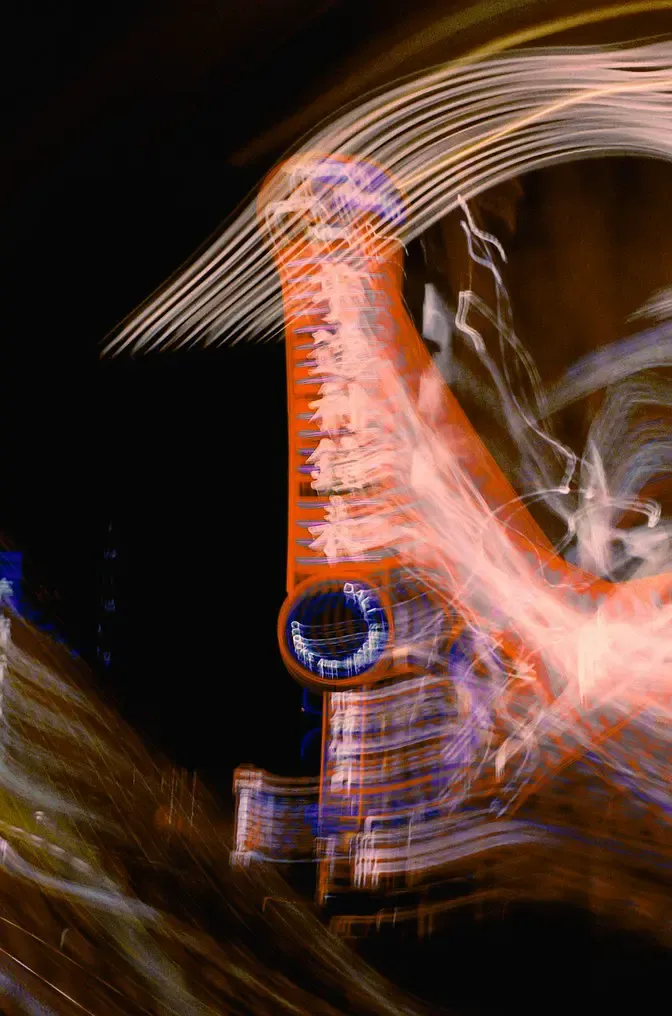
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如下:带着水晶铰链的大墨镜顶在头上,一张素颜的脸,完美无瑕,让晓蕾忍不住想去找出些破绽。她穿了一条紧身运动裤,挎了个金色链子的粉色钱包。晓蕾想,是个马上要嫁人的女人吧,不过女子一个人这么晚来店里有点少见。或者,已经结婚了,跑过来为了打听老公的花还送去了哪里,这种情况以前有过一次。
我老公把他的笔落这里了,"那女人讲。"你有看到吗?"
五味杂陈的心绪像云朵一样掠过晓蕾的脸。她不知道自己期望那男人的妻子长什么样子,但反正不是这样的。不过心底里她依然会仰视她;她长得漂亮,这是那个男人应得的。尽管坦率讲,她的脸上有点东西让人不舒服。她看起来就像那种贵妇——买狗粮的时候一掷千金,算佣人工资时却找由头克扣。
过了好一会儿,晓蕾才意识到沉默已经持续了太久。"我们收过几支笔,"她慢慢地说,感到身上的罩袍变得沉重,很不成样子。她走到放现金的抽屉,拿出一把圆珠笔,煞有介事地摆在柜台上。
那位女士摇了摇头,有点泄气。"不,我说的是一支好笔,"她说。"黑颜色,很粗,"她说,然后她挑明了牌子,晓蕾闻所未闻。"你肯定见过的这笔的。
她抬起眼睛和晓蕾对视,盯住了她的眼睛不放。这如同被一条眼镜蛇盯上了一样进退维谷。过了一分钟,晓蕾不想再纠结了,不情愿地从她的口袋里抽出了笔。
这个女人的面色矛盾,一半是如释重负,另一半是愠怒于要她拿支笔出来还扭扭捏捏了这么久。最后如释重负占了上风。"对的,就是这支,"她说,并伸手接过笔。"谢谢。这笔很贵重。
晓蕾突然慌了手脚,强烈的非理性的念头让她又立马抽手把笔收了回来。她尽可能装出公事公办的、介于无聊和无趣之间的语气。"很抱歉,我不能给你。得让笔的主人来拿。"
"我是他老婆,"那女的说,她脸上现在堆满了怀疑。"你有证明吗?" 晓蕾说。"一支笔能有啥证明啦?"那女的说,"你到底什么意思?"。
晓蕾耸了耸肩。
"你知道吧,那支笔很贵,是他老板送的。你不会想给他找麻烦吧?"那女的说。"如果我拿不到笔,回去他就会不高兴,我也会不高兴。"
内心,晓蕾僵住了。然后那个女的又笑了,表情那般自信,这下有些事情就板上钉钉了。她不会把笔交给这个女人,绝对不。丢了的昂贵钢笔这事上并没有什么规矩,但如果有的话,晓蕾确信她是对的;毫无疑问,失物得让其主人自己来领。她故意在柜台后面的凳子上坐下来,好像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阵线。
那个女人盯着她。"你耳朵聋了吗?把笔给我!"
一对退休夫妇从外面经过,他们迈着老年人的缓慢步子,微微弓腰。她一眼就认出他们了:那个老公公以前经常在早上提着笼子遛鸣禽,直到有一天那手里的鸟笼不见了,她好奇那只鸟怎么了。听到女人提高的嗓门,这对夫妇停下来,探视店里的情况。
那位女人样子像是要往柜台后面走过来。"把笔给我!"
"不行,这边是店员的地方!" 晓蕾的反应能力是在这些年的城市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她的右腿弹出,迅速挡住了她的路。
"强盗! 小偷!"那女人喊道。"我要报警了!
这下晓蕾义愤填膺了,提供了她延长这场对峙的斗志。"去报警啊。 我不会给你开这个口子的! 我们有规矩。"她骄傲地说。看到退休夫妇在门口不置可否,晓蕾连忙把他们招为盟友。"她想让我把笔直接交给她,但这不合规定。" 老奶奶似乎有些迷惑不解,但老公公在听到晓蕾的解释后,转向里面的女人,轻轻地说,"这规矩是为了你好,"他说。"谁会希望自己落的东西被别人随意拿走呢?跟你的丈夫去讲,让他回到店里来自己取嘛。"
听了这话,女人掉头往外走,临走还在地上吐了口痰,留给晓蕾一句,"你会后悔的”。

多年以后,夜晚在床上辗转之际,晓蕾有时会回想从前,想到有许多事情本可以有别的做法。她本来可以把笔交还给那个女人,后一礼拜重新见到她的老公,假装无事发生,继续卖花给他,周复一周,有大捧的玫瑰,也有长久不凋谢的百合。她也可以攥着那支笔,在下个礼拜或者次日还给女人的丈夫;如果真的非如此不可,他大概会亲自回来拿的。或者干脆把它藏在口袋里,远走高飞,也许能把笔当掉,用这笔钱启动自己的生意。
实际上,那个女人离去以后,晓蕾匆忙关了店门;她可不想冒着她真的把警察叫来的风险。当天夜里,她把笔夹在皮包里带了回去,换了两路公交来到一个夜市,坐在铺子外的凳子上,其他下班的工人旁边,嗦了一碗特别美味的酸菜面汤,然后朝她租的房间往回走。
是夜,她没睡好,梦见了那个死在楼上的男的。梦里,他们在黑暗中坐在同一辆大巴上,上海灯火通明的楼房在两旁划出模糊的光影。他坐在她身后那排,身体前倾,他喃喃自语的声音传到耳边,急切而有规律,倒也没让人不舒服。他手持一束雏菊,花瓣挠得她的后颈生痒。接着场景转换,他们一道在舞池里旋转,头顶一颗巨大的舞厅球灯,射出五彩斑斓的光。
翌日晓蕾休息。通常她会躺在床上看些情节艳俗的流行小说,偶尔也会去外滩,坐公交过去大概一个钟头,那也是她知道的少数几个能逛的地方之一。她喜欢眺望浦江对岸东方明珠塔上闪闪发光的粉红圆球,还有那扫描天际线的五彩光棱。有时她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直到发觉摩天大楼的灯光也在午夜将至时歇息了。在上海的头一年,她经常过来,直到有天,她无意中听到一个衣着亮丽的女人告诉身边朋友,那是 "一帮乡下人去看的地方"。此后她就不太过来了。
晓蕾在床上躺了会儿,试图重新睡着,最后她感到无以入眠,终于起身。她套上了一件白色的连帽衫,上面写着“superstar”的字样,字边上镶着金色边框。她很少穿,怕给它弄脏了。她戴了一顶很搭的棒球帽,穿上了她最标致的牛仔裤。在她的床底下有一管大红色的唇膏,是她搬来城里不久时买的。只涂了一次她就束之高阁,因为带来的外表上的巨变当时让她羞惭又讶异。今天,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涂在唇上。她背起女式钱包,走向公交站,嘴里轻轻地哼着歌。
她刚到上海的时候,装瓶厂的女孩们说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赚钱,要么嫁人。但现在,她仍在挣着那点微薄的工资,唯一对她表露过兴趣的男人是她工厂的老板,已婚,年纪是她三倍。那时她在厂里工作了两年,某天,他招呼她去办公室给她结那礼拜的工资。当她在他的桌前弯腰签收时,他把身子靠了过来上,捏了捏她的胸,像是在菜市场上检查一只水果的软硬。他问"喜欢吗?",呼到她耳边的气息热乎乎的。晓蕾挣脱了,没不久就辞职走了人,但偶尔她也会忍不住思忖,要是不拒绝的话,自己的生活会不会更好。
她在离凯旋大厦不远的地方下了公交。当她走近其外围茂密的灌木丛时,她步子变慢,心跳加快。那高高的黑色大门紧锁,不过她一直徘徊着,趁有住户进出时赶紧溜进了门里。比她想象的要容易。里面是一片绿地,灌木修剪成球状,大理石地面的大厅里立着个天使手持三叉戟的金色雕像。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头顶上传来钢琴曲的旋律。一个保安无精打采地坐在前台,但他一见晓蕾就抬起了头。
登记”,是那种咕咕嚷嚷的保安口气。
我只是等朋友,"晓蕾一边说着,一边漫不经心地单手捋了捋头发,这腔势是从那人的老婆那里借鉴过来的。警卫狠狠地瞟了她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大厅的一侧挂着一面大镜子,另一侧放了张白色的皮革长椅,晓蕾心存感激地坐了上去。她拿出那支笔,瞧了一下,然后留心地把它塞回了包里。那个男人会感谢她归还了这个宝贝。他会待客一样招待她,茶水以精巧易碎的玻璃器皿盛装,茶点是纤薄饼皮卷成的千层酥。以前在村子里,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的她,看过一档流行的电视节目,有一集讲了两个女人在大城市公寓里的生活,家里所有的装修和内饰都用了白色——白色的皮革沙发,白色的簇绒地毯,白色的百合。她想象他的公寓兴许也是如此。他们会并肩坐在沙发上,他会把身子压过来,像那装瓶厂的老板一样。只是这一次,她不再会反抗。
几个钟头过去了。空调一直徐徐送来凉风,同时夹带着特有的漱漱声。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过来,几个保姆领着他们打扮漂亮的孩子走过去。刚才那保安下班了,换了另一个上岗。晓蕾时不时地假装在打电话,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坐在那里,观察着此处场景。她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坐的地方离她长大的那个尘土飞扬的村庄有千里之遥,但她像坐在自己家楼下一样舒适惬意。她喜欢打量业主们的脸,后者显得那么聪明和文雅,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话不会只是些——要下雨了;大概是吧;吃了吗,吃了;今天外头挺热。
她想起了她爷爷,他去世前一年办了八十大寿。一群乡亲聚在一起吃烤山鸡,吐出一长串祝酒词之后,他告诉大家说,很高兴自己一辈子都生活在乡亲的身边。他对自己从未离开的事实,真心实意地感到自豪。这样的想法晓蕾听了只感到害怕,她暗下决心要远走高飞。
电梯叮的一声,把她从遐想拽回。她抬起头,见到她最中意的客人闪身走进电梯,公文包干练地夹在一只胳膊下。她起身跟上,刻意让步伐看起来没有很刻意,但电梯门已经关上了。头顶上的金色面板显示,他在四楼下了电梯。前台保安正忙着和别的住户闲聊。她急忙走楼梯去追。
她跑到四楼时,他正走进大厅尽头的那间公寓,然后带上了门。这边地面铺着深蓝色的地毯,顶上挂着仿水晶质地的吊灯。她突然感到一丝害羞,开始却步。四周非常安静。对着电梯旁的一面镜子,她仔细检查了自己的妆容。摘下棒球帽,润了润嘴唇,抚平了头发。她告诉自己,你已经走到这么远了,别怕。
几分钟后,她敲起了他的门,无人应答。过了半晌 ,她又敲了几下,这次更响了,这才听到了脚步声。门打开时,他站在那里,穿着汗衫和短裤,明显刚刚换好。"什么事?"他口气有些不耐烦,"你什么人?"
”惊讶之余,晓蕾试图开口发言。"我是......"
"你要干嘛?"他说。眼里没有一丝认出她的痕迹。
晓蕾听到公寓里头传来女人的声音。"我不晓得,"他扭头向里屋回答。他又看了看晓蕾,这次目光更显疑惑。"我们不感兴趣。
她能瞥见公寓的里头,摆了一张红木咖啡桌,一口迷你喷泉嵌进墙面,抛光的乌黑圆头吐着水泡。见到晓蕾,本来蜷缩在沙发上的白色狮子狗立了起来,吠了几声。而那个男人,看上去仍然没有认出她来。
真对不起,"她说,失望的情绪像巨浪一样碾压过来。她向后退了几步。男主人奇怪地看着她。"不要紧,"他说,然后咔哒一声合上了门。也不知怎么做到的,晓蕾还是找到了出楼房的路,脸颊发烫,匆忙下楼之际,她没有再左右张望。外头凉爽的空气让她松了一口气。她流了许多汗,还是及时想起要脱掉她的纯白色运动衫,以防止弄脏。走这一趟走太戆了。对他有所期盼,也很戆。以为像她这样的人可能会给他留下印象,就更戆了。她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作为某种惩罚,手臂上留下了刺眼的红印子。她坐了会公交,然后昏头昏脑地走回家。一进家们,她马上爬进被窝,躺着,胃里感觉有个洞,胸口填满了羞耻感。好在最后,她睡着了。
她回到店里是第二天,上班前她在批发市场水渍斑斑、晨光熹微的街道上转了四五个钟头。进了门看到永洁挂着不祥的表情等着她,她这才在钱包里翻找起来,笔却不见了。她不晓得笔是被偷了还是掉出去了。不过这并不重要。妻子在前天清早就找到了她的老板。在这天晓蕾回到店里之前,怀抱花束双臂汗津津的永洁,已经下定决心:晓蕾被炒了。随便找个年轻姑娘都可以干这活,讲不定还干得更好。
听到那女的声称的这支笔的要价时,晓蕾大吃一惊,那都快是她月工资的二十倍乐。"她肯定在骗人,"晓蕾急了,"什么笔这么贵?"晓蕾几乎肯定,永洁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笔。但在那关头,后者装出一副识货的样子当做挡箭牌。她说,那是个著名的欧洲品牌。
好啊,那它也可能是假货。",晓蕾心里未能尽忠职守的惭愧感像是昙花一现。"谁会随身带这种名笔?"
永洁没有反驳,但也拒绝支付晓蕾最后两周的未结的工资。"她说:"你给我捅了个大篓子,更糟是算你走运了。"人们会闲话的,我们主要的客户都住凯旋大厦,以后没人高兴来这里了。"
晓蕾也懒得辩解了,永洁说的多少有点道理。起码,某位每周光顾的回头客是再不会来了。"我真的是弄丢了。"她的意思是指那支笔,但她老板不为所动。
"你也清楚丢不丢已经没区别了,"永洁一边说,一边把白色菊花戳进一块绿色的塑料泡沫里,仿佛晓蕾已经消失。
在之后寻觅下家的几个月里,晓蕾发现自己总在城里各处的文具小店里停下来寻找类似的笔,想弄清楚这样一支昂贵的笔,是否真的存在;而如果存在,又在会是在何处。她见到了细杆的圆珠笔,有的装着古怪的粉色或绿色墨水;还有各色文具进口自韩国,有透明的、有中性笔头的、还有可伸缩的。她把各种笔拿在手里加以评估,掂量它们的价值。
晓蕾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那男人的笔相处,用手指搂着它,揭开笔盖,亲自好好体会,更遗憾她没有把这支笔留下来。她当然有再回来过,甚至向批发市场的几个商贩打听,又回到凯旋大厦的周边找了一圈,但一无所获。
即便她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挨家挨户兜售着洗发水和护发素,那支笔仍然让她魂牵梦绕。那时她买了辆自行车,在上海的街道上骑着来来回回,偶尔她会在文具店前跳下车来,每隔一个季节去检查店里的货架。这是一个不太困难的任务,让她拥有了几分掌控感,掌控这个否则准把她压得服服帖帖的城市。
有一次,在一家药房里,她看到一个女店员在用一支胖胖的黑笔在填收据。那形状是她熟悉的,她见了心跳都要停了。"我可以试试吗?"
店员抬了抬眉头,但晓蕾怯怯地坚持着,最后店员耸了耸肩,给了她笔和一块薄薄的灰色纸板来写,后者原本是一个药盒的内侧。这支笔比晓蕾印象中的要轻,不带银笔夹,也没有山峦的镂花,但握在手里的感觉就和那时候一样,而且它也带着那种有点夸耀的光泽。"这笔多少钱?"她问。店员皱着眉头说。"不卖,"
"求你了。"晓蕾说。她开始写起字来,却发现这不是一支墨水钢笔——里面是粗糙的圆珠笔头,在纸板的表面擦过时转得并不顺溜,只留下一缕印痕。
书记员说:"垫个垫子更好写,"这倒是真的。晓蕾看到她刚填好了一张收据,黑色的笔迹清晰。店员好奇地打量她,然后好意地把垫子往前推了推。"你可以试试。"
但晓蕾已经摇着头消失在了门外。"谢谢。"她回头喊道。"我在找的不是这个。
This article appears in the January/February 2021 issue.
"This story is an excerpt from Te-Ping Chen’s upcoming collection, Land of Big Numbers.
We want to hear what you think about this article. Submit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r write to letters@theatlantic.com.Te-Ping Chen, a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r, was a Beijing and Hong Kong correspondent for the newspaper. She is the author of Land of Big Numbers.
原文链接 /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1/01/shanghai-murmur/617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