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東:石頭城紀事與阿爾巴尼亞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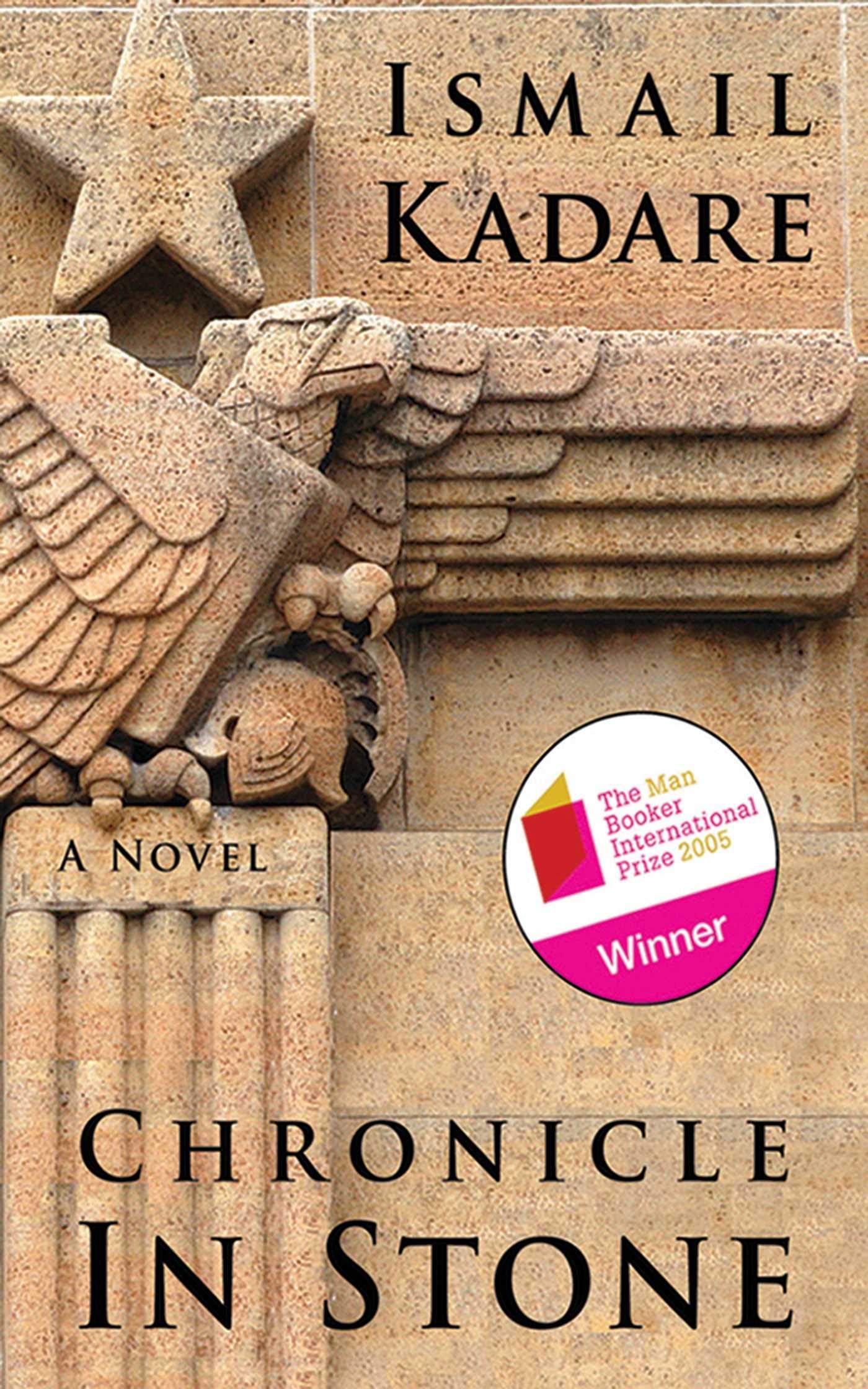
有關阿爾巴尼亞的記憶已經太過遙遠了。當科索沃戰火停歇之後,阿爾巴尼亞再次淡出了我的視野。偶爾提起,只是玩笑,比如,與新京報老總戴自更君一起時,我總少不得拿中國人曾經熟悉的阿爾巴尼亞電影《第八個銅像》打趣他,因為有他記憶疏漏的笑話典故。
不過,當年的“山鷹之國”、“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如今如何,我已完全不關心了。直到翻閱起燕玲大姐推薦的花城出版社“藍色東歐”書系中阿爾巴尼亞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的小說《石頭城紀事》,許多童年時代遙遠的記憶隨之泛起,讓我對阿爾巴尼亞的命運再次好奇起來。
《石頭城紀事》是卡達萊以孩童的視角寫的一部關於阿爾巴尼亞命運的小說,充滿了夢幻般的想像。卡達萊以其充滿靈性的文字,為我們勾勒一座魔幻之城,這座城裡充溢著魔幻般的故事。
孩童是充滿幻想的年齡。小說一開頭,卡達萊筆下的“我”,對冬夜雨水的描摹,從雨點兒從天上落下,跌落屋頂,被屋簷下天溝逮個正著,引向蓄水池——“一座幽深的牢獄”,於是,“它們自由歡快的生活就終結了。雨滴們短不了傷感,回憶起它們再也見不到的遼闊天空,它們曾經飛越過的非比尋常的城市,以及閃電劃開了的天地。”。在“我”的眼中,雨點兒是有生命的靈物。我從來沒有讀到對雨點如此奇特的描述,簡直妙不可言。
不僅是小雨點兒有靈性,在孩童的眼睛裡,一切都是有靈性的,有生命的:“我”會長時間趴在蓄水池大口上與它交談,“它操著地窖的空音兒,總是急於回答我。”水窖是嘮叨的長舌婦,煙囪會像活物一樣哀鳴,大雨之後漫溢的河流形同一匹馬,馬路則會裝死,蛀蟲的合唱,小油燈發黑的燈撚兒悲傷地耷拉著頭。
想像之奇特,文字之靈動,讀起來總讓我欲罷不能。
孩童沒有成人的價值判斷,他們的視角是好玩有意思,這讓“我”眼睛中看到的世界,與大人大不相同。比如,“我”就不能理解“被佔領的城市”,“我”喜歡意大利人的大飛機,甚至為它憂傷——“在哽咽著淚雨的空間擴散著的這種憂傷,究竟是思念誰呢?那邊,遭遺棄的平野百孔千瘡,佈滿水窪。有時,我還以為聽到他的轟鳴,趕緊跑到窗口,只發現天邊懶散的烏雲。”要在中國的文學中,這可太不政治正確了。
當然,成人世界不是童話世界,被佔領的城市就不一樣,皮諾大媽就在去給新娘化妝時被德國佔領者打死了。就像雅維爾跟“我”講“我”卻不明白的話:“你們不可能明白,一座自由的城市是怎麼回事兒,因為你們是在受奴役的環境中長大的”。
石頭城是一座一直受到奴役的城市。十字軍東征來過,土耳其人來過,希臘人來過,意大利人也來了,英國人來轟炸了,德國人又來了。在居民普遍的冷漠中,一種旗幟換掉另一種旗幟。
在城頭變幻大王旗中,石頭城的人,依舊過著自己的生活。尤其書中那些老婆婆們的生活,高齡的她們都是變幻的見證者,她們身上卻有著石頭城石頭一般沉靜的力量。她們個個都是哲人。比如,傑莫大嬸在評論意大利人的潰逃時感歎:“整個世界完全成了泥水坑。”“君主制就是這樣退場”。“他們退場了,讓位給另外一些人,身後只留下污泥和瓦礫。”
想想,這像是一個家庭婦女說的麼?
關於巫婆的故事,我讀到時,突然想到童年時期看的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中的那句台詞,我至今未忘:“東南方向鬼來啦”。
有時候這座城裡還有莫名其妙的荒誕,比如侵略者飛機來轟炸了,未經市政當局同意開炮打飛機,還被罰了款。
在這座城裡,愛情是禁物,關於愛情,沒多少文字,卻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淒厲的愛情故事:空襲時青年男女情不自禁擁在一起,被視為醜聞,這座城市讓懷孕姑娘消失有兩種辦法,一是用鴨絨被和墊子捂死,一是投進水井淹死。那個男青年聽聞之後,說,“如果在人間找不到她,我就下地獄去尋找。”他果然這樣做了,一個個蓄水池找過去,自然不能找到。
本書中,關於當年中國人民的朋友恩維爾·霍查同志,有數次提到,提到他是石頭城人,在法國讀過書,怕被人認出戴副墨鏡,通緝令上有懸賞金額,也提到他要打一場新型戰爭,為了革命事業,親人們開始自相殘殺,酋長把寧願把鐵釘插進自己的眼睛,也不願看見共產主義。
當我最後合上這部小說的時候,重新翻到第一章,我恍然,卡達萊不是簡單地以一個孩童的眼光想像雨點的命運的,這個描摹,既不是顯擺作者的想像力和筆力,也不是與小說主題關聯不大的場景烘托,其實,這小雨點兒的命運,隱喻著石頭城的命運,是石頭城被侮辱與損害命運的寫照。
我不是文學批評者,只能從一個普通閱讀愛好者的角度來談自己的感受。我讀小說很傳統,喜歡看經典的故事結構,但卡達萊的這部《石頭城紀事》,並沒有傳統小說那種出彩的故事情結,但是,他的敘事角度他的想像力,卻讓這部小說贏得了我的心,也重新激發起對阿爾巴尼亞的好奇心。
感謝燕玲大姐的指引和饋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