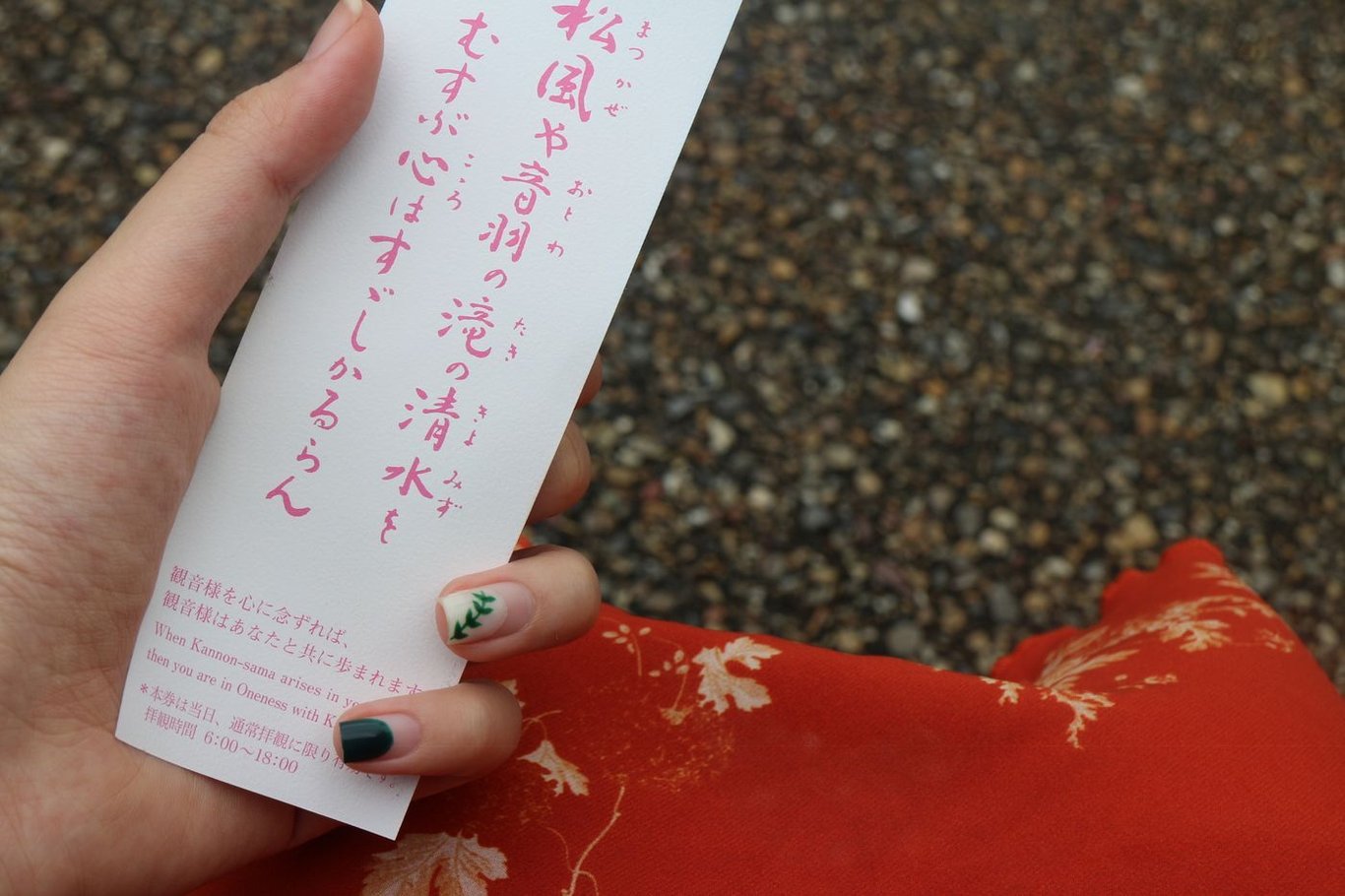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被以蔑视宗教、腐化青年的罪名推上审判台的一刻,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自由言论的殉道者。在柏拉图记录下的《申辩篇》(The Apology)里,苏格拉底拒绝逃亡,饮下鸠酒,以死亡将雅典的民主推上审判台。
苏格拉底之死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权利教育我们未来的公民?
每个社会都寄托于一种社会信条,或说是国家信仰(national creed)而存在,就犹如托马斯·杰斐逊的言论奠定了当代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一旦这种信条遭受挑战和质疑,社会就缺少运转所必须的公民虔诚(civil piety)——就连苏格拉底本人也承认,信仰或虔诚是维持一种社会统治的基础。但是,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是在这种国家信仰和法度之上的:他反对神谕式的思想灌输,而鼓励对话式的争辩和讨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智库。他对雅典城邦信仰的挑战是一种哲学上的挑战,而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怀疑。哲学是一种以自己的推理、逻辑和知识去取代现有观点的欲望,苏格拉底相信自己,作为一个被“神”选定的智者,有超越现有法度的良知和公义,他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定义正义,并将自己描述为“神的礼物”。他追求的是一种对雅典公民社会革命性的改变:人们不该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追求物质上,而应该关心正义和道德,关心自己灵魂的状况,即: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那么,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苏格拉底吗?或者说,自由言论和公民虔诚谁更重要?
很难想象一个所有人都是苏格拉底的社会,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判断置于社会法度之上,并且这种自我赋权毫无根据(没有谁见过那个选定了苏格拉底的神明)。如果社会给予苏格拉底无限制的宽容,对所有的言论和观点都开放,那将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每一种观点,无论是肮脏的,还是卑鄙的,都被赋予同等的合法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种虚无上存在。
所以就连苏格拉底本人,也在临死前维护了这种法度。他的死是有意设计的,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公民不服从——为哲学殉道,以让未来的哲学成为一种勇气和正义的来源;一方面,他没有逃走,而是接受了城邦的审判,以死维护了城邦的法治。他因而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