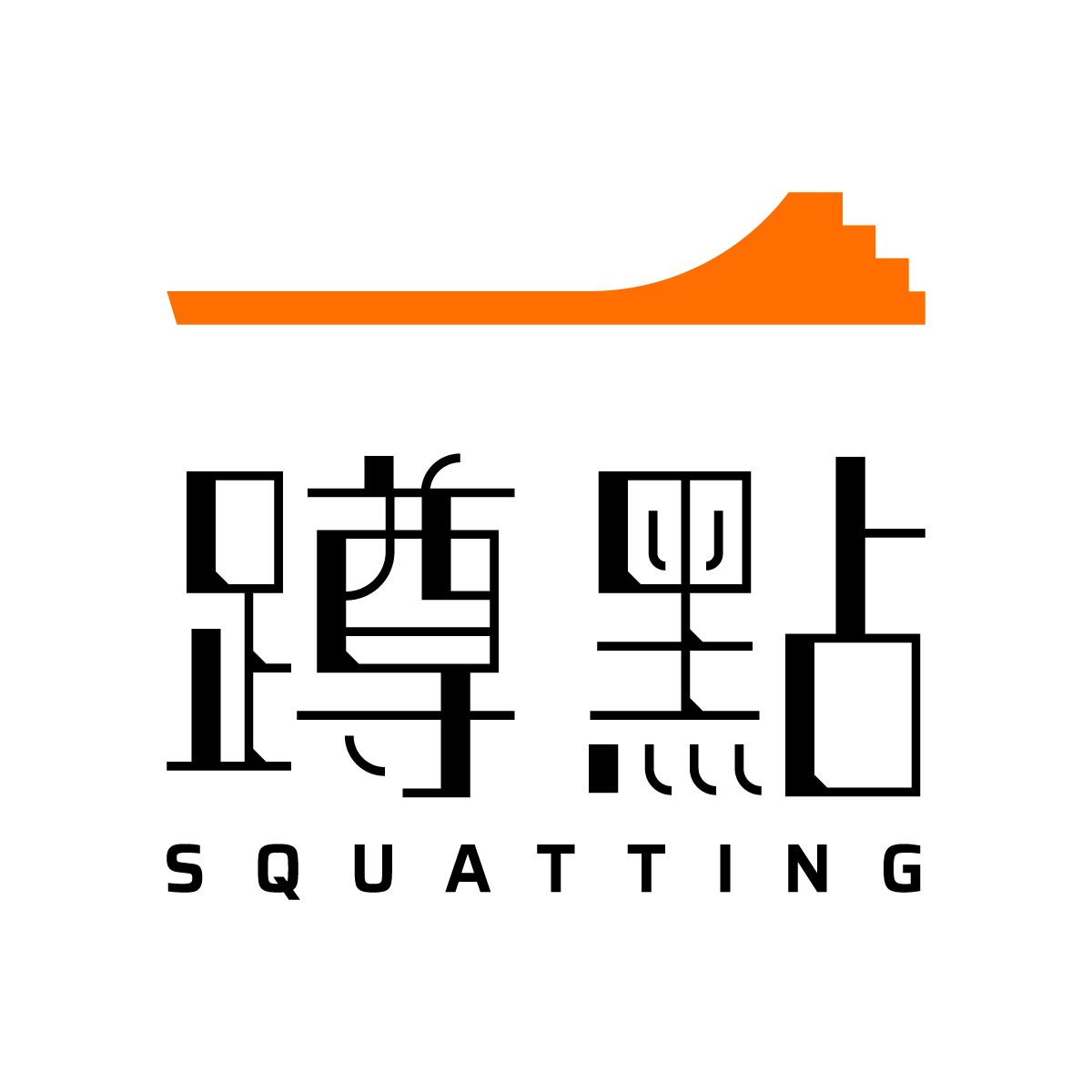阿甘本哲學的貧困之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誰才是「赤裸生命」?

編按:之前,我們分享了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對疫情的評論,他用「傳染病發明論」來警惕人們在「例外狀態」時權力的擴張。雖然這種講法被各方批評,然而在香港,我們見到政府和警察在「限聚令」的執法上越加偏頗......到底在防疫和權力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拉扯?本文作者指出,或者我們更應該追問,這種自由/專制的簡單二分法,是否暗示了在疫症之前,甚至在運動之前,就是所謂「正常」?如果不是,我們將要一種更深入的權力分析。
文/麟暑
在阿甘本對疫情的評論中,他不時慨嘆世風日下,人人甘願淪為「赤裸生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有什麼結果?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才會認為存活是唯一的價值?」;隔離之下的人們「已經被還原為一種純粹生物學的生命,不僅被剝奪了社會與政治維度,連人性與情感也所剩無幾」。在此不難察覺,阿甘本樹立了一組二元對立:一方面是不值一提的肉體生存、赤裸生命,另一方面則是統合了「社會、政治、人性、情感」等等的精神場域。這顯然迥異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觀,反而更接近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中的靈魂/肉體二分法。
阿甘本為何發展出這種對肉體極盡蔑視的理論?我們或可作如是解讀:在歐洲等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體力勞動者向第三世界的全面轉移,勞動者、勞動的身體不再是居於左翼理論之中心的概念。然而,這絕不意味著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階級,沒有人需要為自身「肉體」的存續而擔憂了。恰恰相反,在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進程後,階級分化再度顯現為歐美社會中觸目驚心的現實。
正如阿甘本在西方的眾多回應者所指出的,那些想生存而不能的人,在醫療系統外面排長隊、等一個ICU床位、等一部呼吸機的人,他們才更應該被稱作「赤裸生命」,而不是隔離在家、擔憂自己的精神世界被剝奪的知識分子。
將精神與物質對立起來、並過度誇大精神的作用——這一傾向,在阿甘本的思想中早有苗頭。他曾論述道,「人和動物的區別即在於,動物只有選擇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的潛能,人則有選擇不做的潛能」;而資本主義總是要求人們「學習各種技能,適應各種職業,以便接受市場的擺布」,從而扼殺了人類「不做」的潛能。而什麼是阿甘本心目中「不做」的人類潛能呢?那就是藝術,因為藝術關注的「與其說是行動,不如說是行動的失效」。似乎人類解放的圖像就是人人都做藝術家,拋棄所有生產活動,只從事審美。在此,阿甘本徹底顛倒了馬克思對人類作為「類存在」(species-being)的表述,即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就是人類能在實踐——「做」——中改造自我與世界。
「自由 VS 專制」之外,左翼如何想像未來?
不憚於冒昧的話,我們或許可以如此概括阿甘本的言外之意:要警惕疫情使自由的歐洲向東方專制主義淪陷。韓炳哲,另一位歐洲左翼哲學明星,已在他評論疫情的文章中清晰地表達了類似見解。在阿甘本的關鍵概念「例外狀態」和「牲人」(也譯為「神聖人」)中,我們也可以讀出自由/專制的對立:專制的「例外狀態」對應著自由的「日常狀態」,遭受專制的「牲人」對應著自由的「秩序人」。似乎在「日常狀態」下做一個比較自由的「秩序人」還可以忍受,但是萬萬不能淪為「例外狀態」下的「牲人」。
「自由/專制」成為了左翼哲學家思考的終極坐標,這是一件相當怪異的事情;可以說,這是一種左翼版本的「歷史終結論」。當冷戰終結,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對立結束,似乎左翼對資本主義之外的未來可能性的想像也隨之終結了。左翼理論在後冷戰時代的任務,變成了推動資本主義向著更自由、更民主、更多福利的方向改良,同時警惕資本主義的專制形態。
比如,福柯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生命政治」理論,他的本意是批判以海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說,進而質疑資本主義體系運行的根基。然而冷戰結束後,福柯的闡釋者們卻認為,「生命政治」批判的與其說是資本主義,不如說是形形色色的「專制」:東方專制國家,自由-民主國家專制性的對外政策(如美國反恐戰爭),抑或是自由-民主體制內部的專制陰影(如種種數字監控計劃)。似乎只要我們把種種「專制」因素從資本主義中剔除出去,剩下來的就會是單純而美好的自由-民主體制。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必要去超越資本主義本身呢?
左翼哲學家對「資本主義」這一根本性思考範疇的拋棄,使他們無法看到「自由/專制」或「歐美/東亞」二元對立之下的實質: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VS國家資本主義。即使是左翼哲學家中的「另類」者如齊澤克,也時常掉入這個陷阱。雖然他一直批判後冷戰的西方左翼把自由-民主體制當成戀物癖,但他本人亦常把中國簡單地作為一個失敗了的社會主義專制國家來對待,從而忽略了今日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質。
3月16日,齊澤克發表了反駁阿甘本的文章<監控與懲罰?是的,請吧!>*,其中提到一則中國大陸的新聞:浙江省至少有三所城市給本地工廠設立了耗能指標以彰顯產量回升,這促使了一些企業在工廠空無一人的情況下仍然開動著機器。齊澤克對這一新聞的理解是,它體現了「共產黨政權裡的舊式威權邏輯」,因此中國絕不是他「所構想的共產主義」。齊澤克沒有考慮到的是,給工廠設立「耗能指標」、乃至全國範圍內有關「復工」的種種行政舉措不僅體現了「舊式威權邏輯」,更是徹頭徹尾的國家資本主義邏輯。
正因為齊澤克在某種程度上同樣拋棄了「資本主義」這一思考範疇(盡管這並非他的意圖),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看到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國有化鐵路的舉措或美國總統Donald Trump提議接管私營企業,就認為共產主義有了雛形:似乎對他來說,「自由民主體制+國有化=共產主義」。如此看來,阿甘本與齊澤克所犯的錯誤不是類似的麼?阿甘本看到歐美自由社會出現了國家干預,就驚呼專制降臨;齊澤克看到歐美自由社會出現了國家干預,就歡呼共產主義來臨。絕望的悲觀主義與廉價的樂觀主義,無非是一體兩面罷了。
如果說在全球疫情中真的出現了「共產主義雛形」,那麼它並不是大國們的種種舉措,而是在政府不作為、醫療系統崩潰的情況下,各國民眾的集體行動:自我組織、自我救援、守望相助;更為基本的,是全球無數底層勞動者的付出,才讓社會在危機中免於崩塌。
這才是在「新自由主義VS國家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表現:個人主義自由VS威權主義生命政治)之外,那個真正的第三項:一種集體的、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面對此情此景,今天的左翼思想者需要給出一份真正的回應:與被損害的人們站在一起,共同為人類想像一種別樣的未來。
*Monitor and Punish? Yes, Please!
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