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廖偉棠:異托邦面向自我 |圍爐 · CUHK

我們恆常期待著美的降臨,可當“詩與遠方”的理想成為一種標榜,“氛圍感”成為廉價的時尚,藝術便只能成為生活所扮演的姿態,於是我們被美拒之門外。信息時代中被所謂“藝術”包圍的我們,如何真正碰觸到藝術,又怎樣找到未知角落裡鈍化與失落的自我?
廖偉棠有多重身份:作家、攝影師,但他最珍視的仍是詩人的身份,他的作品流動性極強,時有古典修辭與現代詩語感的結合,在兩岸三地和海外旅居遊歷亦給予他的作品豐厚的滋養。
我們由現代詩始,漫談到香港本土文化,慢慢意識到,或許唯有內向性的覺知與叩問,真誠地面向與記錄,才可找到那“都被分散了的\\一焰我\\一粼我\\一片我\\一陣我\\一縷我”。


爐=甘沐青
廖=廖偉棠
爐| 您在新書《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40條小徑》中提到“現代人對現代詩的疏離”,網絡時代下,我們似乎更容易接觸到詩,但許多時候文字也更氾濫、貧瘠了,那麼我們該怎樣真正走近詩呢?
廖| 有時我們可能會放大一個時代的特徵,但若把時間拉長到一兩百年,網絡對文學的衝擊也許不會特別明顯,它也只是一個載體而已,所以網絡時代對於詩的影響不是那麼絕對的。有人認為網絡的碎片化閱讀有利於詩,我也不完全認同;碎片化是詩的一部分,比如一些短詩和俳句,一些較為即興、感性的抒發也許比較適合在社交媒體上傳播,但真正深刻地切入這個時代,或關於類似生死這種凝重話題的詩,不是在社交媒體一掃而過就能讀懂並留下深刻烙印的。在線閱讀終究是浮光掠影的,所以讀詩還是要擺脫對網絡的依賴,我自己遇到喜歡的詩,甚至一些只能在網上看到的詩,也會盡量打印或者保存下來慢慢閱讀。
同時,讀者自己的主動性也很重要,而非一味依賴推廣者。現在我們有許多讀詩平台,其中的內容良莠不齊,有較好的,但也有一些很時尚化的寫作。如果讀者在當中碰到一首自己特別喜歡的詩,但又不太確定為何喜歡時,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來搜索作者的作品和研究這個作者的相關文章。比如我如果碰到自己喜歡的作者,就會想辦法去讀他的全集;如果是外國尤其英美詩人,我也會找到他們的原本來對照閱讀。讀者不要覺得詩人、推廣者怎樣對待我們,我們照單全收就好了。
讀詩與讀小說相比,對讀者要求的“高”,不一定是說鑑賞力、學養的高,而是要做一個主動的、有想像力的讀者。比如讀一本小說,只要不是特別實驗性的類型,我們比較“被動”地從頭到尾讀完,基本可以得到作者想要傳達的內容。但是讀一首詩,這樣的被動閱讀是不夠的,起碼要發揮想像力:比如讓每一句詩像拍電影一樣在腦海中浮現出來,還原出它的視覺、聽覺、嗅覺等各種感官,這樣做所得到的感受會是翻倍的。我們要積極主動的去投入詩的世界,而不是等待某種詩意的降臨。
爐| 您剛剛講到讀詩時的“想像力”,我們在讀古詩時會有一種“讀古文”的自覺,會自然地猜想一些意象、手法背後的意味,但現代詩尤其翻譯詩的文字更貼近我們的日常語言,我們在閱讀時的想像力似乎更容易被現實經驗框限,那麼您心中現代詩的美感是怎樣的?和古詩的韻味相通嗎?
廖| 古詩的患處在於,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慣性閱讀,由於很多意像已經被反反复复講了一兩千年,我們看到某個詞語、意象,比如“小橋流水人家”,已經有了固定的情感反應。當然也有一些特別的古詩永遠能夠刺激你的反應,它們是會變化的,比如杜甫、李商隱的一些詩,它們其實很接近現代詩。現代詩的一個特點在於它是開放的,這當中的想像是開放的,它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也不期望你去回答標準答案。比如我把一首詩交給你,我不希望你來問我,它真正在講什麼,而是由你來告訴我,“我覺得這首詩是在講什麼”。在這種訓練中,你的感官、感受力、創造力等等,都處於一個被打開的過程,這就是現代詩最大的魅力之所在。它是挑戰性的,而你由此參與了這首詩的寫作,這是很重要的。
閱讀是一種個人行為,我向來不相信一群人蜂擁著共讀一本書的那種行為。閱讀中,每個人都是拿著自己的命運去跟作者的命運做交換,你在其中尋找共鳴也好,尋找碰撞也好,甚至是劍拔弩張的矛盾、衝擊,都是單個的讀者和單個的作者之間一種靈魂的交流。所以這時候越“私人”的東西,往往會是越有觸動的。反而如果寫一些非常公眾的內容,比如汪國真在八十年代引領的那種創作風潮,也許能在一時對某一些要求不高的讀者產生影響,但我不覺得自己有受到任何觸動。每一個有要求的靈魂,都在尋找另一個隱秘的靈魂。你會覺得這個作家他是在為我而寫的,我們是知己,在這樣的感受之下去閱讀他的作品,跟那種類似公文傳達式的共享情感是不一樣的。
爐 | 您講到了閱讀過程中讀者的“個人性”,那麼我比較好奇的是作為詩歌的重要因素,語音會如何影響我們對詩歌的理解呢?比如用廣東話讀一首內地詩人以普通話創作的詩,會影響讀者對於詩歌情緒的感受嗎?
廖| “距離產生美”在這裡是適用的,像美國詩人龐德,他不懂中文,卻又被中文吸引,所以從中發生出意象派詩歌寫作的很多想法,我們在閱讀或寫作中要抓住的就是這樣一個瞬間,去問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被吸引住,而又說不出原因。這個時刻就是你進入詩歌的一個契機,它肯定和你生命中某些東西應和了,但你可能不自知,而一個好的讀者就會把這個“不自知”追尋下去。
爐 | 那麼在您的創作經驗中,會有基於不同語言的讀音上的考慮嗎?您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粵語語言的創作者還是以中文書寫的創作者呢?
廖| 這可以清晰地分兩個層面:如果我寫香港題材,我會用粵語思維來寫,我腦子裡思考時的聲音是粵語,我比較少用口語去寫作,而主要用廣東話發音的書面語;而寫大陸、台灣的題材,就會用普通話的聲音去思維。但我不會很刻意地去想音律的東西,因為音律的計較是寫詩的初步階段,我很快渡過了那個階段,是因為受到爵士音樂的啟發,我覺得爵士樂的自由,那種像呼吸一樣的即興,那才是更符合現代詩聲韻的靈動。
所以在我以前早中期的寫作中可能是感覺到一個節奏,去把它寫下來,而受到爵士樂影響以後的寫作中,我所感受到的節奏更像是一個樂句,從這個樂句我可以衍生出很多變奏,我也任由它變奏,這也是藝術對於藝術創作者的回報吧,在這種自由的創作裡,你是快樂的。我們從寫作中感受到的快樂不一定是源於題材的,也不一定是由於所謂成功與否,而是寫作過程帶來的快樂。在你放開對音韻、語言的很多固定想法之後,就能夠進入這種快樂的自由里面去。

爐| 您提到音樂對您詩歌創作的影響,顯現出不同形式藝術之間的相聯;您同時也是攝影愛好者,而攝影的本質實際是記錄下某個必然發生過的瞬間,在既有的現實裡表達自我,您覺得詩歌是相對更自由的嗎?二者的關聯又是怎樣的?
廖 | 文字的自由也是相對的。攝影好像很受限,拍到與否自己無法掌控,很多時刻錯過就沒有了,但恰恰在於這樣的原因,超現實就誕生了,即你不知道自己潛意識中傾向去拍的是什麼。尤其以前用膠片攝影的時代,拍完要沖洗才能看到影像,而不是像現在常常是經過自我審查後不滿意就刪掉。以前的攝影保留了更多潛意識層面,因為有些東西刪不掉,你才會去看;你曾經認為某張照片是醜的、不好的,但過十年後再看,才發現那張照片恰恰就是當時的你。
在詩裡面也會有這種情況,你最後寫出來的詩不一定是你想寫的那首詩,這時候你要聽詩的話,也許它在揭示一個未知的你、一個未知的世界。你一開始想寫的一首詩,寫著寫著就變了,這時候其實是詩的規律介入了。這沒有那麼玄,它不是一個神,其實就是潛在的你,用弗洛伊德的講法,就是你的本我、超我都在作用,如果不通過藝術,你是沒有機會釋放他們的,當你釋放他們出來,就要尊重他們,不要急著用理性的自己去否定他們,這就是詩的美所在。
爐 | 您所說寫詩的時候理性的介入讓我想起了海德格爾關於語言哲學的觀點,您本身也閱讀過許多哲學作品,這對您的詩歌創作有怎樣的意義?哲學的思辨與詩歌的關係是怎樣的?
廖 | 海德格爾後來認為自己不是哲學家而是思想家,他認為古希臘以後,思想被哲學取代了,令我們遠離了真理。真理應該是我們的近鄰,“詩”和“思”是鄰居,我們要意識到這種近鄰,才能真正去進行思想,而不是像在學校學習哲學一樣把一切系統化、辨證化。
我在讀其他哲學家作品時也會警惕,會提醒自己是作為一個詩人在讀這些內容,而不是在裡面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很多人尋找哲學、形而上學,是為了尋找生命某些答案,希望可以在康德、黑格爾那裡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但詩恰恰相反。詩是不解決問題的,詩沒有答案,也沒有義務提供答案,詩歌可能製造出更多的神秘、更多的問題出來。
詩和思想之間應該是一種共鳴的甚至是一種互相拉扯住、有張力的關係,所以無論讀詩還是哲學都好,我們要摒除掉實用主義或者功利主義的閱讀,而只是把自己交給它們。同時,無論對方是多偉大的“海德格爾”,當你們進入這個語言的場域時,你跟他是平等的,像是《詩經》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種境界。當你們是在琢磨切磋一個問題,那你就能夠感覺到海德格爾所說的“思之美”。而“思之美”到一定的境界它就是一種詩。
爐 | 閱讀他人的作品給創作者的影響有時或許是潛移默化的,不一定是創作者刻意的複現,那麼怎樣在輸入和輸出之間找到一個“自我”的平衡呢?
廖 | 對於初學寫作者的建議,我們的共識就是多讀、多寫,這是必然的。不久之後的某一個時刻你會意識到,你不止是在讀他的文本,你要讀出他的世界來,這時候一個又一個的平行世界、平行時空就會在你的思維里面展開,你的思維里就會有很多個聲音在激盪,這時候你就不是單純在“學”某一個詩人,而只是認識一個好朋友。對於一個好朋友來說,你不會想著去學到什麼,你們如魚得水般地相處,就足夠了。再進一步,如果真的要學到什麼,往往也不只在於技巧性的東西,更能學到的是一個詩人面對他的時代的態度和方式,也許是曹操面對三國、杜甫面對中唐——你要學到的是你要採取一個怎樣的姿態去迎接這個時代的衝擊。
爐| 除了詩人對於時代的態度,外在的環境也會影響創作者的表達,不少作者的文風都有有強烈的地域特性,那麼您認為地理氣候、人文景觀等外在環境對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廖 | 所謂地理、氣候,其實可以歸結為“風土”。風土是一個作家成長過程中滋養他很大的一股能量,而且這種滋養是潛移默化的,也許你沒有自覺,而當離開的時候才會意識到,比如我離開香港來到台灣,才意識到香港滋養著我的東西是什麼,這種影響是蠻決定性的,尤其對小說創作相對來說是更明顯的,但在詩裡面,它不是徹底左右一個詩人的東西。詩是一個楔子或者說引子,每個詩人內心都有一個自己建構的理想世界,這個理想世界是和現實世界在對話之中,在這對話過程中,可能很多詩意就碰撞出來。比較好的例子是杜甫的《秋興八首》,其中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唐朝的世界,一個是他心裡幻像一般的混合了中國很多時期的世界,它們會不斷地交流,所以為什麼詩瞬間的爆發力和張力會那麼強,就是因為詩人的自我意識非常突出和強烈,再配上周圍的環境(包括剛才說到的風土人情),是一種劇烈地碰撞和交流的狀態,所以讀一首詩的時候會覺得它的情感力度往往會大過一本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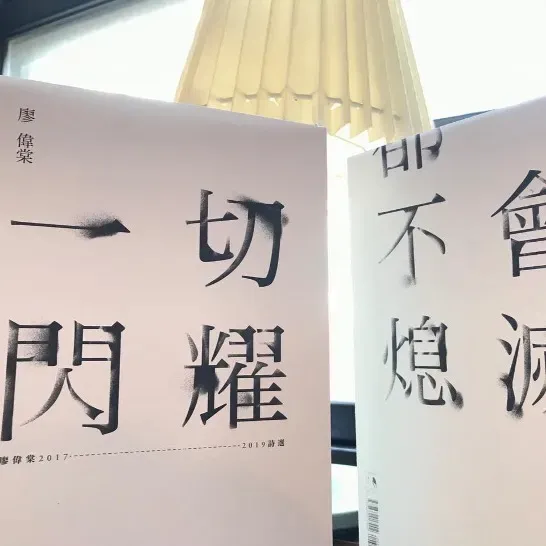
爐 | 那麼香港對您創作的“滋養”是怎樣的?
廖| 很大一部分來自香港本身的社群氣質很強烈,會令到你接觸到很多人,其他人跟你在各個社區、群組裡面的交流互動也相對多,在這個基礎上,我自己也一直都很關注社會運動,從這個角度看,它也給了我很多機會去接觸不同層面的人的生活,而去理解他們。這樣我才能夠寫出香港的詩歌傳統。香港一直有很強的城市詩的詩歌傳統,這個“城市”不是說摩登大都市,而是一種“人的日常”。這個層面上我們也可以說香港詩相對是一種“民主”的詩(這個“民主”也可以套到政治學上的概念來解釋),香港詩裡面詩人的自我認同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像大陸一些詩人可能覺得自己是一種“精神貴族”或者說覺得自己是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那種詩人。他首先是一個香港人,然後才是一個香港詩人,這是一種很民主的“詩學”,這種詩學能夠讓你體察人性和物性,去體察周圍的香港人,體察這個城市的喜怒哀樂和命運,這個城市這兩百年來的東西,會更加親近一個詩人。但如果你在北京、上海,作為一個寫作者,會感覺離地很多。很多東西在拒絕著你,很多敏感詞、敏感區域,會阻止你走向不同的群體。古詩《詩經》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幾種功能在大陸可以說都被剝奪了。可能只剩下“興”吧,你可以說一些象徵的、隱喻的東西,但是通過詩去聚結有共同想法的人,這是不可能的。
爐| 常在您的創作中看到時事相關的題材,也想到您的一句詩寫“把街頭還給戈達爾,把詩歌還給政治”,聽您講完覺得政治在詩歌中的出現其實是一種創作者基於生活的自然表達,而不是作為一個元素刻意的安排?
廖 | 我想對於一個正常社會、城市的一個正常人,政治本來就是呼吸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我們之前害怕了,或者說在自我審查的情況下就會覺得“詩歌不要沾政治”。但“政治”是什麼,它不是政客的勾心鬥角、政權的輪替,其實政治的本意就是人如何自己管理自己,這是一個寫詩的人、一個普通的公民都有責任去做的東西。所以我寫這句詩就想表達不要割裂詩歌和政治,不要認為詩歌就應該是風花雪月的,要是超現實的。詩歌深入現實的時候,也可以達到超現實,深入政治也可以超越政治,這當中很多都基於我們的定義,而我們的寫作也是在重新定義、把很多詞拉回它原本的位置。這兩句詩表達得很突兀,和我們的潛意識不合,其實也是想造成讀者頓一頓,想想“他為什麼這樣寫”,想一想是不是我們對政治的想法太缺乏想像力了,我們的思維僵化了?
爐| 這也讓我想起近年香港本土文化的興起,當中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都帶有一種個體在社會中所遭遇的茫然或困惑,同時身邊很多內地的朋友也非常喜歡有類似表達的香港音樂人(比如mla),好像雖然有著語言和語境上的相隔,但這種情緒卻是相通的?
廖 | 可以說是時勢造詩人吧,mylittleairport,更早的達明一派,甚至Beyond這樣有自己的立場態度,在作品上非常重視自我表達的音樂人,香港會有很多。大陸有很多實驗音樂人、小眾的音樂人可以做到這些,但是香港可以見到相對比較大眾的音樂人也能去嘗試,這跟整個香港詩在這二十年來的蓬勃是並行的。所謂“時代不幸詩人幸”,對香港來說,過去二十年浪潮澎湃,這樣的一個大風大浪的時代中間矗立著一個孤島一樣的城市,每個人必然都是心潮澎湃的。在這種狀態下你自然很想去抒情,去表達自己。而以前的香港,表達自由度還是很大的,現在雖收緊了一些,但大家還是習慣“我口說我心”,表達欲還是很強,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自由社會給我們奠定的、像是天性一樣的東西,恰好這又是詩所要求的天性——暢所欲言,沒有什麼是詩的禁區。所以香港的詩和由詩變種而來的帶有社會關懷、時代認同的流行歌,都特別蓬勃,而傳到大陸,也會令人耳目一新,因為(一些藝術創作者)作為偶像歌手卻能夠為一代人去發聲,在他們身上凝聚了一代人的期待或者說這一代人所承受的東西,大陸的朋友會比較容易感受到這種表達上的落差,所以我也蠻佩服像黃耀明在大陸的粉絲,我覺得他們是真正相信藝術力量的人,才能夠堅持下來。

統稿 | 甘沐青
審稿 | 於滕浩然
圖 | 廖偉棠
微信編輯 | 蔡佳月
Matters編輯 | Marks
圍爐 (ID:weilu_flame)

文中圖片未經同意,請勿用作其他用途
歡迎您在文章下方評論,與圍爐團隊和其他讀者交流討論
欲了解圍爐、閱讀更多文章,請關注本公眾號並在公眾號頁麵點擊相應菜單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