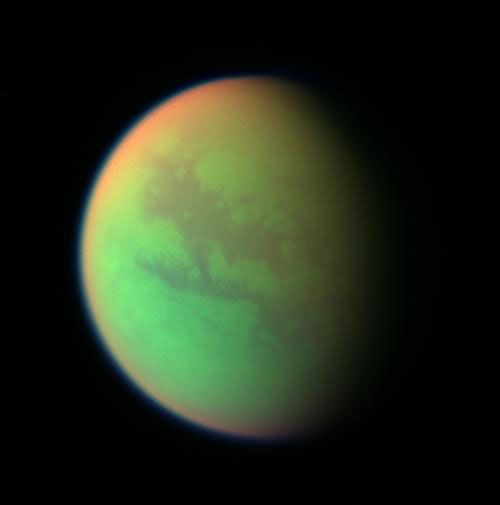邊境
上車前,其中一名乘客問這位載我們下山的「司機」:「欸!你成年了嗎?」這位臉色泛黃但是掛著笑容的藏民男孩表示肯定,儘管包含我在內的四位乘客都不相信他有駕照。「出發囉!」男孩坐在這輛灰塵遍佈的手動波箱汽車的駕駛座上,用手機播放起一些除了旋律之外只有他自己聽得懂的歌曲——除去那些藏文歌詞,那些乾癟的搖滾旋律似乎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
在車裡感受到的入夜後的原野和入夜前沒有太大分別,路不會因為黑暗平等地覆蓋大地而變得平整,更何況這裡並沒有路。乘客因為顛簸而劇烈搖晃。男孩也搖晃,但他播放的藏文搖滾樂又讓我覺得他自己是故意在搖晃,畢竟他看起來像是將這塊原野當成他的舞池。車的高燈(遠光燈)照亮了前方枯死的樹幹,他猛打方向盤躲閃,大聲唱著歌,但完全跟不上播放的音樂,好讓各位體驗他故意營造的刺激與混亂。「哎呀!天黑啦!找不著路啦!」他故意嚇唬我們,讓大家更相信他未成年。坐在前座的我隨口說了句:「那你按著那些輪胎印走就行。」
大約過了半小時,我抵達了山下的營地,男孩的音樂聲也隨我離開他的車而中止。那位在此等候多時的司機,真正的司機,抽著菸看著我朝他的車走來,笑著問我:「怎樣?你看那些藏民開車是不是不要命一樣?要是這裡發生交通事故了,警察過來,他們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我坐上了他寬敞整潔的車,他把車駛上剛好夠寬的柏油路,路燈的光在黑夜把整條路投射到司機的視野中,提示他僅能以規定的軌跡行駛。道路兩端像是邊境,司機被禁止闖進邊境之外的區域,那是光無法覆蓋的地方,意味著泥濘、違法甚至是生命危險。
司機全神貫注,車裏播放的是他選的「正常音樂」。即便有個別路段沒有路燈,車燈所照亮的地面依然有交通標線;沒有標線的地方,乘客至少知道那是條可以支撐汽車的穩固的路。無論如何,只要車在平穩行駛,只要窗外能看見任何人造物的跡象,乘客便可以沉浸在「實證主義的喜悅」中,尤其是那些剛從沒路的地方回到柏油路上的乘客。
從塔迪姆餐廳享用完美味的牛肉湯後,我起身前往獨立大街的盡頭,也就是塔克西姆廣場,路上經過了一個月前發生恐怖襲擊的地方。廣場中央是共和國紀念碑(Cumhuriyet Aniti),是隨著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而被澆鑄成實物的記憶。這個紀念碑上面有國父凱末爾、舉著旗幟的士兵、抱著嬰兒的婦女、馬匹等,外圍則是一個在世界各地都象徵獨立與勝利的拱門。2022年末的這次旅行中我造訪了不少紀念碑,這一個是雕刻得最複雜的。上面的每一個細節都被官方、遊客、學者等解讀了成千上萬次,例如凱末爾穿西裝意味著土耳其要成為現代化的共和國。這麼一看,土耳其語棄用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來拼寫這類事件也能和凱末爾穿西裝相關(修改拼寫方案也的確是凱末爾的傑作)。

這又是另一種「實證主義的喜悅」。歷史事件(記憶)被諸如凱末爾主義等意識形態統攝,然後以合乎邏輯的方式被輸出到公眾的意識中。這些記憶被仔細打磨,然後進入工業化流程,輸出成遊客可以拍攝甚至購買的產品:雕像、明信片、鑰匙扣、書籍、電影⋯⋯這些記憶產品對來訪者——不論她是當地居民還是外地遊客——發出警示:你只能以規定的方式記憶這些事件。凱末爾不會像末代蘇丹一樣再度穿上傳統服飾。落日之下,共和國紀念碑的輪廓便是記憶的邊境,任何超出邊境的行為皆被視為違法。
數日後我到訪的另一個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我多年前在書中讀到過。它位於塞爾維亞第三大城市尼什(Niš)郊外的一座山丘上,名為布班(Bubanj)。形態上,它是三個拳頭,分別代表二戰時在此地被殺害的兒童、女性和男性,共有近一萬名。相比伊斯坦堡的共和國紀念碑,布班要抽象得多,和南斯拉夫土地上所有紀念碑式建築一樣抽象。拳頭沒有清晰可見的手指,僅僅是幾個方塊和棱柱的拼接。站在這三個拳頭所組成的空間中,我不能像一眼認出凱末爾一樣認出哪個拳頭代表的是哪一類受害者。在這裏被呈現的二戰記憶,比先前在伊斯坦堡所接過來的土耳其建國記憶要模稜兩可數百倍。儘管在視覺上,布班的形狀要硬朗得多,也十分直白地傳達出戰爭的殘酷性和對建立新政權的決心,但是它的邊境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難以捉摸。

它不像南京大屠殺或是吐斯廉一般的博物館,赤裸裸地將死難者骸骨置於訪客眼前。了解布班所紀念的死者僅能依靠想像力。儘管我研究二戰的歷史,但我對塞爾維亞在二戰中的具體情形,或是八十年前發生在布班的事情毫不知情。對於毫無歷史知識的外國遊客而言,他們更無法想像這些拳頭的意味。因此,布班構建了相當虛弱的記憶邊境:它無法向我傳達記憶的細節,而僅能喚起我的想像力,促使我運用最低限度的道德自覺與死難者共情,而非在這陽光普照、青草遍地的公園裡大聲歡笑。但事實上,這個公園是尼什市民的郊遊地之一,在此野餐、遛狗甚至舉行音樂節都不會遭受任何譴責,畢竟模糊的記憶邊境削弱了它對觀者道德上的約束力。而在土耳其,侮辱國父可被檢控,共和國紀念碑因而無法容忍在它面前所表現的任何不莊重。
然而,我並非要在凱末爾和布班兩個紀念碑之間分出個好壞來——邊境的強弱與紀念碑的好壞,與後世所呈現的記憶之公正性毫無關係。無論是被路燈在視覺上串起來的山間小道,還是完美雕琢的凱末爾雕像,它們都指代一種被規訓的路徑。正如我總是從我居住的地方下斜坡走到上環站,按燈箱上的箭頭和文字安排自己的路徑,被規定好方向的扶手電梯帶到月台。陳如茵(Cheri Chan)的廣東話和英文廣播告訴我即將到站的列車終點站是柴灣(港島最東端),所以我相信上車後絕對不可能坐到堅尼地城(港島最西端)。站在月台上,面前隧道裡的黑暗被屏蔽門隔絕。門是由玻璃做的,所以反射著月台充足的燈光,讓人覺得面前的黑暗並不真實。廣播結束,進站的列車隨即把光灌進隧道裡。屏蔽門和車門同時打開,如同邊境長官查驗護照結束的瞬間,我被允許繼續剩餘的路徑。踏入列車,告別了穩固的混凝土月台,取而代之的是能將我送往既定目的地的大型現代工業產品。我如一顆滾動的磁鐵,那些箭頭、文字、軌跡、標線可供我吸附,又將我釋放,好讓我尋找下一個可以吸附的目標。
接過凱末爾相關的記憶後,我從塔克西姆廣場出發向西北方走去,經過一些無人的破敗街道,隨後下坡,想找一個地圖上標示的希臘正教會教堂。教堂在馬路對面,但似乎沒有地方能讓我穿過馬路,不要命的當地人趁著沒車的間隙闖過去,我沒有心思冒這樣的險。彼時夜幕低垂,而路燈還沒有開始工作,對面的教堂昏暗得像個廢墟。因此,過馬路的念頭被打消,我決定按原路返回塔克西姆廣場。我過於相信自己的方向感而沒有使用地圖,但明顯無法在半黑又雷同的骯髒街道中找回我來時的路,便開始隨心所欲地走。
清真寺門前的小廣場上,有數個穆斯林男孩騎著滑板車,橘色的燈光僅能照到廣場的一半。這一半和沒有光的一半之間涇渭分明,就像那些紀念碑嘗試通過規訓記憶來劃清的好與壞、正義與非正義、生與死的界線。這個街區陰暗又污穢,路邊烤肉店的店員一點都不像我在塔克西姆廣場附近看到的那些烤肉店店員,後者恨不得要把我抬進他的店裡。我抬頭一看,是敘利亞菜。那個店員坐在鎢絲燈下,面前是一些不知道有沒有烤熟的但是發黑的肉。我繼續走,蔬果店的老闆準備打烊,他站在街邊,一邊收拾,一邊轉過頭來打量著我這個不速之客,或者是不速之客脖子上掛的相機。野狗從我身邊經過,似乎它們也有既定的目的地,不像我一樣隨便闖進他者的空間。
回到旅館後,我上網查到這個空間名叫塔拉巴西(Tarlabaşı)——「伊斯坦堡最危險的地方」,「伊斯坦堡的貧民窟」,「搶劫、殺人、販毒、縱火」,「五歲孩子能拿著刀到處跑」,「你進來了,你不舒服,住在這裡的庫爾德人也不舒服」。似乎我從塔克西姆廣場往西北走便是非法越境——遊客區和非遊客區,安全區與非安全區之間的邊境,跨越者後果自負。而我的確這麼做了,那一個多小時裡的我得以不受規訓。
從伊斯坦堡往新德里的飛機上,我低頭看書。飛機緩慢地靠近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國邊境的交點,舷窗外詭異的光線讓人無法分清白天還是黑夜——分清了又何妨。我因此拒斥了一切可以提示我時間流逝之物,不再看手錶、手機、翼尖規律閃爍的燈光,允許書裡字詞嘗試建構的現象在腦海中成為真正的現象,縱使這些現象不合邏輯,不按時間排列,甚至不合道德。
那本書是鄂蘭寫的,但我沒有讀進去。她試圖讓我和我的同代人知道,人類處在困境中。她沒有提供任何的工具好讓我面對困境,而僅僅是描述了那個困境的輪廓。這個輪廓的內容很清晰,稍微了解過歷史的人就會知道她想說的是二戰、現代性和道德虛無主義。但她所構建的空間就像布班一樣,鮮明的形狀下潛藏著模糊的邊境,沒有提供實證主義喜悅的光明,也不知道邊境之外有什麼具體的危險。
我站在布班的三個拳頭下做了什麼?我直面他們,也僅能直面他們。我嘗試尋找這些在布班終止存在的個體的蛛絲馬跡,但是只有三個拳頭,三個被笨拙的混凝土塊代表的群體。他們是誰?她和他是誰?我在尋找的同時,也是在記憶;我在記憶的同時,也是在遺忘,畢竟記憶永遠伴隨著遺忘。所以,當人說「我是我所記得的」(I am what I remember)時,人也是其所遺忘的。
時隔半年,我在2023年11月21日再次開始寫作,完成了上面的這些內容。我已經快走到了這一歲的邊境。走過這條邊境之後,我會不會還是走過這條邊境之前的自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須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