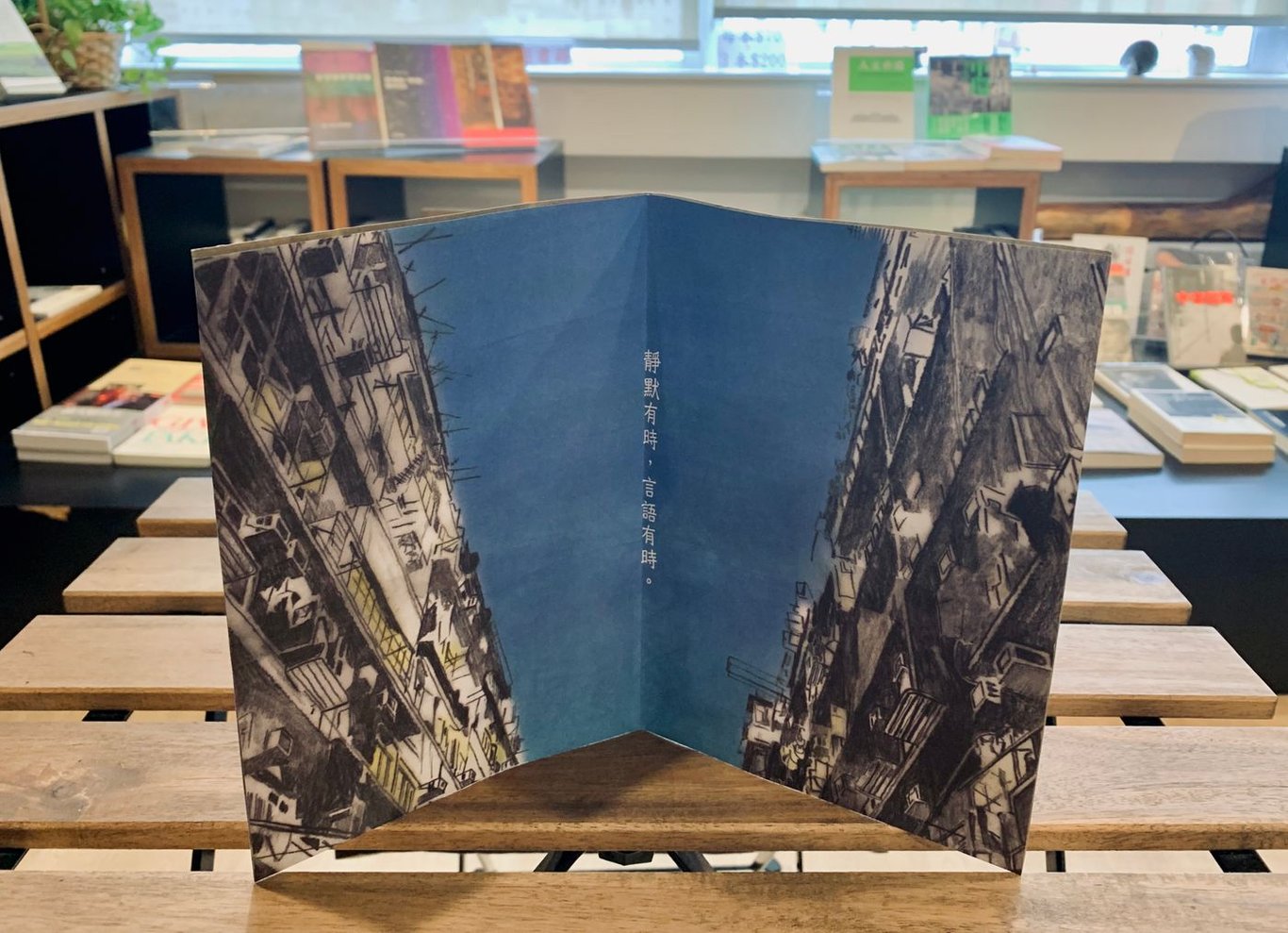一場香港的飯局,一次深圳的按摩 |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們價值何在?
數月前,應室友之約,赴了一場宴。
稱之為「宴」,大概是心中對其有種禮儀性的畏懼。室友稱其為一場非正式對話,是她的前同事騰出家中飯桌發起的晚餐交流。
任何人只需帶一個問題、120港幣便可參加,包飯、包交流、純英文。
01
我和室友遲到了小會兒,到場時,各員已就坐,圍繞在客廳旁的飯桌。
客廳是香港公寓中罕見的大,飯桌也是,刀叉碟子整齊擺好,西餐的架勢。

開飯後,自我介紹是基本的,西餐的禮儀也是必要的,菜放中間,咖喱雜菜、烤雞、色拉、芝士塊、水果......
自然不會像中餐,筷子勺子你夾我舀,菜碟被輪流端到每人面前,又輪流舀進自己的餐盤,雙手絕不需伸直向前,人絕不離桌。
然後開始隨意聊天,在場共9人,2男7女,都與女主人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兩個香港女生,剛剛大學畢業,國際學校英文教育背景;
一對剛訂婚的未婚夫婦,男方是英國白人,老師,女方是華裔,醫生;
一個挪威白人男子,外派到香港做亞洲區食品經銷;
一個菲律賓女子,國外呆了多年,從事金融科技;
然後便是從事教育咨詢的香港女主人和我室友,兩人均曾長期留學美國。

我是唯一一個純中文背景出身的人。說我不怯場,是假的。
雖然已經接觸過不同文化、不同膚色的人,也和其中一些成為知心朋友,但是我實在沒有把握能在這種陌生的多元環境下以一敵眾。
尤其你正佔一席,數雙眼睛盯著你,你便無事可逃,無話也要找話。
02
各人亦心有所懷,有備而來,打開話匣子自然很容易,從猜測職業聊到旅遊的國家、從不同地區美食聊到工作經歷。
菲女漫不經心又義憤填膺地抱怨道,澳大利亞的珀斯是她去過最髒亂的地方,引來香港女的共鳴。
英國男邊比劃邊優雅地介紹英國最好吃的芝士要怎麼個吃法,和挪威男相投甚歡。
氣氛看似十分融洽,但暗中波濤洶湧——至少在我心中。

當你不能自然成為談話中的焦點,那就必須用參與證明自己的存在,也就必須迎合他人的話語圈,而以英文為載體交流時,就意味著你要融入英語文化圈。
我不是英文母語、他們浸染的都是西方文化、為什麼他們去過那麼多國家?他們說的歌手、食物、地名怎麼我都不知道?
開始有無數螞蟻在爬上我的皮膚,撓著我的心,坐立不安,恨不得找個洞鑽進去,三個大紅字朝我步步逼來——「局外人」。
我大可以在這時給自己定性:你和他們不是一類人,他們比你見識得多太多——你夠不著。
我也可以硬憋一股氣:那我就要證明自己夠得著,不能讓他們小看我,挺直腰桿,擺也要擺出氣定神怡的樣子,裝也裝出我都聽得懂。
幸好螞蟻上臉時,有來自神的聲音潰退蟻軍:
「記住,你的篤定在哪裡。
是否一定要融入這場談話、成為主角才能帶給你安全感?是否要證明你「夠得著」,「稱得上」,你才有自信面對這群人?你如何看待他們?僅從他們的文化背景、社會階層、看似一應俱全、毫無瑕疵的外在表現?
不要忘記,你是誰,與你的出身無關,談吐無關,只與我怎麼看你有關。我看你是喜悅的,美的。」
神話語的力量,瞬間心安。
03
余下的整夜,心定神怡,好奇的便問出口,聽不懂的那就一笑而過,該分享的時候便分享,無須說話的時候就仔細聆聽。
是個新奇而美好的夜晚,沒有遺憾,也不至於印象深刻。
於是之後很久未再想起這件事,直到遇見按摩小哥002。
工作原因肩頸勞損得厲害,於是便跑去深圳找了家按摩店,給我按摩的是002號,他不肯道出自己的真實姓名,用他的話稱呼自己,單名兩個日。於是我且叫他002。
按摩時我趴著和他聊了起來,不是面對面眼神交流,似乎雙方說起話都更加敞亮。從養生聊起,我說到自己整天對著計算機敲鍵盤,落下一身疼。
002卻回了句:「你們都是文化人啊……」語氣中竟帶著感嘆,又隱約參雜著恭維。
我有些尷尬,受不起這稱號,連忙推托,便問起他的工作,他便開始像倒苦水一般吐出,打工仔一個,每月只休兩天假,除吃睡都在店裡,工資高低全靠客人多少,出多少力,掙多少錢。
「那你住哪兒?」我問道。
「老闆統一租了房子。不過我常住在店裡。」
「為什麼?」
「不用排隊洗澡啊。」他語氣故作輕鬆。
我聽著心中一陣難過,卻又不知如何回應,只在靜默中嘆息。

他看我沈默,便又問我在哪兒工作。
「香港。」我有些猶豫,怕他又將我以為成什麼。
「香港工資很高啊。聽說洗碗的都有上萬塊。」如果當時我能看見他的臉,那臉上應該是寫著羨慕,「我還沒去過香港……」
「是,但物價也很高。壓力大。」我說的是真心話。數字是冰冷的,而背後的人情冷暖又有誰知?
04
按到手臂時,他注意到我手腕上的橡皮環。
「信、愛、望。這是什麼意思?」
那是橡皮環上刻的字。我心中竊喜,說道:「我是基督徒,信、愛、望是聖經里的教導。你相信這個世上有神嗎?」
「鬼神之說嘛,半信半疑。我們農村很多的,信佛多。」
接著又胡亂繞了些,我想繼續引導話題,他似乎不太願提了:「我農村來的。不像你們城裡人,見識多。」
「不像」兩字變成硬塊,直賭我胸口,我竟不知如何回應,只是升起一股悲涼。悲涼中冒著煙氣,朦朧到感官深處,忽又清晰,看到了數月前坐在飯桌前慌亂的自己。
此時的他,和那時的我,是否在一瞬間有過情感的交匯?是否被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纏繞,任由它支配我們的言語、神態、動作,乃至認知?
看見面前的人像隔了一條銀河,那頭是「你們」,這頭是「我」。
忽的那銀河升到天上,「我」在地上仰望那難以企及的高度,也許一生無法跨越。
05
如果我尚且是002所說的「你們」,那當他遇上那些飯桌上談笑風生的人們,又會有何感想,作何反應?
如果我不認識神的話,我是否也會自覺將人分成三六九等,把自己放在002之上,飯桌男女之下,隨人而自傲或自卑?
而002呢?他不知是誰創造了他,他以為自己的價值在出身、見識、工資、教育,他也許掙扎一輩子都無法擺脫這些標籤,人前卑微,總漫不經心又深重感嘆地「你們啊……」

又或許有一天他衣錦還鄉,在他那被燈紅酒綠遺忘的農村老家,人們一口一個老闆,點頭哈腰,畢恭畢敬,他是否會揚起不屑一顧的嘴角,昂首看人低?
人若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為何而生,向何而死,多麼容易被這個世界的各類標籤所捆綁,多麼容易從他人表象去對照自己。
「人生而平等。」現今社會,誰人都能華麗麗地喊出這句口號,但要從生活去感知出來,行出來、信出來,需要多大的抵抗力。
06
又有多少人,憑自己一腔熱血抗爭,撞得頭破血流,撞至改朝換代,制度更易,只可惜,這種對完美人性的渴望從未實現。
從前有魯迅先生,窮盡一生,仍發出疑問:
「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麼?」
曾天真以為魯迅先生振聾發聵吶喊地只是一個朽去的時代,只是而今呢?
閏土與趙太爺仍遍地都是。

而我們,我,在何人面前是閏土?又在何人面前是趙太爺?
除非有一種超越人性本身的根,深深地扎進這個世界的本源,深深地知道,剝去這個世界強加給我們的一切外殼,我們到底是誰,到底是誰定義我們的價值,不隨任何情況而動搖。
這無法從任何被造物中找到答案,非金錢、非地位、非教育、非法律、非道德、非社會制度。
非從創造人的神來不可。
若非有一位超越人之上的造物主,在創世之初,造人之後,在赤裸而生、毫無價值的軀殼中吹了一口氣,視之甚好,那麼我們心中對完美人性的追求從何而來?
若非這位造物主看人人可愛,各有千秋,又是誰將「生而平等」的美好放在我們心中?

我們愛謙卑,不愛自大;
我們愛自信,不愛自卑;
我們愛平等,不愛等級。
只是人性的墮落,我們想象是如此完美,現實中卻如何也活不出來,就像那天上的銀河,再努力跳躍也夠不著。
這才需要造物主自己降尊,道成肉身,經歷最深的痛苦,遭人最狠的鄙視,卑到死蔭之地,人方才知,原來自己無需證明什麼,原來神已在這最低谷向人彰顯了最偉大的愛。
而這愛,願意傾盡宇宙之浩渺去贏得微如塵埃之人的愛,難道不足以證明我之為我的重要與確信?難道不足以讓我在此生扎根,不隨人之喜惡而搖曳浮沈?
07
忽而又想起那次「晚宴」,話題快收尾時,女主人主動提及自己的家庭經歷。
她一家人都是基督徒,只是弟弟出生即患「貓叫綜合症」,外貌異於常人,生活更無法自理,家中自是操碎了心,但當中也有太多感恩,弟弟如今已成人,至少能夠照顧自己。
她說話時語氣平靜而篤定,完全不是在吐苦水,亦非博同情。
這是在眾人談美食、侃電影、聊旅遊、吐槽工作之後,她有勇氣打破看似融洽的氣氛,異軍突起,在一眾熟悉或陌生的人面前敞開自己最脆弱的一面,非故作輕鬆,而是真實經歷過痛苦後的感激、站立、扎根。
她的信仰全寫在閃閃發光的眼睛中。美得不可勝收。
那一刻,是銀河落到了地上,流成清澈的泉水,無需你跨越,它只是緩慢趟到你心間。
那是耶穌的心腸。
寫於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