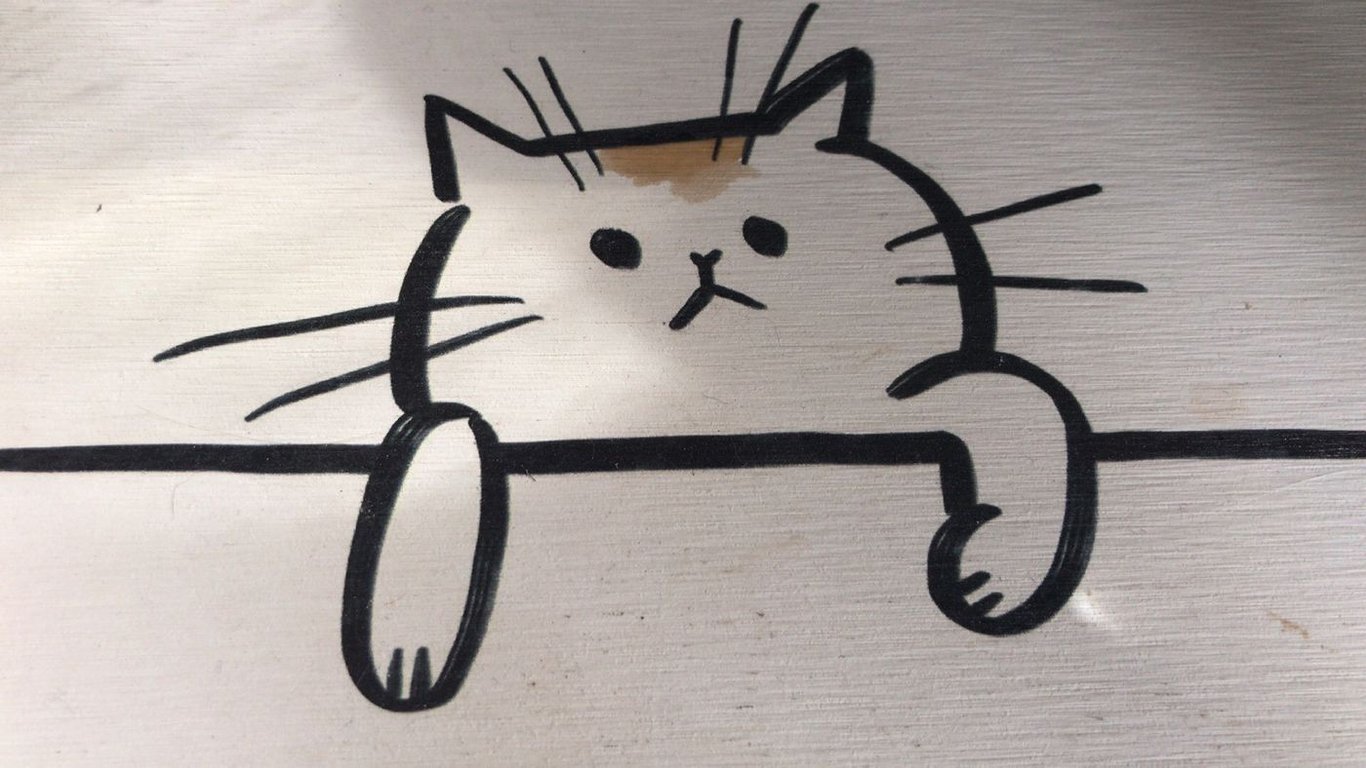鲜血流不进书房,死者已计入代价
1
余华写的《许三观卖血记》我差不多二十年前读的,几乎什么情节都记不得了,甚至忘了许三观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年代。
说不定,我还曾经张口就来跟人推荐说,这本小说讲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许三观卖血的故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记忆偏差,是因为八九十年代是我童年记忆的年代,那些年里,卖血挣钱的事就发生在身边,所谓“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蜷,五十大元。”这些往事以及后来河南爆发的艾滋病血祸,高耀洁医生调查过,南方周末报道过,阎连科小说写过,顾长卫电影拍过——大大小小的犯了违碍,如今都已成尘封文献,道不清说不明了。
我想说的是,这回重读《许三观卖血记》时,让我醒目到的不再是许三观的卖血,而是这么两句话:
这一天,毛▉席坐在书房的沙发上说:身边只留一个。于是三乐留在了父母身边,三乐十八岁时,中学毕业进了城里的机械厂。
这说的是上山下乡。许三观三个儿子,按照领袖的指示,可以留下一个。这是那时无数家庭面临的现实。电视剧《人世间》第一集讲的就是这种情况。那几年的历史,余华在小说里讲得非常简省,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场景描写,连年份都没有。翻天覆地的年代,那么多可怕的可笑的事情,他只写了一件事:说话。
2
先写的是许三观说话。他从街上回来,满肚子疑问,跟老婆说:
我这一路走过来,没看到几户人家屋里有人,全到街上去了。我这辈子没见过街上有这么多人,胳膊上都套着个红袖章,游行的、刷标语的、贴大字报的,大街的墙上全是大字报,一张一张往上贴,越贴越厚,那些墙壁都像是穿上棉袄了。我还见到了县长,那个大胖子山东人,从前可是城里最神气的人,我从前见到他时,他手里都端着一个茶杯,如今他手里提着个破脸盆,边敲边骂自己,骂自己的头是狗头,骂自己的腿是狗腿……
又说:
你知道吗?为什么工厂停工了、商店关门了、学校不上课、你也用不着去炸油条了?为什么有人被吊在了树上、有人被关进了牛棚、有人被活活打死?你知道吗?为什么毛▉席一说话,就有人把他的话编成了歌,就有人把他的话刷到了墙上、刷到了地上、刷到了汽车上和轮船上、床单上和枕巾上、杯子上和锅上,连厕所的墙上和痰盂上都有?
接着说:
文化大革命闹到今天,我有点明白过来了,什么叫▉▉▉▉?其实就是一个报私仇的时候,以前谁要是得罪了你,你就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说他是漏网地主也好,说他是反革命也好,怎么说都行。这年月法院没有了,警察也没有了,这年月最多的就是罪名,随便拿一个过来,写到大字报上,再贴出去,就用不着你自己动手了,别人会把他往死里整……这些日子,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是不是也找个仇人出来,写他一张大字报,报一下旧仇。我想来想去,竟然想不出一个仇人来,只有何小勇能算半个仇人,可那个王八蛋何小勇四年前就让卡车给撞死了。我许三观为人善良,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个仇人,这也好,我没有仇人,就不会有人来贴我的大字报。
这是小说视角和节奏有意思的地方。
许三观的一堆絮叨,把宏大叙事和历史总结给留白了。这个缫丝厂工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存、婚姻、绿帽子,儿子和面子,为了这些才值得去卖血,为了这些卖血而死也甘愿。这很日常,但绝不是琐事,而是惊心动魄的大事——普通人能把握的不过如此,哪有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一说?小说写的小民生存之道和日常苦乐,就是时代的真正主干,而惯常所谓的滚滚历史车轮都藏在小民的“说话”里。
按照小民说话的习惯,历史可以如下总结陈词:
后来,毛▉席说话了。毛主▉每天都在说话,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放下了手里的刀,手里的棍子。
毛主▉接着说:“要复课闹革命。”于是一乐、二乐、三乐背上书包去学校了,学校重新开始上课。
毛▉席又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许三观去丝厂上班,许玉兰每天早晨又去炸油条了,许玉兰的头发也越来越长,终于能够遮住耳朵了。
又过去了一些日子,毛▉席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举起右手向西一挥,对千百万的学生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一乐背上了铺盖卷,带着暖瓶和脸盆走在一支队伍的后面,这支队伍走在一面红旗的后面,走在队伍里的人都和一乐一样年轻,他们唱着歌,高高兴兴地走上了汽车,走上了轮船,向父母的眼泪挥手告别后,他们就去农村插队落户了。
再然后,就是毛▉席坐在书房沙发上说的那句话。这一句写得很厉害,厉害的地方就是“书房”和“沙发”的细节。书房和沙发是领袖思考和运筹帷幄的地方。人要怎么整,仗该怎么打,钢要怎么炼,挥挥手,闹运动,抽抽烟,搞生产,听听报告,世界大势尽在胸中。
在一芥小民想象力所及之处,世界运转的因果就是这个样子。于是毛坐在那儿说了一句话,许就要坐船去上海,沿途卖血救差点死在乡下的儿子。
从毛到许的因果,源自官僚系统巅峰到谷底的运行。官僚系统善于搞运动,就像一块大石头丢进水里,激起层层涟漪,波纹逐层扩大,同时不断有人学着丢下大大小小的石头,形成无数中心和层层涟漪。有时候,大石头激起的涟漪已经消失了,新的石头还在不断往水里丢。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波波不断。这就是运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台机器的运行需要在一波一波中不断进化升级,把不好用的零件替换掉,把马力不够的角落改装一下。
最重要的是,一波波的震慑力像输液一样渗透进人的毛细血管,一芥小民许三观由此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卖自己的血,做自己的主人。
许三观的鲜血再怎么流,也流不进领袖的书房里。
人的悲欢绝不相通。
兔死尚且狐悲,人何至于此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已经不是人了。我们常说害怕机器越来越像人,实际上真正要怕的是眼下的人越来越像机器:官僚系统这台机器的思维逻辑早就统治了日常生活,渗透每一个人的脑子里。
所谓官僚,不是古代说的官员或大人,那些至少还是人。古代皇帝是官员的头子,有时会好奇老百姓“何不食肉糜”,这么想,显然是在拿自己的日常和人民的生活做对比,是无知,是愚蠢,但至少还是从一个懂得饿了要吃东西的“人”嘴里说出的蠢话。
现代官僚系统,或科层制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不但不蠢,还过于精明。理性的第一步是抽象,用组织结构和流程把人抽象成为各司其职的符号。目中无人是系统运行的前提,越是组织庞大、权力集中的系统越要抽象。
首先是从身份和语言上就取消了具体个性,你不是张三李四,也不是父母儿女。所谓公私分明,你不要把情感带到工作里。其次是高度的切割,大小事务被理性的结构切割,分层,完整的意义被取消,人当然也被取消,不说别的,我们自己不也常以抽象的市民、用户、客户和消费者自居吗?否则你就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当然,很多时候你在五花八门的身份符号间切换,寻求“有关部门”解决问题,最后还是寸步难行。
因为官僚系统的所谓权责分明,会把你作为人要面临的具体处境切割成无意义的碎片。权责分明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相互推诿,理直气壮地推诿。
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诸如此类的通知:由于接到上级指示,如何如何如何,敬请配合。官僚结构的规则是向上级负有听从的义务,奉命形式意味着不用对选择和行为负责,相当于进入了安全的“代理状态”,可以没有道德和情感负担。
这就形成了官僚体制运行的最强逻辑:对事不对人。
年轻的时候,我一向把“对事不对人”的品质视为一种美德,讲道理不讲人情,有理性不胡搅蛮缠。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会在某些时候不说人话,用概念解释概念,用结论证明前提。这种时候,往往发生在我想拒绝某个人或想撇开某件事的时候。我把自己抽象为某个“规则”、“规定”或“现状”的服从者。
作为一个并没有书房和沙发的人,我却坐在了自己幻想出的某张沙发上,用屁股的位置来进行宏观局势的分析。
然后说,我也没办法啊,就是这样的。或者更可耻地说,想想大家的利益。但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我说的这个“大家”。
一旦越来越习惯作为机器零件的存在,即使再惊心动魄的血,看在眼里也不过是报表和曲线。人能抽象思考,才有了文明,但过度抽象也是让人失去人性的最佳方式。极度理性的精明算计,带来的接过是目中无人的非理性疯狂。
如果理性会让人冷眼旁观同类的死亡,这种理性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3
运动就像打仗,尤其是在机器的助力下,已然半机器的人服有意无意地从于超越个体意志的命令,高速运转,高度紧张,成为自己和他人眼中的符号——这并不一定会让人很难受,反而会觉得很安全。
当我盯着屏幕打游戏一样操作射杀工具,很难感觉到倒下去的是个人——和我一样又怎样,此刻我只是士兵。当我登录后台操作一下按钮,也很难想象的出某些素不相识的人会遭受到什么。当我拒绝一个痛苦的人时,只需要加一句按照上级指示就能心安理得了。
听多了官话,就自然学会了打官腔,常年官僚体制的思维渗透,终于让我们养成了官僚体质,习惯服从,善于响应,仿佛随时都能上前线。
去年写一篇关于“服从”的文章,讲到一九七二年的一个科学实验。忍不住要重提一遍。
实验者以科研的名义要求被试者电击小狗。过程中被试者会听到或看到小狗嚎叫与奔跑(暂且不提实验本身的伦理问题)。结果,二十六个受试者中的二十人都自始至终服从指令,将电击加到了最高级别。这些人有的表现很痛苦,有的忍不住哭泣,有的很犹疑,但无一不服从。
这个电击实验,是对著名的米尔格拉姆电击服从实验的复制。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米尔格拉姆陆续找不同身份、职业、性别和年龄的1000左右受试者进行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常生活中负责且正直的普通人,被权威引诱到陷阱中,完全压制了自己的感知,不加批判地接受主试(权威)对情境的定义,做出了可怕的行为。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代理状态”。
同样,其他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显示,没有任何权威的人,也可能会对他人行为产生影响。所谓服从,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源于个体动机,而是源于社会等级更高位置者的动机体系——这不正是官僚体质者脑中的抽象等级世界吗?
或许,希望官僚体质者听懂人话和说人话是一种奢望和苛刻。他们身居高位,坐在沙发上点兵点将,不免有人混淆其视听,堵塞其耳目。所以你说外面是雨雪风霜,他看着屏幕说不正春暖花开吗?他们念讲稿,发通告,并不对言行负责,又不是他们想说想发。逼他们直面现实,难免令他们如坠云雾,不说人话,答非所问,像磁头生锈的复读机。
不能说人话的时候说了人话,就是搞错了形势。那将意味着把自己当做具体的人,要面对常识和人性,要有痛感,有耻辱感,要负责,免不了产生共情。那将是何等可怕?——脸面将荡然无存,局面将难以收拾,谣言四起,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啊。
只有说好空话和搞好形式能救他们,让机器之心运转良好地失去共情能力,不至于崩溃,不至于让无用的人性浮现。
4
许三观就懂这个。
他虽然看洞悉了真相,处处小心翼翼,但终究没逃过运动,老婆被人贴了大字报,挂着牌子在街上挨批。许三观去送饭,碰见一个人。那人问他,你家开过批斗会吗?
许三观说,我老婆在好多地方都批斗过了。学校、工厂、街上……他掰着指头数。
那人说,家里也要批斗。
这人是谁?什么意思?许三观摸不着头脑。小说这么写:
许三观不认识这个人,看到他的胳膊上也没有戴红袖章,他摸不准这个人的来历,可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他不敢不听,所以他对许玉兰说:“别人都盯着我们呢,都开口问我了,在家里也要开你的批斗会,不开不行了。”
虽然没有红袖章,但不敢不听。群众的眼睛当然是雪亮的,在任何时代都雪亮。
于是,许三观在家开批斗会批斗老婆。
这天傍晚,许三观把一乐、二乐、三乐叫过来,对他们说:“今天,我们家里要开一个批斗会,批斗谁呢?就是批斗许玉兰。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叫她许玉兰,别叫她妈,因为这是批斗会,开完了批斗会,你们才可以叫她妈。”
许三观无师自通地应对了一芥小民在运动中的尴尬处境。这是他的生存智慧,也是最深的黑色恐怖。主动进入代理状态,切割亲人关系,运用另一套说话方式展开批判。
这种事我想也不敢想。
当然,时代的车轮已滚滚而过,许三观经历的事我只能说不会再发生了。但同样不太敢想的还有一种情况:稀里糊涂地成了机器运转的代价。
一如许三观,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于我们就是天大的事。一芥小民有喜怒哀乐,有清晰的痛感,但凡回不了家、睡不了觉、和猫猫狗狗分离都可能惶恐无措,更何况生死关头求医无门,那是怎样的绝望和恐惧?
我想起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同时期作品《活着》里写富贵的儿子有庆如何死去:
验到有庆血型才对上了,我儿子高兴得脸都涨红了,他跑到门口对外面的人叫道:
“要抽我的血啦。”
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他还硬挺着不说,后来连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着说:
“我头晕。”
抽血的人对他说:
“抽血都头晕。”
那时候有庆已经不行了,可出来个医生说血还不够用。抽血的是个乌龟王八蛋,把我儿子的血差不多都抽干了。有庆嘴唇都青了,他还不住手,等到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那人才慌了,去叫来医生,医生蹲在地上拿听筒听了听说:
“心跳都没了。”
医生也没怎么当回事,只是骂了一声抽血的:
“你真是胡闹。”
注:封面图为《许三观卖血记》改编的韩国电影,2015年上映,导演是河正宇。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