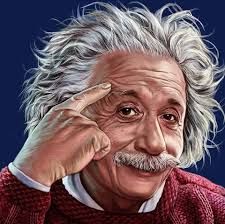壹個中國籍傭人的自白

我出生在1988年,那壹年村子裏的大事之壹,就是河對面的臺氏正在建新房。我是在今天,三十二歲的時候,徹底意識到,我並非家裏人,而是家裏的傭人之壹。這是我人生裏最大的大事之壹了。
意識到我的傭人身份之後,我決心不再當傭人。
我可能要去當流浪漢,而且我發現從我家出走的流浪漢特別多,多到數不完。原因倒也簡單,我家本來就是大家子,家裏人 — — 或者叫主人 — — 有幾千幾萬人吧,傭人數量更是萬億人。
但如果流不成浪,我估計要繼續回家做工,這跟我說的不再當傭人並不矛盾。因為當我內心明了自己不是傭人之後,壹切就變了。
我可以繼續介紹下我家的屋子,屋子很大,可做的工種也很多,可以去屋頂鋪磚,可以去院子掃地,可以去廁所倒大糞,可以去屋後通陰溝,可以去廚房燒火,可以去地裏薅草……所以也可以睡在屋頂,院子,廁所,屋後根,廚房……還是很自由的,這也我當時也覺得自己就是屋子的主人之壹,畢竟這個屋子除了頂樓房間不能去,其他地方想去哪兒去哪兒,想做啥工做啥工。
我們做工的時候,大喇叭還放著昂揚的音樂,全天無休,所以不管做啥都快活。而且我們還有由對比而來的歡樂,我稱之為”傭人的快樂”,就是我們有諸多可以驕傲自豪的東西,比如我家裏的地板塊數數最多;客廳的煙灰缸最漂亮;我們壹年積下的生物肥(人畜的糞便)最多;比如我家安的攝像頭總數最多,甚至人均數量也最多;比如我們家最早在廁所用上智能無線出紙機 — — 只要用手機對著機器掃二維碼,就可以出兩片衛生紙。據說現在已經連刷二維碼都省去了,直接站著刷臉即可。
就說壹點,我們的樓是村裏最高的,高到什麽程度?上面看不見下面,下面也看不見上面。我們跟上面匯報事情的時候得用對講機。
但是,在這次出門之前,我已經漸漸覺得這些”傭人的快樂”不足以讓我快樂了,因為我的傭人同事們壹遍遍為諸如”我們家壹年用的衛生紙可以排成四百米高的金字塔,全村第壹”興奮自豪的時候,我看到他們邊說邊用衣袖擦鼻涕,畢竟平均每人分到的衛生紙其實只有2.67片。
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但我不知道出問題在哪兒。
再比如,我們家的廚房雖然鋪著進口的意大利瓷磚,但是我們用的竈還是最原始的土竈,燒的是柴和看起來像柴的長條東西,點火的打火機倒是很高級,所以每次給竈引火都要四十分鐘,因為煙熏眼睛難受,所以要五十四個人輪流點火。
再比如,我們的廁所雖然有智能自動出紙機,但是我家的如廁文化是便後不用沖廁所,沖廁所是有專人負責的,由於我家主人很多,傭人數更多,所以,沖廁專員的數量也是極多的,還安排三班倒和KPI考勤。
我想知道為什麽,我想尋求根本的答案。比如廚房的土竈,顯然是落後於潮流的,村子裏基本都用上煤氣竈了,所以我28歲的時候第壹次出門,去左邊的寨子學習煤氣竈。
而且很重要的壹個原因是,家裏天天吃的所謂”自家特色”的菜,已經讓我反感到吐了,我估計這是我壹直身體苗條的原因。
在外面的這些日子,最快樂的是可以看到我家的全貌,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樓層(之前沒出門時,很難看到其他樓層),能看到發生的許多事情,但這些也正是沒意思的事情,無非是哪裏起火,哪裏爆炸,哪裏停工,哪裏在打架,哪裏在強奸,哪裏在塗抹墻上的血跡罷了。
比如,經常會有人從高樓層被扔下,像扔垃圾壹樣,如果還是活人,壹般會沿著管子通到廁所,讓其徹底搞臭;如果已死,就丟到通向廚房的管子裏,落進柴火堆裏,當柴燒掉。廚房的同事們幾乎不大可能註意到,因為生活是如此繁忙,而又無聊,大家無論是燒火的,下廚的,切肉的,倒泔水的,做西式糕點的,都不會註意到這屍體落地時的悶壹聲響,更何況大喇叭裏播放的昂揚的歌聲從不停歇。
我有時被這些事件所震動,就忍不住地遠遠地對在底層工作著的眾朋友說:
“妳對我們的家,有參與感麽?妳不覺得這個家很畸形麽?”
但我瞬間又改口說:
“妳對藍天白雲,壹樣喜歡麽?妳不覺得這大地很美麗麽?”
日子就這樣過去,壹邊學習煤氣竈技術,壹邊想著他們是怎樣巧妙地讓我們誤以為我們不是傭人而是主人等問題。直到前幾天的壹件事,讓我出離憤怒,讓我明明白白地看到自己是怎樣被欺騙。我想,他們能用如此拙劣的謊言來欺騙我們,說明我們根本不是”家人”,既然我們不是”家人”,更不是”客人”,又生活在這個家裏,生老病死,那麽只能說明我們是傭人。
翻看我們的家譜,往前幾千代我們便是這樣的身份了,我原本以為我們是二十壹世紀的村民,已經用上了智能出手紙機了,舊的命運應該終結了,但顯然我太幼稚。
總之,在32歲做了這個決定,我就知道,我將註定流浪,或者也會很快回來,如果無處容身的話,而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又都在這裏,世代為傭,這是我的家,我們的家。
但我真心盼望我們都不再只是傭人,都能以主人(即能對家裏的事情壹起負責)的身份住進這所巨大的房子裏,就像我出生的那年 — — 1988年 — — 河對面的那家人壹樣,我相信那壹天壹定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