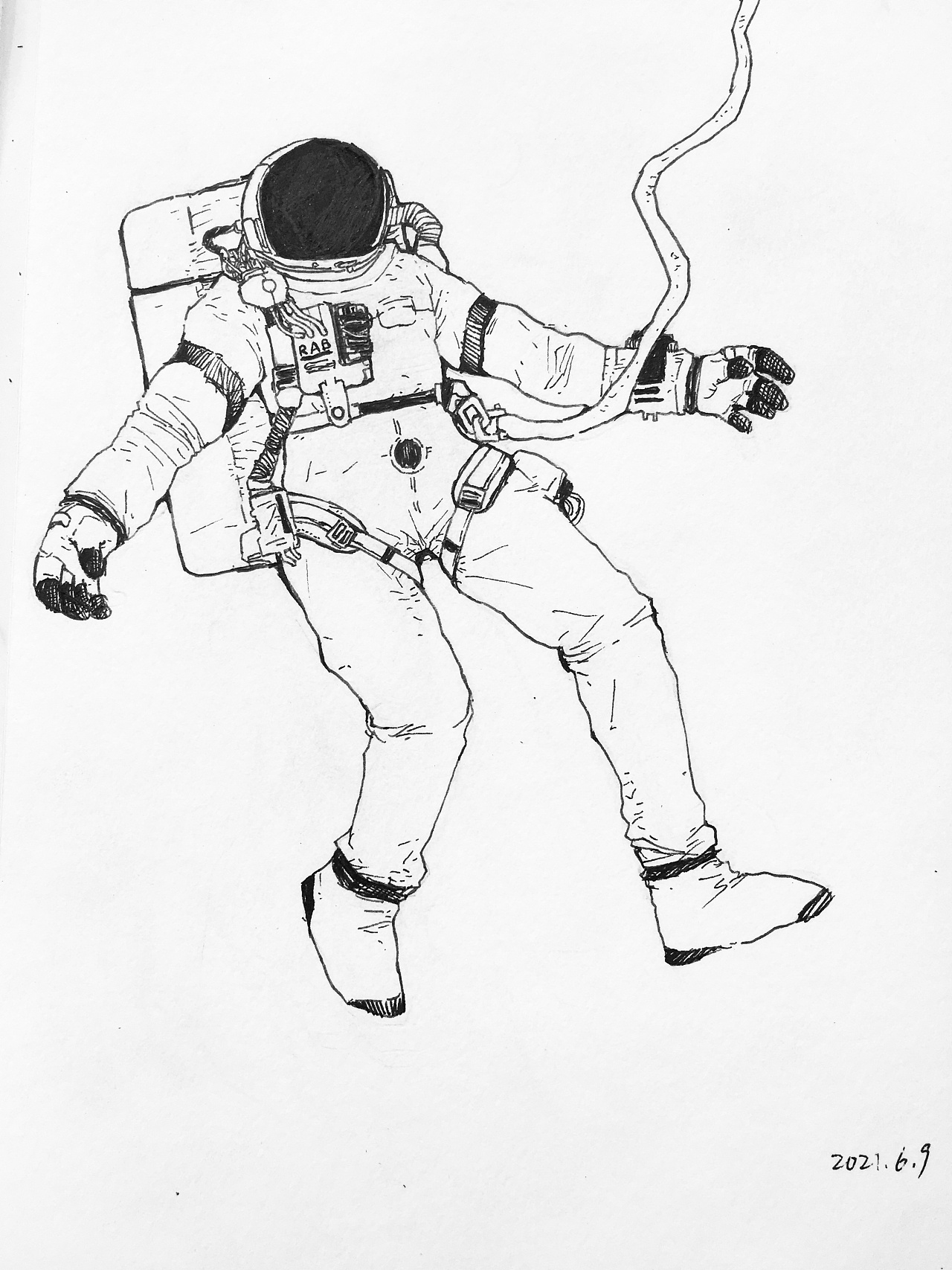隨筆|當「事件」墜落
前天看完了鐘曉陽的《哀傷紀》。
找到這本書的機緣是,被我借出了小半年的唐諾《求劍》,斷斷續續把閱讀的戰線拉得極長(看唐諾的書像和老朋友嘮嗑,時間總是無所謂)。前幾日讀到其中一篇文章,即是寫《哀傷紀》。引致我立刻奔波去大學圖書館尋覓此書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此書的由來——《哀傷紀》的第一章《哀歌》,原為1986年出版的短篇,2014年再版時,鐘曉陽為其寫序,誰料竟然交出五萬字的小說,是為第二章《哀傷紀》;其二,若有熟知唐諾的朋友便知道,他寫起喜歡的書來,語調總是動人到彷彿不去找來看就好對不起你手上捧著的這本書。在此不妨抄錄幾句:
我當時最接近的閱讀經驗是讀《楚辭》裡的屈原。⋯⋯它是一次竭盡所能的詢問,問情為何物。⋯⋯這樣的旅程,最終一定會上達神前。
(抄唐諾的文字一定要節制,否則極容易不小心就費去七八百字。)
因此去看了。
鐘曉陽的文字是白話文,但是有詩的節奏,讓我想起海浪。我是那種會在大太陽底的西九龍海岸和鵝鑾鼻山徑定神凝視海岸邊懸崖下浪花一褶一褶拍來而大半天不肯挪一步的人。而《哀傷紀》根本就是一片海洋。由遠方眺望的讀者大概只得見其海水之蔚藍悠遠和浪潮之起息行止,然而邁入海中,才可領會浪頭撞擊時纏繞在腿腳上的奇異力道。
而也許因為我們都是那個求天問地不得回音的詢問者,身在同一片海洋,因而低頭時我看不到遠眺者眼中的蔚藍,只留意到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海浪移動時在水面留下的白色足跡、幾粒黑色的沙子順從地划過腳趾、響亮海浪轟鳴中細微錯位的節拍。
書中最驚心動魄地刻在腦海裡的,是女主角回到舊居,和老朋友一起細數從前鄰居的後來遭遇的那一小段文字。「那個從前⋯⋯的人,後來居然⋯⋯」,他們敘舊時用的是這樣很老套的句式。然而讀到那裡時,我卻像是第一次繞到熟悉事物的背面,被全然不同的景象所擊倒。從前因過分精微而不願也無法解釋的蜷縮著的思緒,在那一刻奇蹟般舒展開來。
我想起冬有一天問過我而我答不出的話:為什麼覺得「不敢」愛?
「那個從前⋯⋯的人,後來居然⋯⋯。」我在害怕那個「居然」。那些不被人理解的人生突轉,和觀者之間橫亙著的恐怕不只是時間的空白,還有一些巨大而超出理解範圍的、爆炸光芒不可逼視的「事件」:一場死亡(及其遺物)、一場愛情(及其開始與結束)或者一場相遇(及其遺憾)云云。
現在輪到我和冬了。我察覺到它緩慢下墜時產生的晃動,如同在暴雨前嗅到悶濕的泥土氣味。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將經歷的「突轉」的方向,可光是軌道變向時的咔嗒聲就足夠叫人膽顫心驚。親密關係的情感在這些時刻突然沈重得無以復加,我們孱弱的、初生的手臂幾乎無法支撐它的重量。我編造出無數「那個從前⋯⋯的人,後來居然⋯⋯」的句子,可是沒有哪一種結局可以削減這種惶恐半分。幸福和恐懼原是一體兩面,正如生和死大概是同一位神明掌管。
某日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和冬在北京的照片,然而收到點讚時卻感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的孤獨。我慢慢變得不願也不能解釋,不想因話語和文字的無能而損失掉回憶的半分細節。霎時間整個世界都成了我們二人之間的秘密。
於是我們最終也變成了「怪物」。因執著於自己身上的掙扎而無法與世界目光相容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