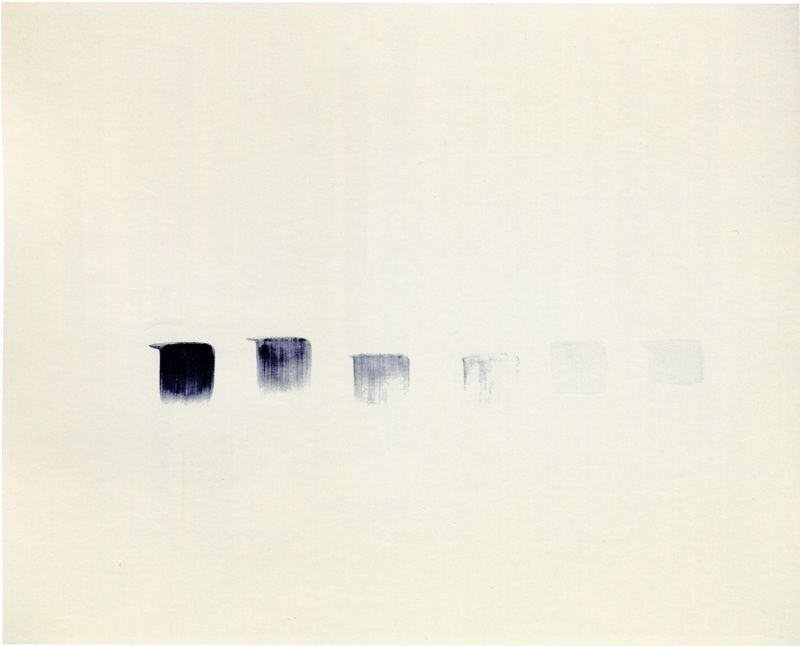提問之後,返家的旅程才正開始?《餐桌上的神話學》
戲劇 2019–03–11

演出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時間 2019/03/01 19:30
地點 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文 — — 羅倩
《餐桌上的神話學》(以下簡稱《餐桌》)從舞台上的餐桌聚會中進行《奧德賽》的排演開始,綿延出表演與表演者自身生命經驗的討論,同時也將自身放入區域性視角 — — 藉亞洲的地理位置來對神話故事《奧德賽》進行反身性詰問。以表演者稱之,是因為演出較少涉及虛構性的「複雜扮演」(complex acting),從多數表演者以自我敘事的角度來看,比較是介於「簡單扮演」(simple acting)和「非扮演」(not-acting)之間。【1】透過七位表演者共同創作(台灣、南韓、日本、菲律賓、印度),演出聚焦與連貫在七個主題上:英雄、女性、他者、變形、政治、神祇、家園。以接力或協力的方式在舞台上進行自我敘事,而奧德修斯作為神話中無法被控制的人類,同時也是位Nobody。【2】
Nobody作為《餐桌》的主要命題,在結尾以一連串為他者發聲敘事的方式說出。Nobody是嘲諷式的雙關語,「沒有人/無名之輩」是作為個體的無名之輩;同時也是「所有人」的群體指稱,例如「沒有人是局外人」;「沒有人」也指稱了在空間中的無人、無主體狀態,它排除了人的存在。在這裡恰恰是談及了一種字詞上可能的弔詭,例如:在我控訴的同時,我既無法被人指認,控訴的對象也同時消隱。無所不在卻又看不見,只因為這樣的控訴無法指認出所有人中的特定一位。作為受害者,加害者藏匿在權力背後的無名狀態。看不見也難以指認,卻能以整體性的具體壓力感受其無形的存在。
我以為,在表演者眾多自我言說的生命經驗中,在日常生活器物的使用與聲響中,在罐頭、食物、電器、餐具的搬演與碰撞中,眾多物件代理了區域、國族、想像的認同與投射;在多個何謂亞洲的小我敘事中,如何透過在日常的餐桌食景,讓觀眾想像自身,即是超越餐桌之上與之外的,身處與認同的「亞洲」自身究竟為何?
《餐桌》給觀眾的感受是身體性的、物件性的以及影像性的。餐桌上被重重敲打噴出的罐頭醬汁好像是打在觀眾身上一樣。那些表演者喃喃自語的敘事好像也是我們身體經驗的一部分──那個應該熟悉卻常被日常生活物件表象掩蓋的自己。
這些關於自身困境的進行式,當它以全英語被展演在跨國家的表演者的舞台上,好像拿著擴音機清楚明晰的在對我們進行提問一樣。當表演者說著台灣究竟屬於東亞還是東南亞,還是以上皆非?我們是否是China的一部分?(以Republic of China或Chinese Taipei來說,這些因歷史所留著的字詞)究竟是China還是Taiwan?是富裕的亞洲還是窮困的亞洲?時尚潮流的亞洲還是土地與工業污染嚴重的亞洲?
在舞台設計與表現手法的呈現上,就近期曾看過演出的經驗,觀看《餐桌》過程中浮現了出許多演出的片段殘影(afterimage),節奏感的外溢殘影如眾人聚在桌前使用物件,恍如再拒劇團2018「白晝之夜」《年度考核協奏》,當然《年度考核協奏》相對來講更具結構與節奏的嚴謹度。
即時投影的外溢殘影是高雄衛武營開幕季二十四小時連續演出的《The Second Woman》(2018),透過影像讓演員朱芷瑩更細微的臉部與肢體表情被放大,加強感官接受的映像。《餐桌》的影像則是透過大螢幕的影像投放,讓觀者有更多觀看舞台上表演者肢體與動作的其他視角,影像甚至可以作為敘事主體的補充功能。
《餐桌》在建構現場與影像的安排上成了相互補充的關係:現場在下,影像在上。【3】兩者都擁有劇場空間中的現場性,當然影像中藏有幾個已預錄的「過去」片段影像(如泳池那段)形成不同影像觀看的差異。就「過去」與「現在」兩種不同時間點中共同展現在劇場空間中的角度來看,也可以進一步追問:演出一開始,表演者在排練「過去」的《奧德賽》,同時自我詰問「現在」在亞洲排練古希臘文明的史詩神話《奧德賽》的意義是什麼?在演展各自生命經驗的自我敘說的同時,隱含與凸顯了跨亞洲不同文化與不同藝文工作者的差異性。其實與《奧德賽》文本跨時空「對話」的方式已經展開了,作品所呈現出的時間層次也是相當豐富的。
除了即時投影,《餐桌》中也可以看到影像的表演性,如在每個篇章段落投影的字卡(Intertitles)上直接進行影像書寫與塗改的趣味。【4】由於節目單上未提供七位表演者個人與如何投入集體創作的足夠資料,也許那位一直坐在入口處,在餐桌周圍拿著攝影機遊走對焦,協助Google翻譯何謂「亞洲的現代性?」與提示字卡的工作人員,也該視為其中一位在舞台上的接近「隱形的他者」的表演者吧。
最後,就意義的層面上,借用李維史陀說法:「我認為:『沒有秩序的意義』是絕對無法想像的。在語意學裡有件很詭異的事情,那就是:『意義』(meaning)這個字很可能是整套語言裡面,意義最難以尋獲的一個詞。『意思是』(to meaning)究竟是什麼意思?我覺得我們可以給的唯一答案,似乎是:『意思是』代表一種能把任何資料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能力。……在不同層次上用別的文字重新說出來。」【5】《餐桌》擬人化了許多生活當中的物件,並賦予什麼國家與什麼樣的人的想像。作品說了很多,但就「意義」與「意思是」的層次上或許仍舊是一個無法有明確「意義」的提問?(至少就導演觀點來看)如同表演者個人經驗分享是否足以代表一種區域或國家現狀的症狀(symptom)?或僅可視為一個全體中被說出口且被觀眾接收到的抽樣樣本(sample)?
或許這是《餐桌》聰明與狡黠之處,以海神波賽頓(Poseidon)作為最後章節。在當代頻繁與密集的跨文化交流的對話與探索下,《餐桌》有機會從表演者之口表述眾多個人經驗,物件也已擬人化的轉譯,但關於亞洲本身的問題與究竟如何各自找到回家的路?似乎找回家(意義)的路徑才正要開始,演出卻已來到尾聲,戛然而止在那片掩蓋一切漂蕩的海。
註釋
1、漢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在《後戲劇劇場》中以展演藝術的角度視之,提及了Michael Kirby三種扮演的區分方式,雷曼認為「展演藝術和後戲劇劇場一樣,重要的是一種現場性(liveness),是具有挑釁性的人的存現,而不是要扮演角色。」漢斯–蒂斯‧雷曼,李亦男譯:《後戲劇劇場》(2版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74–175。
2、在此篇文章中,由於筆者較無法掌握《餐桌上的神話學》,是導演Baboo對於美國劇作家Mary Zimmerman改寫的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再改編,或是對荷馬史詩《奧德賽》概念的直接挪用,但一定程度受到參與紐約林肯中心的導演工作坊的啟發,再交由演員集體創作發想?編劇何應權參與的角色為何在節目單也沒有特別說明,較難掌握資訊,因此略過版本差異與演出結構的討論。
3、就影像是對於現場的補充來說,舞台餐桌兩側所安排的觀眾席,觀眾不論是坐在哪一排,由於實驗劇場座位排數少,觀看的整體視點的差異性是較低的。
4、字卡章節(CHAPTER)分別為:1. TELEMACHUS、2. PENELOPE、3. CIRCE、4. CYCLOPS、5. ATHENA、6. NOBODY、7. POSEIDON。
5、李維史陀著,楊德睿譯:〈神話與科學的邂逅〉,《神話與意義》,台北:麥田,2005年,頁31–32。
2019–03–11首發於表演藝術評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