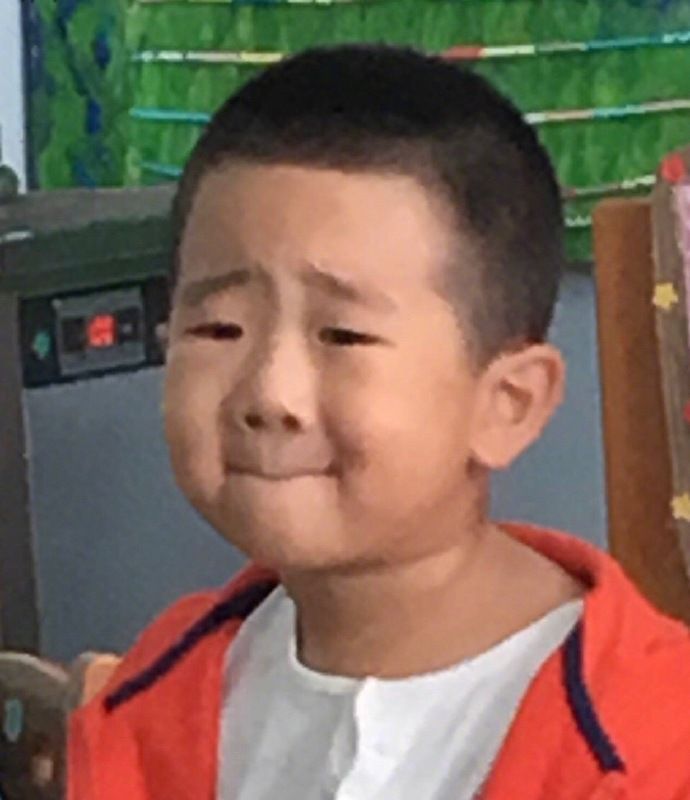碎念絮語(一)

Hello Matters。好久不見。
上一次寫下這行文字,居然是21年的3月。近四年過去了,一個大學生都即將步入工作崗位了(如果找得到的話)。再次登入,發現20年4月的一篇文章被封存——彼時中國教育部暫停陸生赴台升學,直至今天。不曉得為什麼這篇有關「政治綁架教育」的文章會被封存,難道是滲透,反正也link不到了,曾經的無知和「輕狂」就隨他去吧。
不對,怎麼能「隨他去」呢。
說回四年,這四年於我而言是劇烈的。失去了陸生的身份,離開了精神的故鄉,回歸了戶籍的在地,開始了講台的生涯。不管是COVID-19的戛然而止還是情感狀態的狗血淋頭,從大環境到小內心,這四年於我而言是劇烈的。當然目前並無意細數這四年經歷的時刻,也無法複述出這四年發生的故事。一方面這確實不該是我三言兩語就能夠說清道明的過程,另一方面,我自覺以現在的文字能力絕對只能建構起空洞乏味的內容。一筆帶過的說法是,最初的焦頭爛額被如今的油嘴滑舌(沒有)取代,好像一切都在變好。但我似乎又不甘心就這樣「步上正軌」,我擔心自己猶豫,我害怕自己麻木。
我變得割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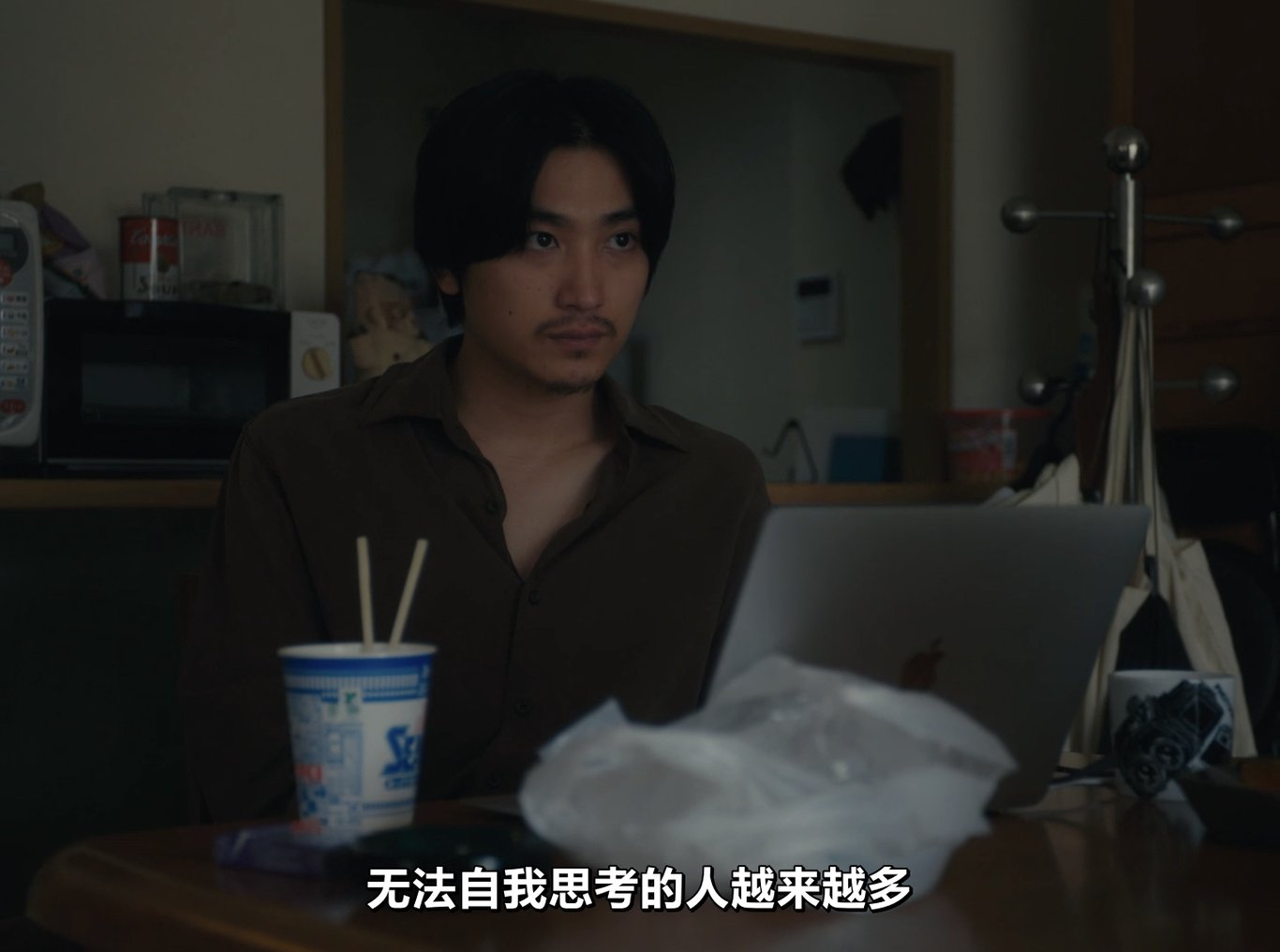
當然可以直接把皮球推脫給所謂的「大時代背景」。數位化的衝擊、短影音的裹挾,大數據的替代……「無法自我思考的人越來越多」。雖然我不曾有「刷短視頻」的不良嗜好,但也自知逐步陷入短平快的享樂主義旋渦。嘗試反抗。從被噤聲的朋友圈,到被舉報的讀書會,包括兩極分化的課堂。
我想我是一個需要輸出的人。誠如成舍我老先生所言,「我要說話」。我承認我喜歡「在發聲」的感覺,但四年下來的持續性輸出(暫且不論質量)終於換來了一種無力感。一方面雖然我愈發地知道沒有辦法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滿足所有人,但偶有的零星反饋難免讓我開始自我懷疑——真的有必要嗎?另一方面,最近在和朋友的對話中突然驚覺自己「缺少了輸入和成長」。是的,半桶水終究有晃蕩完的那一天。我有點慌了。我開始油嘴滑舌(好吧可能有),我開始打馬虎眼,我開始胡言亂語。直至現在我開始推課,冠冕堂皇地說這門課我不上了,因為自己「太累了」你們「聽不懂」這樣「沒必要」。但我知道,這只是在逃避。
我需要調整。被唾棄的「大時代背景」揮鞭讓我心中的人格馬車分道揚鑣。如果Freud是對的的話,那我需要把割裂的「自我」一點點的建構回來。我開始嘗試重新培養觀影的習慣。在我的認知裡,電影是導演價值觀的輸出,相應的看電影就是一個被輸入的過程,這點上包括音樂和文字也是一樣。於是盡可能的看電影、跑影展,樂不思蜀,個中故事的沉醉與沉痛,又是另一個議題了。不管怎樣,這應該是個好的開始。

一場電影後回看這些文字的時候發現,句句都圍繞「我」為主語進行陳述。想起曾經被人指責過度自我為中心,用詞好像是NPD(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自戀型人格障礙)。再看確實感覺好似一個剛學英文的一歲小孩,只會用「I」表達內心的訴求。但轉念又想,這些是關於我的內容,或許這才是我又開始試著寫長文的目的,或者說於我自己而言的價值和意義。
是的,好消息是我又開始試著寫「長文」了,雖然這些文字簡短得不值一提。但歸根結底這些文字不是那種應付檢查、堆砌空洞的書面工作,而是可能得以照映自我、建構「真實」的內心自反。一些雜緒、一些碎念,一些自言、一些絮語。希望能夠堅持下去。
對了,除了前面提到直至今天仍被禁止的赴台升學之外,限制還涉及到了抵台旅遊等方面。但兩岸應該正在努力恢復往來。大陸已經有不少高校送出學生赴台交換學習,且恢復了福建居民赴金門馬祖旅遊。似乎離「回家」的日子越來越近了,雖然我再也無法——從來無法——真正意義上的回到那裡。

願一切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