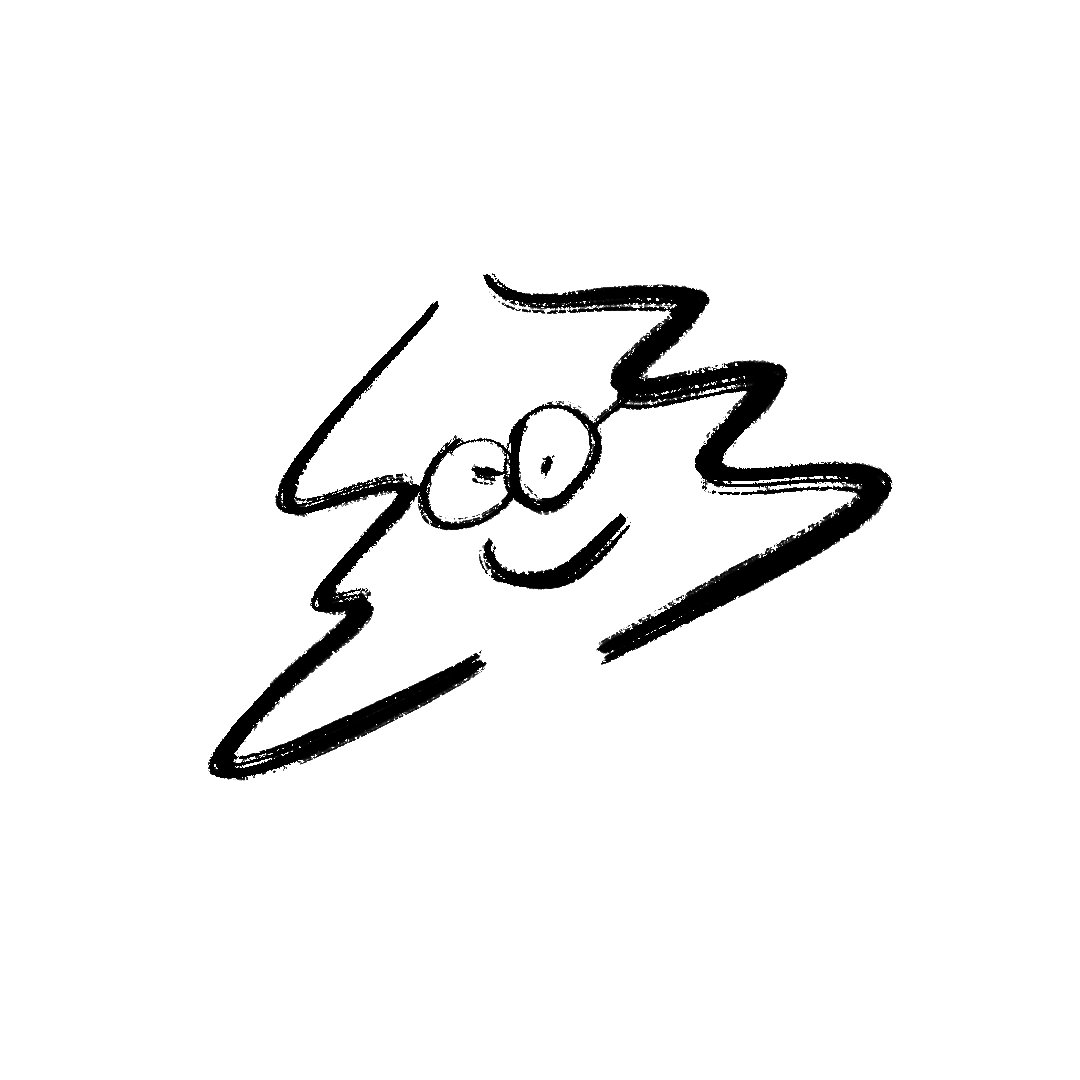【人物專訪】「傷心慾絕」的浪子 李威龍的塗鴉與瀟灑

判刑前一日, 在荔枝角收押所探望阿龍。他拿起聽筒就講個不停,「不用擔心,我不會坐太久了,應該一年多吧!」還高興地說,「在這裏,很多人喜歡我的畫,畫到不想畫了。」
阿龍常說,「無準備就是最好準備」,一如他的隨性,果真是什麼也沒準備,在還柙一星期,無人送物資,甚至福利官都幫他尋親,與母親多年無見,再見就是隔著玻璃。「我媽拿了熱湯與職員說,要送進來。」阿龍尷尬掩面。
翌日,李威龍被判監3年2個月。
法官游德康讀出判詞指,李威龍在案件中曾多次購買玻璃瓶裝飲品,在背包中有多張相關收據,電話中亦有多段有關製作汽油彈的影像和搜尋紀錄,亦有向同案中的其他人提供製汽油彈的指導,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量刑起點為4年,因早前承認屬交替控罪的「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酌情扣減略多於百分之二十。

「我不是為了社會做的」
在正式開審前的一晚,李威龍(阿龍)在Instagram中做人生第一次的直播。他穿著白色享利領的上衣,用毛巾蓋著大腿,用另一台手機放著廣東歌。
「有什麼心理準備嗎?」網友續問。
「沒有,沒準備就是最好的準備。」他笑著說。
有人說「手足加油」,他皺一皺眉頭回應,「算是吧,我聽到這些稱呼會尷尬,不過多謝支持。」一個與阿龍相熟的朋友打趣地問他,是否坐在馬桶上直播,他有點害羞地否認,解釋自己只穿了「孖煙通」(男士四角褲),所以蓋著毛巾會好看一點,「後面是衣櫃,不是厠所」。
一位自言曾在壁屋生活的網友留言,「我們為香港這個社會付出太多時間。」
阿龍托著腮嘀咕,「如何回應你好呢⋯付出太多時間⋯⋯」,他停了一停,繼續說,「沒有啦,我沒有為社會,可能你是為了社會,我非常respect(尊重)你,但我從來不會為任何人去做些什麼,買外賣可能會吧,我為自己而已,不要想多了」,一陣沉重的氣氛,阿龍笑瞇瞇地打圓場:「我是仆街來的,不要想得我太好。」
在朋友的起哄下,他在直播中唱了《發現號》,「撞進了冰山,捲上了急灣,一秒從未想折返⋯⋯」唱完後,阿龍著大家早點睡覺,不用理他。
當晚直播的觀看人數最高峰時約十二人左右,有人加入,又有人離開,,有不少「Dead air」(靜止)的時間。
直播結束時,手機畫面顯示有四十八人曾經參與。
2022年5月16日,灣仔汽油彈原材料庫案如期開審,被控「串謀意圖危害生命而縱火罪」的阿龍在早上還在更新Instagram story,告知朋友自己吃了一個豐盛的早餐,「案件審前,咖啡先行」。
控方推著九大個證物箱、一個偌大的行李箱,進入法庭。第一天審訊過去,控方仍未處理到阿龍的答辯取向,他還是能夠成功以原有條件保釋。穿著黑色連帽風衣的他,插著褲袋,拉起帽子,獨個兒從法院走出來,幾個報社的新聞攝記也衝上前拍相,只見他挺起胸膛,沒有遮擋鏡頭,昂首闊步地望著前方走去,沒有回頭,沒有閃縮。
軍訓學校與男童院的青春時光
阿龍小時候在內地居住,8 歲才來港讀小一,父親脾氣暴燥,經常拿他來出氣。在小五、小六時,阿龍要為升中選校,「我為了不想和家人一起住,自己冒簽申請表,開首的數個志願全是填寄宿學校。」最終他入讀一所位於赤柱的寄宿男校。
「小時候住青衣,老實說,赤柱在哪?我是沒有概念的。」阿龍想起童年時的自己,只想遠離那個強行被稱作為家的100呎單位。
在寄宿男校的日子,阿龍每天早上六時多便要起床晨操,學校的教育偏向體能式的訓練,「類似軍訓學校」,不時會有海上活動,出海學滑浪風帆。阿龍不諱言,「寄宿加男校,意味著暴力成份會比較多,同學和阿Sir也是會打人的,即是等同於半監房的生活,大同小異」。
「不過打人和打交是不同的,我們會稱為自由搏擊。」,當時青春期,男孩子是會較暴躁,總要有武力發洩的,「把四張床單鋪在地上就開打,阿Sir知道的,還會問何時打完收檔。」
在阿龍十五歲左右,由於多次離家出走,父親報警,屢勸不改,後來就進了男童院,住了數個月。阿龍的年齡大,不用怕被欺負,「最深印象的是那裏沒有窗,廿四小時開冷氣,早上九時才起床,不用步操,定時還會有活動、零食。」
「不止比寄宿學校好,甚至比現時的竹篙灣隔離營舒服。」他笑說。
「在男童院後,阿爸和我要上青少年法庭。」阿龍形容當時的環境與學校老師見家長無異,法官與他們是面對面坐,(青少年法庭)較為輕鬆的。」阿龍搖搖頭,笑了一笑。
法官知道阿龍不喜歡回家,判了他入住觀塘的青少年宿舍,逢星期五身邊的同學回家時,他便要到觀塘睡覺,有時會流連網吧。到了星期一,又從觀塘回到赤柱,周而復始。
後來阿龍中學也沒有畢業,被踢出校,十八歲前的他,跟隨福利官的指示渾渾噩噩地上班,大多也是一些半職的工作,而他仍是住在青少年宿舍,因為不再是中學生的關係,他需要每個月付六百元租金,除了租金之外,阿龍定期還要繳三百元給宿舍負責人,「他們會替宿生儲錢,儲到我走時,好像有三千多元可取出」。
閱讀雜誌、歷史、王家衛和尼采
學歷不高的阿龍在十八歲時離開宿舍。他到髮型屋幫人洗頭,第一個月的工資便整整兩萬元。在髮型屋工作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看免費的潮流雜誌,那時候的阿龍最喜歡謝霆峰和陳冠希。
「在時裝雜誌中,你會看到他們會穿一對勁大的拖鞋拍硬照,好奇怪,我不會說他們靚仔,但有型。」阿龍喃喃自語,「真是好X有型」,他接著說,「不記得是《號外》,還是另一本雜誌了,最後的幾頁會推介很多另類文化,無意中認識到很多非主流的東西」。
後來他愈看愈深入,發現地下文化是受到二戰影響,當時的他對於歷史認識不多,「真是拗爆頭」。
有一期雜誌介紹王家衞的《阿飛正傳》,阿龍看得著迷,不單是梁朝偉的油頭,而是王家衞對於情感的細緻描述,「有些東西你是永遠得不到,世界上沒有永恆不變」。環環相扣,「後來讀到尼采,很多事便讀通了,人的一生注定苦難,你要如何走,你終極也是要面對它,超越它。」
阿龍滔滔不絕地分享他的讀書心得,眼前這個中學也未畢業,夜蒲網吧,與書本好像扯不上關係的人,卻喜歡讀散文、新詩,喜歡林夕,喜歡周耀輝,「在男童院時,最愛讀《神鵰俠侶》,因為發夢也想練成《玉女心經》」,他說完後掩面,為自己兒時的趣怪「夢想」感到靦腆。
威龍的刺青與塗鴉
滿身刺青的他,看看起看起來凶神惡煞,但其實多愁善感,手臂紋的中文字尤為吸睛,「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恨」。這是五代南唐詞人李煜寫的一首詞在國亡家破,身為囚虜後寫的詩,李煜在慨嘆人生的愁恨該如何才能避免,而只有自己的離情別恨是深長無限。
「覺得有型,很隨性就紋了。」
對於藝術,阿龍不喜歡過多的解釋,就像他在街頭的塗鴉作品「傷心慾絕」,撇捺的搭配總是很修長,像傷心的時間會蔓延。「『傷心欲絕』是一個台灣龐克搖滾(Punk rock)樂團」,而阿龍在橫街窄巷到處寫的「傷心慾絕」是多了一個「心」。
「這個時代很傷感,生活很苦,但你可以甜。」 他從口袋中,抽出了一張寫著「傷心」的貼紙,「送給你,報答你請我飲嘢」。
後來,我才發現即使沒有取到阿龍的手繪真跡,幾乎港九新界也能看見他的作品,後巷、路牌、電箱、唐樓⋯⋯甚至有人在他的社交媒體留言,在西貢也見過。
他的作品就像一個個都市傳說。

「總有方法」活在真實中
不久,他的朋友也加入了我們的飯局。訪談一下子變成了老朋友聚會的調子。 阿龍笑著說:「我最擔心的是監獄人工低,無人性的,聽說每天上班,每個月也只得三百元。」他說得激動,朋友也趁機「揶揄」他:「也沒有潮牌買,多錢也沒用呀!」
阿龍說過慮也無法改變現狀,「卡繆曾經說,荒誕離奇是人類的根本處境,哈維爾也說過,我們要活在真實中」,很多人說現時的香港很差,但阿龍卻認為「香港最美的時刻就是當下」,即使每天有不同的政治打壓,社會氣氛很差,但人是流動的,「最壞的時代,才有最好的人」。
「我們總有方法去做小小的抗爭,舉個例,你明明可以六時下班的,但你做到七時才走,如果人人也可以六時準時離開公司,打破潛而默化的加班文化,那香港就不會有工時問題」,阿龍強調自己必定是那個「六時準時走」的人,相信在抗爭的路上,即使身邊沒有人和應,獨自一人在漆黑的隧道,看不見出口,也必須堅持走下去,「因為你就是那一點光」。
他把杯中的剩餘的酒一口乾掉,直言不諱,假若他是現時的政權掌舵人,「其實我會更兇更狼,只是大家角色不一,雞蛋與高牆,我選雞蛋。」
「為什麼選雞蛋?」
「因為雞蛋那邊,型啲。」
消失的輕鬆 他趴在大腿上
「刑期為38個月,即時監禁。」法官宣讀判詞時,重覆了兩次。
在聽到判刑後,李威龍合上雙眼,低下頭,上身完全趴在大腿上,坐在旁聽席的我們已看不到他的頭。
阿龍沒有再像往日般瀟灑,沒有在被告欄中再眯起笑眼。
「當你走進被告欄時,你會𣊬間明白,即使再多的旁聽師,實際上有些路,你必須自己一個走。」
阿龍沒有向公眾席的方向望過來,家屬席沒有他的家人,他轉身就在被告欄內的小門中消失。
有人大力嘆了一口氣。
延伸影像|Youtube
|不定期更新|Instagram:@shit.will.come.true
|舊文章主要結集|方格子:新屎坑 shitwillcometrue
|Matters、Medium:新屎坑 shitwillcome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