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 | 哲学人类学 | 人类学不同于民族志

人类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可以无限追溯的渊源,回顾20世纪以来的学科历史,人类学家的思考倚重于哲学的概念与知识传统,而哲学则试图在异域的民族志中寻求西方认识论的启发与替代。然而,壁垒森严的学科分工想象让学者们固守领地,人类学家满足于负责“特殊”的民族志写作,哲学家引述经验只是为了充实“普遍”的分析,二者一面暧昧相望,一面彼此拒绝。
回顾哲学和人类学交织的历史是有必要的。人类学一词早在古希腊哲学已经出现,在哲学受到其他思维范式冲击时,人类学的立场和哲学人类学为人立法的倾向每每是康德、舍勒、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家背水或仰攻的阵地。不同于思辨追寻“人是什么”的哲学和神学人类学思辨,近代以来的人类学实践强调通过田野,接触异质的文化,在实践中进行理解、思考和深描。这套语法虽然在20世纪才系统化为人类学的学科,却早已在历史的流转中与哲学家相遇,是卢梭遇上的加勒比人,康德在哥尼斯堡读尽的旅行日记,黑格尔在海地革命里发现的时代精神。而在现代人类学理论奠基的年代,经典的人类学现象、概念与理论也总刺激那个时代最卓越的哲学心灵不断回应和思考。哲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基于世界范围内民族志材料提出了互渗思维的理论;太平洋的马纳(Mana)概念对20世纪初欧洲现代社会反思启蒙的持续共振;维特根斯坦多次阅读《金枝》,从中获取的灵感启发了他“语言游戏”等一系列后期思想;莫斯的礼物理论不但是最具生命力的人类学辩题,也激发着德里达、马里翁(Jean-Luc Marion)等哲学家的不断回应。
对读哲学与人类学不是去攀附两门学科的亲缘性,更需要的是超越西方中心和学院中心,与在地的行动者一起构筑经验和理论的连续,揭示和理解被压抑和忽视的声音和思考,学习田野里涌现出的伦理和反思:正如作为记者的福柯在伊朗革命时所体察的“灵性革命”,乌鸦族印第安勇士教给乔纳森·里尔(Jonathan Lear)的“基进希望”,正如亚马逊部落启发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对本体论的再聚焦,埃及穆斯林女性的读经运动中马木德(Saba Mahmood)开始了对现代社会自由和伦理观念的反思。无论是丰富对人的境况的学习还是重构对世界的理解,人类学与哲学都需要从典籍转向实践,并在对实践的共同聚焦中重启交流、对话。
哲学人类学是结绳志与哲学社共同策划的系列专题。我们试图通过共同译、校的方式来开启一种共学共读的模式。这是一场去中心化的合作,目的并不是要辩论人类学与哲学的高下之分,而是试图与文章的作者们共同探讨,人类学与哲学在当代如何以新的方式彼此联结、彼此贡献。在本期文章中,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从对人类学和民族志各自使命的反思与区分出发,旗帜鲜明的反对那种将人类学折叠为民族志案例积累、在细碎的材料中总结所谓规律性的学科定位。在他看来,人类学的使命在于寻求让生活得以继续前进的方法,而非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作为“教育”的参与观察,习得一种思辨人类生活可能性与条件的智慧,而非戴上一层“替报道人说话”的伪装。作者号召以跨学科的方式打开人类学的多元化探索之路,从而批判性地拓展关于人类生活的对话和交流,用人类学家而非民族志作者的声音加入时代的论辩。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恰恰就是一种在尘世中做的哲学。
原文作者 / Tim Ingold
原文标题 / Anthropology contra ethnography
译者 / Michael
校对/ 孟竹、叶葳、星原
摘要
民族志(ethnography)旨在描述在某处、某时被一群人践行和感受的人生。然而人类学则是一个对于世界上人类生活条件和可能性的探究。人类学和民族志或许可以很好地为彼此做出贡献,但是它们的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民族志自身就是一个目的;它不是通向人类学研究目的的一种手段。此外,参与观察则是一种人类学式的工作方式,而不是一种民族志数据收集的方法。做人类学研究是与人们一起学习/研究(to study with people),而不是对人们做研究(make studies of them);这样的研究与其说是为了民族志书写,不如说是为了教育。人类学教育赋予了我们推断世界上人类生活境况的学术手段,而不必假装我们的论点是从我们曾与之一同工作的人们的实践智慧中提炼出来的。我们的工作是和他们保持对话,而不是替他们发声。只有承认人类学研究的本质是思辨性的(speculative),我们才能够使自己的声音被聆听,并且和其他学科进行适当的对话。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在一条构建未来大学(universities of the future)的大道上引领航向。
关键词:
民族志、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教育、哲学、艺术、大学
正文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并不反对民族志。就我理解,民族志的目的是通过写作、电影或者其他图像媒介提供一个关于生活的记述,如同它真实地在某处、某时被一群人所力行和感受的那样。好的民族志研究情感细腻、注意语境下的细微差别、细节丰富,并且最重要的是,忠实于它所描绘的一切。这些都是值得尊重的品质。
因此,我所反对的不是民族志本身,而是反对把它描绘成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全部意义和终极目标。我相信将人类学折叠成民族志导致这个学科偏离了它恰当的目的;这阻碍了人类学对于我们时代重要问题的讨论做出贡献,并且损害了它在学术界的地位。我主张,为了这个学科的未来,我们必须停止含糊其辞,应当解释清楚人类学和民族志之间的不同。当然,这意味着要明确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定义和目的。
所以这里是我的定义。我坚持认为,人类学是对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一世界上的人类生活条件和可能性的探究,它是慷慨的(generous)、开放的(open-ended)、比较的(comparative)也是批判性的(critical)。它是慷慨的,因为它关注并且回应他人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在调查中,我们欣然接受给予我们的一切,而不是利用托词来索取不属于我们的事物,而且为了我们自身道德、学术和实践上的成长,我们尽力去偿还我们对他人的亏欠。这首先发生在参与观察中,我之后将会回顾这一点。人类学是开放的,因为我们不寻求最终解决方案,而是寻求生活得以继续进行的方法。就此而言,我们致力于可持续的生活(sustainable living)——这种可持续性不是通过排斥他人来只为一部分人保持世界的可持续,而是让世界为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提供一个位置。人类学是比较的,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可以选择这条路,也同样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没有一条道路被预先规定为是唯一“自然的”。所以,“为什么是这条路而不是那一条?”这个问题总是在我们脑海中显得格外重要。人类学是批判性的,因为我们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人们大体上认同,主导当今时代的生产、分配、治理和知识的组织结构已经把世界带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寻求可持续的方法时,我们需要一切可得的帮助。然而,没有任何专业科学、原住民、教义或哲学已然拥有了通向未来的钥匙,但愿我们能够找到它。为了我们自身,我们不得不一起创造那个未来,而且这只能通过对话来完成这一创造。人类学的存在就是为了拓宽这场对话的范围:去创造关于人类生活本身的交流。
如果你认同我对于人类学的定义,那么我认为你也会同意,人类学的目的和原则是与民族志完全不同的。作为不同的事业,人类学和民族志或许是互补的,它们或许有许多东西可以互相贡献,但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有差异的。然而,我想把这一点解释得绝对得明确,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差异被社会人类学的某些创始人以同样坚定的论据提出,然而后者的立场到今天仍然被一些人所支持。他们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也是:民族志是个殊的(idiographic),致力于记录经验层面的特殊性;而人类学是规范的(nomothetic),致力于比较式的归纳和探索在人类事务中如律法般的规则性。这个想法就是你先去进行你的民族志研究,然后在下一阶段,把你的研究转化成一个用来比较的案例,和其他类似的研究放在一起,希望能显现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普遍性。每次我听到“民族志案例研究”(ethnographic case study)这个说法被天真地反复讲述,好像它完全没有问题,我都会皱起眉头表示反对。而每当该研究描述的人被写成好像就属于民族志学者本人——如“格尔茨的巴厘岛人”(Geertz’s Balinese)——我的皱眉就变成了尖叫!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贬低民族志研究的精神和目的了。有时我会被指控为想攻击民族志。但是我的目标恰恰是相反的。我是要保卫民族志,以抵御那些会把他人的生活包裹在案例中的人,以及那些仅将民族志视为实现人类学概括目的的手段、而其自身没有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的人。我想要保卫民族志以抵御那些只将它视为一种方法的做法。当然,就像任何手艺活一样,民族志有着自己的各种方法——它的经验法则、它的工作方式——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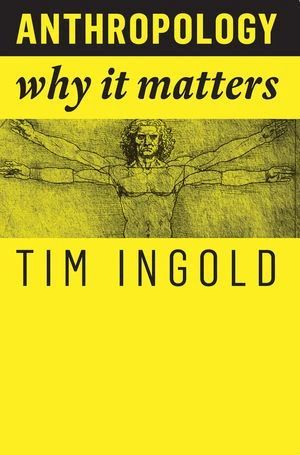
这让我回到了参与观察。我已经提到,参与观察是人类学实践的关键,而且保证了它慷慨的参与和回应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与人沟通的方式。但我也想强调,参与观察和民族志不一样。“民族志田野调查”(ethnographic fieldwork)这个概念延续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你在田野中所做的是收集关于人和他们生活的素材——或者,为了美化你的社科履历,你可能称这类素材为“定性数据”(qualitative data)——之后你会对其进行分析和撰写。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观察在教科书中经常被描绘成一种数据收集的方法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笔墨被洒在了对参与和观察进行结合的实践困境与伦理困境方面,仿佛它们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都知道,一些事是非常令人不安的,那就是表面上诚心地加入一群人,但后来却把他们弃之不顾,于是你的研究就变成了对他们的研究,而他们成了一个案例。然而,在参与和观察之间实际上没有矛盾;确切地说,二者缺一不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观察和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混为一谈。观察本身不是客体化。它是注意人们在说什么做什么,观看和倾听,并且以你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也就是说,观察是一种投入的参与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作为人类学家,这是我们所做的,也是我们所体验的。而且我们做并体验这些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即我们在自身的实践与道德教育方面蒙受他人之恩。简言之,参与观察不是一种数据收集的技术,而是一种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这份承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石。
用“的(of)”和“与(with)”这两个小词所描述的不同作品之间的区别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把观察转变为客体化,超越了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与存在本身,把它们变成被严格限定的研究主题。我们因而得到了对这个或对那个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is or that)。然而就我的理解,人类学的实践意味着与(with)人一起研究,而不是对他们进行研究——就好像我们在大学里与老师一起学习/研究。这么做是为了使我们更加智慧和成熟,增强我们的观察、推理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期待将来我们能够把这些能力用于任何可能面临的问题上。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观察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教育而并非民族志。它是一种学习的方式,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学习可以是变革性的。
这里隐含了一层关键的意义。在描述真实性的要求下,民族志研究者在他/她的写作上有时会感到束缚。你不能随便写,且你所写的需要被证明是对于你调查对象所做、所说、所思的一个公正描述、解读或分析。作为人类学家的我也不能随便书写。但在我的写作中,我至少可以依据我的阅读、我参与过的对话和我自己批判性反思,来主张我所认为的真实,或尽可能接近于我能获取的真实。人类学不外乎就是思辨性的(speculative),而且,我想珍惜和保护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拥有的智识自由,去思辨世界上人类生活的条件和可能性。当然,我必须做好准备用推理、观点和证据来支撑我的立场。但我本就无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证它,即假装我提出和辩护的观点是从我与之工作和学习的人那里提炼出来的。实际上,我可能极其反对他们。参与观察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我们当然不必去认为,人们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真实或美好的。他们可能会做或说一些我们认为可恶、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用同情的面纱来掩盖这种憎恶,或对于他们的言行进行美化叙述,而是直接与他们争论。因为在论述我们为何有这样的感觉时,我们能够增长自身的智慧,并增强我们自身观点的力度和严谨性。
我相信我们必须要求有权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在我们自己研究的基础上说出我们自己的思考,无论它是不是与我们对话者的想法相符。我们或许从他们告诉我们的东西中有所收获,但作为人类学家而不是民族志研究者,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反映它。就像任何其他学科的实践者一样,我们必须准备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而不是躲在他人的声音之后。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这个时代的重要论辩——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论辩——之外,或发现我们只是在为他人提供任人随意摆弄的材料。我们很清楚,还有许多思维狭隘、排斥异己或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人会迫不及待地填补这个空缺。我们人类学家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说,而且我们需要在那里(译注:指在时代的论辩中找到一个人类学家的位置)去说出它们。然而,只有卸下这样的伪装——即认为我们只有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时才有发言权、身为人类学家却无话可说——我们才能让他人感受到我们的存在。

我想呈现的是,人类学在根本上是一个思辨式的学科。在这一层面上,它类似于哲学,但与(至少大多数哲学家所做的)哲学所不同的是,它在尘世中做它的哲学工作,与居住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进行对话,而不是对已被树立为经典的文本进行晦涩的反思。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能做出比大多数哲学家更好的哲学,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长期与生活脱轨并且迷恋于空中阁楼的思维实验。但这种思辨的抱负再次将人类学和民族志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它为人类学开启了许多其他的探究之路——比如通过艺术、设计、戏剧、舞蹈和音乐,更不必说建筑、考古学和比较历史学。与这些领域成功的跨学科合作恰恰取决于承认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民族志。举例而言,虽然民族志和艺术史结合得很好,但尝试结合民族志和艺术实践往往会导致失败的艺术和糟糕的民族志,这不单损害了民族志研究者对忠实描述的承诺,也损害了艺术的实验性和介入性质疑。但是一种具有实验性和质疑性的人类学就能够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与艺术实践相结合。不同于民族志和艺术史,人类学和艺术实践的关键在于,它们不是通过将行动和作品置于语境中来进行理解——不是对它们进行解释、罗列然后将其搁置——而是让行动和作品在场,以便我们能够直接对它们作出处理和回应。
我想要以一两句关于人类学的未来与大学的未来之间关系的话来收尾。人类学是一个大学学科;如果失去了大学所提供的避风港,人类学将无法生存。所以,目前在大学内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决定这个学科的生死存亡。当前,大学正在向企业式的新自由主义屈服,而人类学正饱受煎熬。我们正处于和整条船一起下沉的危机之中。我认为我们需要为大学作为包容、智慧和人性之地的未来而奋斗;在那里,思想将得到重视,各国人能够和平地聚集在一起进行思想的辩论。我认为这也是人类学的未来。因此,我对人类学未来的憧憬也是我对大学未来的憧憬,而且人类学必须在这样的大学中居于核心位置。然而,只有彻底地与那种将人类学简化为民族志案例累积的做法一刀两断,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的大学中成功锁定人类学自身的未来。
作者: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是阿伯丁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曾在拉普兰的萨米人和芬兰人中间进行田野调查,写作主题涉及环北极地区环境、技术与社会组织,人类社会中的动物、人类生态及进化理论等。他近期的研究聚焦于环境感知和技能实践。英戈尔德目前的学术兴趣在于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建筑学之间的联结。他的近著包括: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2000), Lines (2007), Being alive (2011), Making (2013), 以及The life of lines (2015)。
译者:
Michael,一个关注巴基斯坦边境的学生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43. 东北的昨天:从通化讲起 | 东北研究 1
144. 东北的今天: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 | 东北研究 2
147. 哲学人类学|「礼物」的哲学谱系
149. 让剑道成为奥运竞技项目?——不了,谢谢
150. 反思男子气概:作为照护者的父亲们
151. 蜜蜂照料的生态化:瓦螨疫情中的多物种身体和信任关系
152. 哲学人类学 | 人类学不同于民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