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容不下的純真——讀《麥田裏的守望者》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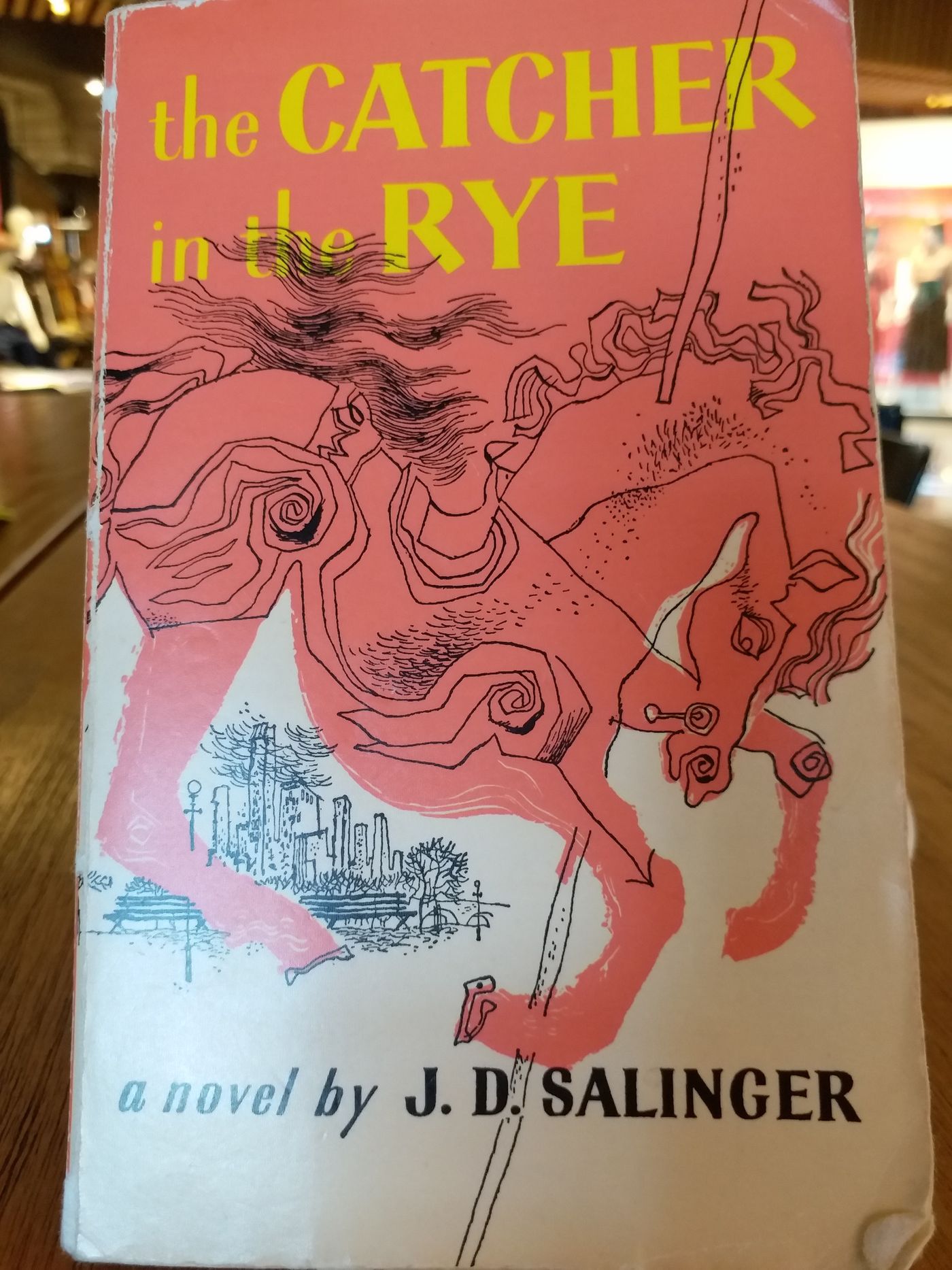
“The Catcher in the Rye”這本書是我至愛十大小說之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讀,讀了不下十次,中譯本有的名為《麥田捕手》,有的名為《麥田裏的守望者》,是美國作家塞林格(J.D.Salinger)1951年出版的小說。
故事主角霍爾頓(Holden Caulfield)正是「世界容不下的純真」的具體化身。霍爾頓是個率直、純真,卻對世界充滿疑惑,也充滿成長的焦慮的十六歲少年,作者用這少年的口吻,以這少年的自述來寫這故事,透過霍爾頓被第三間學校開除後在外流連三天所遇上的人、所發生的事,以及他許多的回憶,呈現世界的虛偽和荒謬之處,並且展示作者所珍視的真誠和單純。即使已經讀過很多遍,讀到某些地方,我仍然會笑出聲,想深一層,其實是笑中有淚。整個故事將現實和回憶環環相扣,霍爾頓每一個經歷、每一段對話,都能觸動人心、引人深思,但所用以敘述這一切的語言卻是那麼淺白、通俗、率直。
故事中有三件事是我很喜歡的,而且我認為是很有代表性的,從這些事件中就能一窺作者透過霍爾頓想要表達的思想。
第一個是有關霍爾頓的愛情觀。
霍爾頓像一般少年那樣約會過很多女孩,因為少年對性的好奇,他甚至也跟約會的女孩有過親密舉動,卻沒有一個真的能成事。只有一個女孩,他沒有將她跟「性」連在一起,那就是曾經住在他隔壁的琴(Jane),作者透過好多片段、回憶,從霍爾頓的敘述中那些與琴同度的時光,讓人感受到他有多喜歡她。他們相識的經過就已經表現出霍爾頓對琴的獨特情感:
「我認識她的經過是因為她家的那隻德國種獵狗老在我家草地上拉屎。我母親為這事十分生氣,她去找了琴的媽,鬧得很不愉快。過了一兩天,我在俱樂部遇見了琴……我跟她打招呼的時候,她對我冷得像塊冰。我真他媽的費了不少工夫跟她解釋,說我他媽的才不管她的狗在哪兒拉屎哩。對我來說,牠就是到我家的客廳來拉屎都成。嗯,這以後,琴就跟我做了朋友。」
霍爾頓非常仔細觀察琴的動靜,那不是男孩對漂亮女孩的注目,而是單單喜歡她就是她:
「我並不打算把她說成地道美人。可她的確讓我神魂顛倒……她只要一講話,加上心裏激動,她的嘴和嘴唇就會向五十個方向動。這簡直要了我的命。而她也從不把嘴閉得緊緊的。那張嘴總是微微張開一點,尤其是她擺好姿勢要打高爾夫球或者是她在看書的時候。她老是在看書,看的都是些非常好的書……我母親不怎麼喜歡琴……甚至都不認為琴長得漂亮。我呢,當然認為她漂亮。我就喜歡她長的那個模樣兒,就是那麼回事。」
他形容從前與琴看電影牽着手時:
「我希望你不要僅僅因為我們不在一起摟摟抱抱地胡搞,就把她看成是他媽的冰棍什麼的。她才不是呢。我就老跟她握著手,比如說。這聽起來好像沒什麼,我知道,可你跟她握著手卻是滋味無窮。大多數的姑娘你要是握著她們的手,她們那隻混帳的手就會死在你的手裏,要不然她們就覺得非把自己的手動個不停不可,好像生怕讓你覺得膩煩似的。琴可不一樣。我們進了一個混帳電影院什麼的,就馬上握著手,直到電影放完才放開,既不改變手的位置,也不拿手大做文章。跟琴握著手,你甚至都不會擔心自己的手是不是在出汗。你只知道自己很快樂,你的確很快樂。」
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措詞(他根本就是個孩子),卻表達了心靈最深的感動。
琴搬走之後,他們沒有再見面,從故事開始沒多久,霍爾頓就有一個近在眼前的機會跟琴重遇,但他緊張得不敢現身。後來他提到他想要打電話給琴,但有趣的是,這個「想要打電話給琴」的念頭在整個故事中重現了好多次,每一次他都會有莫名其妙的理由擱置了這個念頭,到某次真的撥通電話了,那邊卻沒有人接聽,最終到了故事結束時,他都沒有跟琴聯絡過。
霍爾頓的學長卡爾路斯是個對各種性事非常有經驗的人,霍爾頓逗他玩,問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他:「你主修什麼?性變態嗎?」卡爾路斯卻一本正經跟他提到自己最近跟一位東方女子的關係,然後霍爾頓如獲至寶一樣,抓住他所說的什麼「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關係」,說起他自己對愛情與性的困惑:
「我知道那種關係應該是肉體和精神的,而且也應該是藝術的。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跟人人都這樣——跟每一個和你摟摟抱抱的姑娘——跟她們全都來這一手。你說對嗎?」
然後他感嘆地說:「我的性生活糟糕得很。」
「自然啦,你的頭腦還沒成熟。」卡爾路斯這樣評論霍爾頓。
「不錯,一點不錯。我自己也知道,」霍爾頓說。「你知道我的毛病在哪兒?跟一個我並不太喜歡的姑娘在一起,我始終沒有真正的性慾——我是說『真正的』性慾。我是說我得先喜歡她,要是不喜歡,我簡直對她連一點點混帳的慾望都沒有。嘿,我的性生活真是糟糕得可怕,我的性生活真是一塌糊塗。」
這些對話中表現出諷刺性:霍爾頓認為自己將性與愛緊緊相連的心態讓他的性生活「很糟糕」,但卻正好顯出他內心的純真(卡爾路斯卻說這是「頭腦還未沒成熟」的表現,作者想諷刺的正是這種所謂的「成熟」),以及對愛的執著!這份純真與少年成長中對性的困惑交織在一起,這份對愛的執著,反襯他所身處的環境和文化充斥裝模作樣的虛假。這是霍爾頓可愛之處。而最有趣的是,他與他所喜歡的琴的交往中,他覺得最接近「性」的一次,是琴因為害怕繼父而哭泣時,他擁抱琴,親吻她的臉,安慰她,但事實上,這也跟「性」沒有什麼關係。
第二件很觸動我心的事情是霍爾頓提到有一次他去看電影,他其實不怎麼喜歡電影,只是約好的朋友未到,無聊時一個人走了進去。那個年代(1940年代末)紐約的電影院在播放電影前會有現場表演節目,由現場樂隊演奏配樂,當時正好快要到聖誕節,他看到了每年都會重複演出的聖誕節目,他這樣描述:
「所有那些天使開始從包廂和其他各處出來,手裏拿著十字架什麼的,那麼整整一大嘟嚕——有好幾千個——全都像瘋子似的唱著:『你們這些信徒,全都來吧!』真是了不起。幹這玩藝兒的本來意思大概算是虔誠得要命,我知道,同時也好看得要命,可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虔誠或好看的地方,老天爺……去年我跟薩麗海斯也來看過一次,她不住口地稱讚,說服裝什麼的都美極了,我說耶穌要是能親眼看見,準會作嘔——見了所有這些時髦服裝什麼的。薩麗說我是褻瀆神明的無神論者。我大概是這麼個人。耶穌可能真正喜歡的恐怕是樂隊裏那個敲銅鼓的傢伙。我從約莫八歲開始就看他表演……他是我生平見過的最好的鼓手。整個演出中,他只有機會敲一兩次鼓,可他沒事做的時候從來不露出膩煩的神色。等到他敲鼓的時候,他敲得那麼好,那麼動聽,臉上還露出緊張的表情。」
如果霍爾頓算是「褻瀆神明的無神論者」,那麼我覺得他可能是最接近上帝的無神論者,從他對聖誕表演的厭惡,以及(最重要的)他對那位謙卑的鼓手的欣賞,再次顯出他對真、善、美的喜愛,並且含蓄地透露了什麼是真正的「信仰」。
看完電影之後,霍爾頓把那電影批評得體無完膚,他形容說:「那電影混帳到了那種程度,我倒真是捨不得不看。」(每次讀到這裏都笑死我!!)不過這還未算惡劣,他說整場電影最讓他受不了的是坐在他旁邊的那位女士:
「(她)在整個混帳電影放映時哭個不停。越放到假模假式的地方,她越哭得兇。你也許會以為那是因為她心腸軟得要命,可我正好坐在她旁邊,看出她並不是心腸軟。她帶著個小孩,小孩早已看不下去電影,一定要上廁所去。她不住地叫他規規矩矩坐著。她的心腸軟得就跟他媽的狼差不多。那些在電影裏看到假模假式的玩藝兒會把他們的混帳眼珠兒哭出來的人,他們十有九個在心底裏都是卑鄙的雜種。我不開玩笑。」
這段話是典型的霍爾頓語氣,原著英文版本中那些咒罵 (“goddam”, “hell”, “bastard”)在這段文字中不斷湧現,承接上面有關聖誕表演和鼓手的敘述,看得出他心底對於「虛假」非常厭惡,而「真誠」對他來說是謙卑地做事,以及溫柔對待那些真實生活裏的人(尤其是小孩子)。
這兩個片段,對我這個從小上教會、又容易流淚的人來說,是非常「到肉」的挑戰:什麼是真實的虔誠?什麼是真實的憐憫?霍爾頓的率真不斷揭露我的虛假,同時不斷呼籲我回歸真善美——而這是真實的對上帝的敬畏,是真實的信仰。
至於第三件事,是霍爾頓被學校開除,在外流浪了兩天之後,趁父母不在溜回家(他想等再過兩天父母收到學校的通知,消化了他被開除的消息之後,才正式回家,避免見到他母親的強烈反應),與他最疼惜的妹妹菲苾(Phoebe)聊天,妹妹知道他又在學校出事,他批評在學校所見的一切虛偽(他的用語是「假模假式」)的事,然後菲苾沒好氣地說:
「你不喜歡正在發生的任何事情!」
霍爾頓聽見妹妹這樣說他,心裏更煩了,他激動地說:
「我喜歡,我喜歡。我當然喜歡。別說這種話。你幹嗎要說這種話呢?」
「因為你不喜歡。你不喜歡任何學校,你不喜歡千百萬樣東西。你不喜歡。」
「我喜歡。你錯就錯在這裏——你完完全全錯在這裏!你他媽的為什麼非要說這種話不可?」
「因為你不喜歡,」菲苾說。「說一樣東西讓我聽聽。」
「說一樣東西?一樣我喜歡的東西?」
霍爾頓當時已經一夜沒睡,而且正在發燒而不自知,他無法集中精神思考,腦袋裏想到的卻是一些人、一些事,例如:他在火車站附近的咖啡店遇上的兩位提著破籃子到處募捐的修女,其中一位還跟他討論文學;另一個是在他從前就讀的某間名校的一位名叫詹姆士的同學,詹姆士生得瘦削、個子小,卻因為堅決抵抗霸凌,誓不低頭,最後從宿舍的窗戶跳出去,倒斃在宿舍入口的台階上,寧死不屈。霍爾頓跑到樓下時,只見「他已經死了,到處都是牙齒和血,沒有一個人甚至敢走近他。」他身上還穿著霍爾頓借給他的那件窄領運動衫。
霍爾頓想這件事想得入神,菲苾就說他「連一樣(喜歡的)東西都想不出來」。
「不管怎樣,我喜歡現在這樣,」霍爾頓說,「我是說好像現在這樣,跟你坐在一塊兒,聊聊天,逗著……」
「這不是什麼真正的東西!」菲苾抗議說。
「這是真正的東西!當然是的!他媽的為什麼不是?人們就是不把真正的東西當東西看待。我他媽的對這都膩煩透啦。」霍爾頓激動地回應。
對霍爾頓來說,他真正喜歡的事物是關乎真善美的,但這樣的事物很難述說,他是直覺地想到那些他覺得是代表著真善美的人和事,他只能舉例來說,例如那兩位修女和詹姆士同學,他又舉了一個例子說其中一樣他喜歡的事,就是這樣與菲苾待在一起,與她閒聊和開玩笑,但人們從來不看這種「在一起」是「真正的東西」,也就是「有價值的東西」,他為此感到厭煩。
然後,霍爾頓在與菲苾的對話中,終於想到可以怎樣解釋自己真正喜歡和真正想做的事,他引用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詩句「你要是在麥田遇到了我」,說:
「……將來要是能他媽的讓我自由選擇的話……不管怎樣,我老是在想,有那麼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塊麥田裏做遊戲。幾千幾萬個小孩子,附近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是在那兒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說孩子們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幹這樣的事。我只是想當個『麥田裏的守望者』。我知道這有點異想天開,可我真正喜歡幹的就是這個。我知道這不像話。」
跟他說自己的性生活「很糟糕」一樣,他說自己的夢想是「異想天開」和「不像話」,都是帶著少年的純真與迷惘,更諷刺地揭露成人世界已然失去誠摯的心靈,那是世界容不下的純真。

(我引用的中譯本是南京譯林出版社施咸榮的翻譯,讀過許多翻譯名著,不得不承認,內地的翻譯是很有水準的,非常傳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