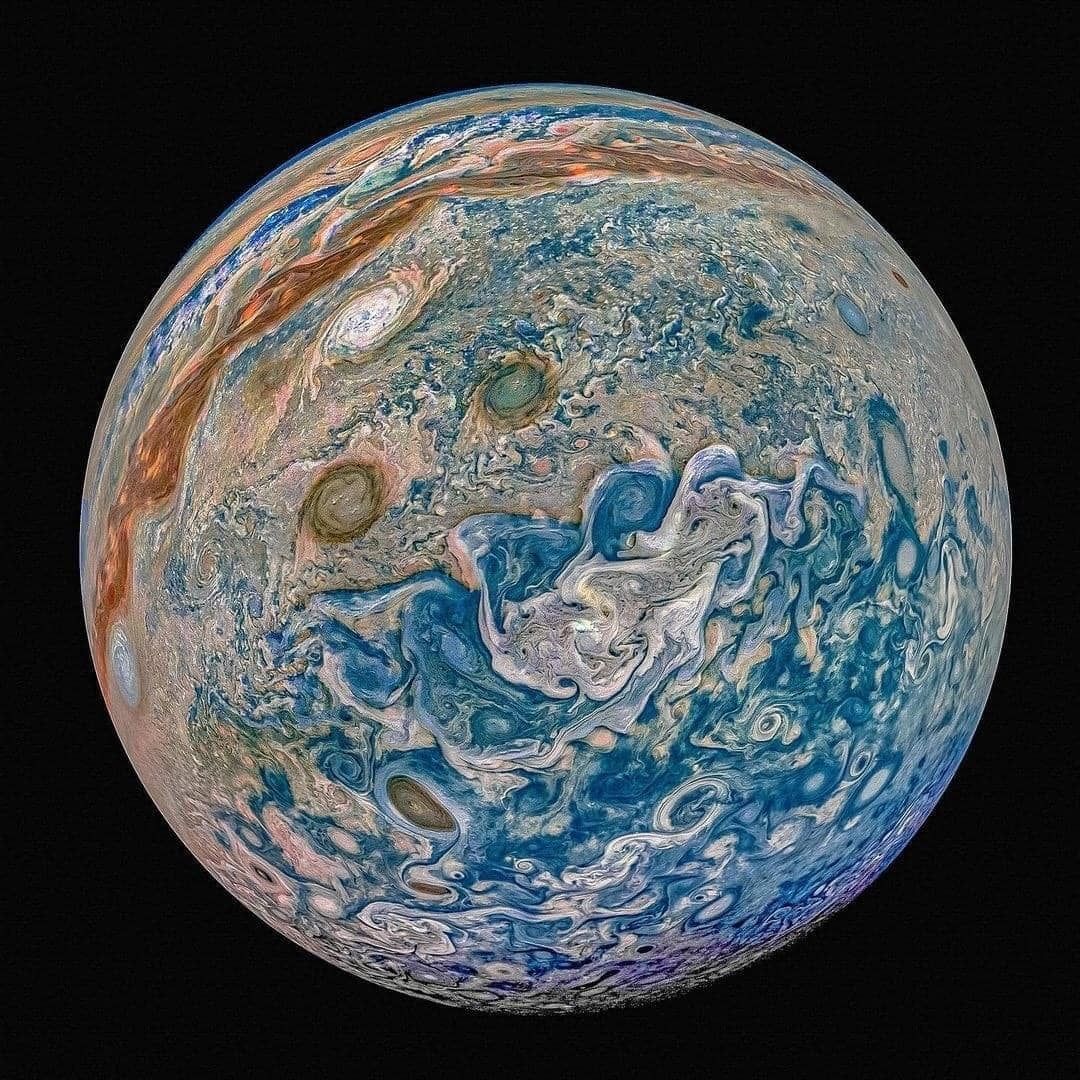個人小寫|如何完美地收妥自己的情緒
先說結論。答案是不可能。
我其實以為我可以很快回到正常狀態。畢竟最後幾年,我很刻意疏遠老爸。幾個月打不到一次電話,過年找盡理由不回家。就算有機會回南部,也像做賊似地閃閃躲躲,非良心大現不回去看他。我疏遠他的程度,連向來與我感情較好的大姊都無法原諒,與我冷戰直到最後我們在醫院碰頭才解。
很久以前我與一個家庭狀況雷同的朋友聊起,我說,我們都很清楚,當我們的父親過世後,我們一定會後悔。後悔沒有再多為他做點事,沒有再對他好一點。但即使知道未來一定會面對這樣的後悔,現在的自己,真的就是只能這樣,無法多做什麼。連一點點都沒有辦法。
整個治喪期間我沒怎麼哭。告別式上,司儀要子女們跪地伏著致哀一分鐘,我聽著右手邊傳來大姊的哭嚎,連二姊也跟著抽抽噎噎不停,唯我雙目皆乾,什麼情緒都沒有。可能旁邊的親戚長輩看在眼裡都要說,那個小女兒怎麼連一滴眼淚都沒有掉,真不孝。
告別式後,火化,圓滿宴,撿骨,入甕,最後是晉塔。全部事情結束後約莫下午四點多。我要二姊夫不用車我回住處,我搭捷運就好;我還交代二姊,如果不會太累,就到熱鬧的地方走走,去去低迷的陰寒氣。
不知道為什麼,我開始感覺什麼地方,空空的。
那天回到住處後晚上放聲崩潰哭了一場。隔天,再隔天,再接下來到了今天,看似一般,卻隨時都會掉下淚來。也不見得是真的想起老爸的什麼,但就是哭了。
我想起外公外婆接連過世之後,阿娘有次告訴我,從今以後,她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了。我那時聽了只覺替娘心酸。對比現在,假如連我自己都有那麼多無法承受的時刻,我不知道比我更與老爸親近的兄姊們該怎麼度過。
我想我很幸運,到四十幾歲才失去父親。我已成年,各方面理論上都足以自立。比起身邊許多年少甚至童年時就失去父親的朋友,我想我很幸運。
然我還是覺得,人真的很脆弱。一路長大,都在學習怎麼讓自己更加堅強,除了要堅強地在這個世界上存活,還要有足夠的堅強,好應付在生命各個階段來臨的悲傷。而那彷彿是怎麼存都不夠的存款,只消一次提領,整個就透支了。
昨天去見阿娘。原以為還要聽她講那些過往的怨氣,也做好心理準備。然或許人走了之後,有些糾葛也稍微歇了手。阿娘問著喪禮上的一些瑣碎,聽我講一些混亂到令人發笑的事情。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我始終低垂的眼神,她沒多說什麼,只勸要我多休息一陣。
「會有一些情緒,要好好整理。別太勉強。」
似是某種過來人心得,一種學姊帶學妹的經驗分享。畢竟我多了一個身份,與她同為喪父者。
回程的火車上,我腦子裡盤旋著阿娘幽幽地問我的那句:
「我最後沒有回去看他,妳會怪我嗎?」
我說不會。我還亂七八糟地說了類似就算你們有結婚然後離婚也不是每對前夫前妻都會去參加彼此的葬禮吧之類云云,希望能沖淡一些她不需背負的罪惡感。
而我掂量不出她凝聚了多少勇氣問出這一句。老爸還活著時,她偶爾會跟我說,她時常夜半想起過往種種,「心肝頭凝嘎睏抹企」。那樣一句話、一個狀態,所承載的恨與怨,我不是當事人,卻也可以感受些許。我不知道此後我娘會不會再有這種輾轉反側的深夜,可能會,可能不會。就像我這幾天也不時問著自己,我知道我對老爸還是有怨,有很多不能諒解,這一切真的隨著他的入土,我都放下了嗎?
而我是否如過去的我所說,在老爸百年之後,我一定會後悔他生前沒有再對他好一點。我後悔嗎?
我可能有很多種情緒,而後悔的占比可能小到無從計算。我想起昨天和阿娘說的,就算是親子,我叫他一聲爸爸,我是他的女兒,也不代表我們就該如世俗期望的親不可分。
這似乎將是一段漫長而無盡的釐清。目前我好像只能說到這裡。
(此文為2019年11月我父過世後事期間,寫於個人臉書。此處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