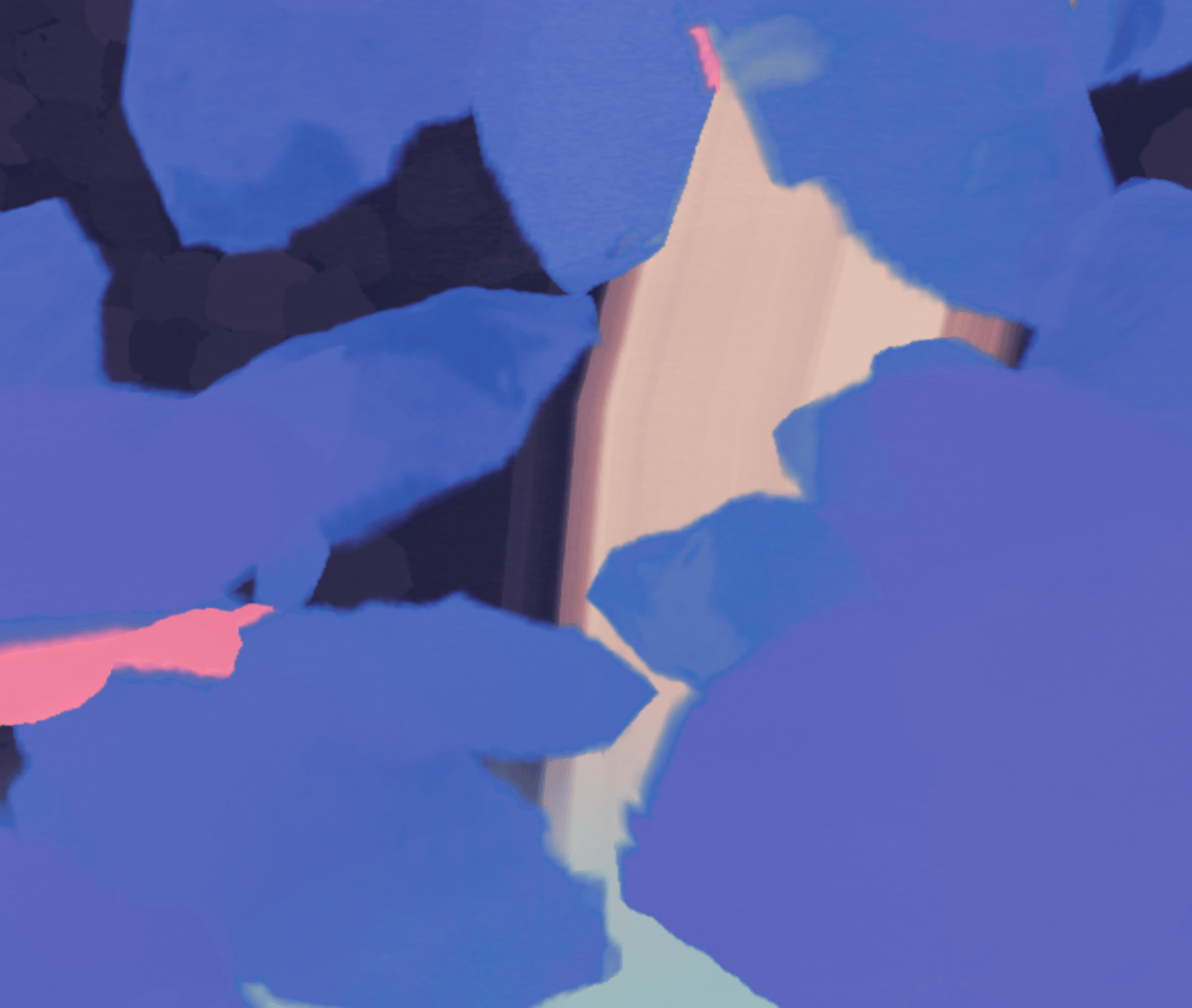寫作的理由
Matters 是很小的社群,無論是活躍的用戶,還是標籤裡的計數。我認為以目前的運營模式,它只能永遠是小型 forum 的形態。我在這裡寫的唯一原因不是為了讓人知道自己,只是因為喜愛的那個女孩子也在這裏寫,而我希望有一天她也許,又或者一直不會,發現我在某個地方陪伴過她。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寫著短短的,不成樣子的詩:也許在我看不見的地方,或者在我死後,有人會發現它們,知道有一個過去的人寫過這些話,用他的方式陪伴著另一個孤獨的人。
每個人寫作出於不同的意義。那個女孩子希望自己被記住。她寫:
我想寫一句消極浪漫主義的詩
一句就可以讓世人記得那個只寫了一句消極浪漫主義的詩人是我
為了寫作我強迫自己夢見歌劇院和老圖書館的樓梯
然後是消防通道的樓梯和扶手上的銅屑
她也為瑪奇法朵寫過一首詩。後來我才發現因為翻譯的問題,Macchiato 就是我聽過的手風琴「漂浮瑪奇朵」裡同樣的那種一份牛奶,兩份義式濃縮的小小一杯咖啡。她也想讓人記住她喜歡的 Macchiato,讓人在說起這個詞的時候,想起的詩人是她。在 MoMA 裡她半開玩笑地和我說,
我覺得我的東西一百年後也可以在這裡展出。
我相信她是認真的,也相信她真的可以做到。而我不能。但我並非相信我寫得較差,只是我從來不屬於這個時代,不屬於博物館和這個社會體系,聲音難以被很多人聽到,所以我只屬於我的朋友們、更少的孤獨的人。我是這麼告訴她的,我死後不會進入博物館,只會回到天空 (cosmo)。
在她身上我看到的是深刻的孤獨,是想要被人記住的努力,即使那種記住並非是理解,而是成為標本,成為裝訂的書頁,成為凝固的形態。也有人寫,出於一眼可以看穿的虛榮。那些人的 title 比詩句更長,思想比靈魂更空。而我,不想為了自己而寫作。
她送我一本封皮是深黑、紅框的 Ferlinghetti 的 Poetry As Insurgent Art,詩人寫:
Poets, come out of your closets,
Open your windows, open your doors,
You have been holed-up too long
in your closed worlds.
Come down, come down
from your Russian Hills and Telegraph Hills.
我難以做到沒有一點為自己寫作的意味,因為我也是我自己的讀者,也是那個同樣困在肉體裡,不得不脆弱而經受孤獨的人。只是無論如何,即使我出發於自我,在詩所完成的時候,它就已經不再屬於我自己。同樣地,我曾抄給她一段加謬:
在我看來,藝術並不是一種獨自的享樂。它是通過給予最大多數人以關於共同的苦樂的特殊的形象來使之受到感動的一種方式。因此,它迫使藝術家不離群索居,它使他聽命於最謙卑、最普遍的真理。一個人常常因為感到自己與眾不同才選擇了藝術家的命運,但他很快就明白,他只有承認他與眾人相像,才能給予他的藝術、他的不同之處以營養。正是在他與別人之間的不斷的往返之中,在通往他不可或缺的美和他不能脫離的集體的途中,藝術家成熟起來了。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藝術家甚麼都不蔑視,他們迫使自己去理解,而不是去評判。
為個展準備的 zine 連續工作了三個日夜終於在週一的深夜完成了內容,還待排版,印刷,手工修訂,拆散其中一本為展做準備。兩三天裡每天就吃一頓飯,結束時覺得身體不是自己的,還能感覺到東西,可好像是從另一個地方奇怪地看著這具操作著的身體。
在今天你為什麼寫作?這是最最重要的問題。我曾回答「大概是希望經我之手鍛造的文字,讓人們彼此相愛」。我的另一個回答是,希望陪伴一些和我走過同樣艱難旅程的人,讓他們知道前面並非無盡的黑暗,而是一片海洋,一個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