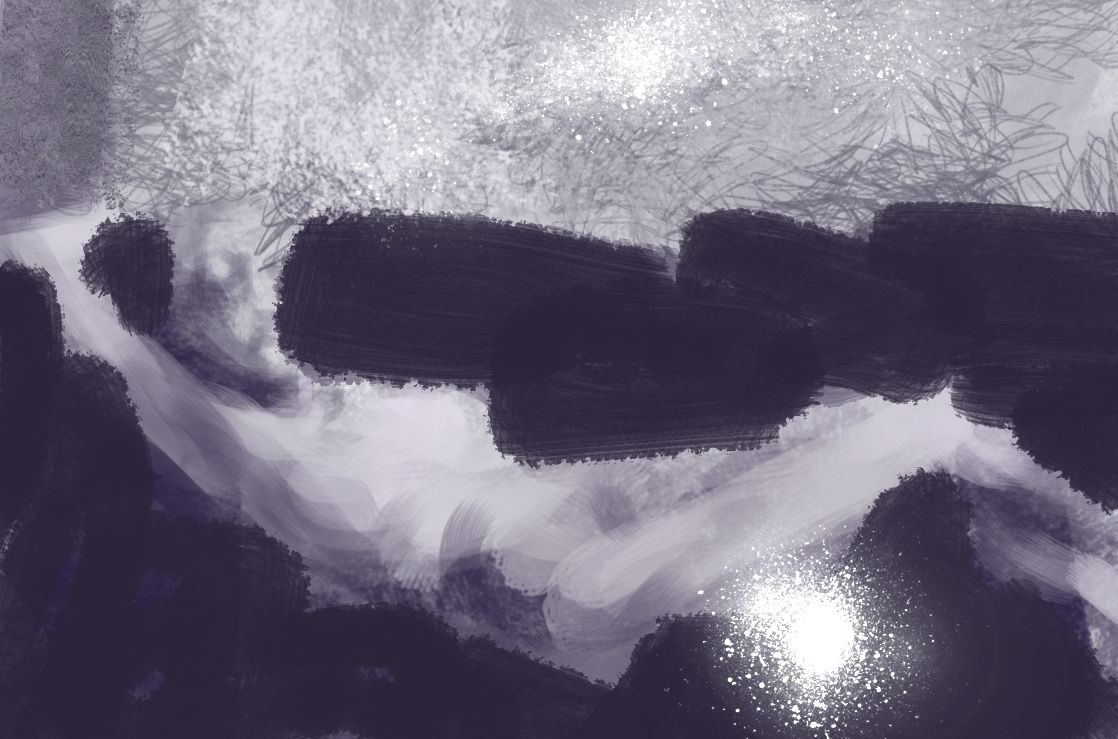【讓愛發電】以母系社会为透镜,翻看父权话语 (五)|听一听,停一停
第五章
我们上一章提到,至少就我熟知的汉文化地区来说,总有各种原因让孩子难以得到刚好又不过分的爱的支持,从而也埋下了各种不同的结症,甚至暴力的根源。暴力的根源不仅是肢体、语言暴力或者侵凌性带来的,缺乏爱的照顾的,常陷入无回应之境的孩子也一样容易被暴躁、愤怒所控制。在成长的过程中,这部分逐渐被压抑,却容易在亲密关系中、网络中和没关系的陌生人交往中展现出来。这章我想以自己为例子来说一说这事情。
我在和泽的相处中我也发现了我对他有时候会很愤怒、或不耐烦。而这也常会被其动机所遮蔽,而且动机看起来总是冠冕堂皇的。越是冠冕堂皇的关心、操心、为XXXX着急,背后就越藏有自己无法面对的挫折、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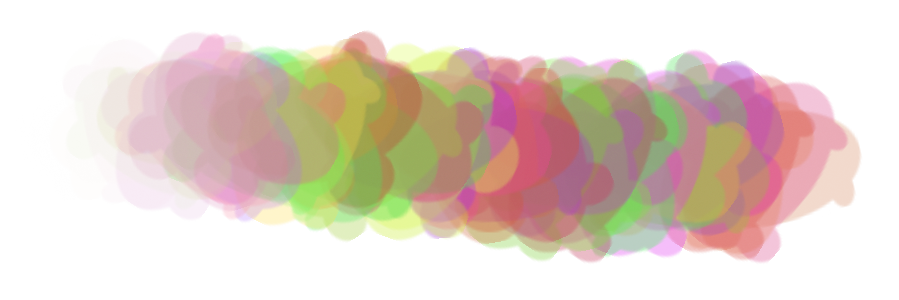
最初的时候我就老要盯着泽学习,非常焦躁于此,觉得他考学考不上,未来如何就更失控了。为此,我也做了好多次自我分析,但对无常的未来的焦虑总克制不住。这与我妈妈十分相像,她一想到我在国外与她分隔开,就常说“我要是突然有什么意外,看你怎么见我最后一面。”她以设想未来的无常,来遮掩对我离开的不满。这是无意识的,于她并不容易察觉。我也终于在一次次地面对自己的焦虑之后,意识到原来我不是害怕未来的失控,而是害怕面对自己的无能。
这察觉是因为有一天泽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了,但他get不到点,我又没有能力解释得清清楚楚。我就崩溃了,忍不住生气地说:“我已经回答了可是你却听不见!”我的怒气令气氛变得沉重。在过了一阵之后,泽跟我好言相劝,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着说,我没办法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没有办法!
我知道自己常有“全能感”,在意识还没行动的时候身体已经动了起来,马上、立刻要把事情都就位了、安排好了,也常为此焦躁,因为如果做不到,就会陷入焦急甚至愤怒之中。我也常常在与泽的问题讨论中,做那个“解答问题”的人。我无意识中以此颇为自负,因为能证明我的“全能”,但也相当焦虑,就如男性对待phallus一般,我紧握着一种假象。假象才需要时时刻刻去证明“我有”,在无法证明的时候,我忍不住焦躁、怒火中烧。但最后当我决定要面对自己时,就看到了自己最害怕的:在很多事情上,我都是无能的。脱下愤怒的防御之后,我忍不住为自己的无能而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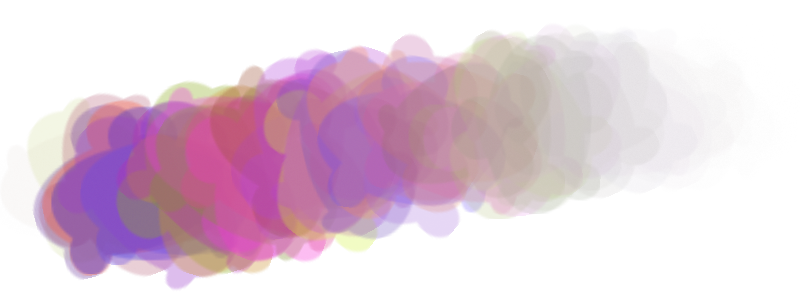
我在平时当然可以说:“人又不是人民币,怎么可能人人都喜欢呢?”或者说“人又不是神,总有不知道的事。”但我的无意识并不是这样的,我幼时的经历注定我会在一些事情上非要认定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不可,对自己的笃定是一种防御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症状,症状是来帮助稳定主体精神结构的。
这种笃定,使我坚信自己拥有真理的时候,就要将其灌输给别人。使我在认为“女权主义”是对的的时候,就以它为剑刺伤别人。对不了解女权的人,则报以冷笑、轻蔑,毫不犹豫地选择撕裂式的方式嘲讽、攻击。直到周琰问我:你希望别人理解“女权主义”吗?我至今,很感谢两年前,我们第一次网友见面时,她对我的批评。我想了一夜,决定改变方式。但这只是我骂人骂得少了的开始而已,那时候,我还不理解“理解”一词。
在写《我想你们了,我的女朋友们》的时候,我也说了我的那种着急:我这个方法才是好的、对的,你得听我的。
除了前面说的,回答不出问题时的愤怒,我在病弱无力的时候,也容易有焦躁和愤怒。比如严重醉咖啡,头晕目眩得不行的时候,如果我看到泽在看手机,而没有一直看着我,我的心里就会升起一股强烈的焦躁。如果我的要求不能立刻马上得到回应,那就更加生气起来,愤怒的火在心里直烧,就会愤怒又无力地向他喊起来:“快点!给我倒水!”
在事后,我心里又很后悔这样坏的语气同他说话,但我无法接受自己是有错的(否则全能感又遭到挑战),就会又想,是他没给我我想要的,是他的错!这些感受就在心里斗争着。
有一次我又感到晕眩无力了,我看着他为我出去买面包,我希望他快点跑步,全新全意地为我跑这趟面包店,也觉得他应该全心全意地跑回来,只是想象他在路上看一眼手机或者逗留一会儿,不是全心为我,心里就会很生气。我心里希望他为我疯狂、不顾一切、以我为中心。实际上,这也是许多女性热爱的“霸道总裁”、“宠溺文”类型小说中的特点。

我无法拦着自己心里上升的冲动,但我希望我不要被自己的欲望蒙蔽双眼。我不希望我的世界,只有泽一个人,让他承担如此之重。这并不公平。但这不是理智可以说服的,这一段自我理解并不容易。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一些自己会如此的“理论上的原因”。理论上,婴儿时期疏于照顾,或有什么变动(比如大手术)就可能导致我这样的情况。婴儿时期,由于太过于脆弱,当得到妈妈的照顾时,会十分满足,但如果母亲疏于照料,或者没有爱的目光给孩子,孩子会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在最开始以咒骂的愤怒和痛苦浮现,如果再得不到回应,那就是没顶的恐惧、绝望,是无人回应之绝境。泽常说害怕闭眼,会十分害怕,会有无限的坠落感,直到后来他说他小时候长期被一个人锁在家中,我才清楚了这缘。
等我的焦躁稍微平息,泽跟我说:不要急,慢慢来,他会在我身边。我看着他,开始了我的自述,我说:我讨厌xxx,因为她很像我,尽管交集无多,但我一想到她,心里就升起愤怒。
“我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她,是因为我讨厌我爸。我是很像我爸的,她跟我又像,这不过是一个镜像的转移。因为我爸已经死了,所以我不能对任何人说我讨厌他。我跟你说没用,你们没有交集。我想跟我妈说,跟我弟说,说我对他的恨。说他在我身上留下的那些不负责任的创伤,一个比一个重。我怀念他,可是我也恨他,恨他在过去,从来没好好地陪过我们,恨他伤害我妈,伤得那么深。又给我们留了一堆烂摊子。我是太恨了。结果他倒好,死了,痛留给我们。……”
泽就像我的分析师,我们之间有着全然的信任。在我需要他沉默地接住我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倾听者。这个倾听者,可以让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就像往常许多时候那样。而我,并不会预设他能给我一个分析师的回应,这个回应常常由我自己来完成。

我说到了我对我父亲的爱,爱他就如恨他一样,并不是容易接受的事。因为他是我家庭灾难的始作俑者,是让我妈妈苦了一辈子的人。如果我爱他,也如对自己母亲背叛了一样——尽管我妈妈常说,你们有血缘关系,你再恨他,最后他还是你的爸爸。可有一样东西停住了,卡在那。是时间。我意识到我不断地回到他去世的那个时间,或者说,我的一部分,还卡在那个时间点没有离开。过去的三四年里,我无数次梦见他复活,却保持着活死人的状态,说不了几句话,需要我们全家人的照顾,我为了他去工厂打工。只有偶尔的时候,梦见他能跟我说一些话。有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妈妈阻隔了我和他的联系,还是他阻隔了我妈妈看见真实的我。这其间的复杂,真是难以言明。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写我与母亲的关系前,必须说我与他的关系。
在梦里,他总是处在既生又死的时刻。在这场对他的恨的开端的痛苦诉说中,我发现我停留在了他去世的瞬间。他在过世前不久,他忏悔了曾经的所作所为,他意识到了他曾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就在我即将有个好爸爸的时候,我失去他了。我期盼了二十多年,就在快实现愿望的时候,我失去他了。我永远地失去他了。他跟我的外貌性格非常相似,他甚至像对儿子一样对我。我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没人认为我值得读书;没有人认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人生,除了他。在我们可以开始互相理解的时候,像双生子那样互相映照的时候,他离开了。这遗憾所形成的痛与症结并不显眼,它最开始的时候是恍惚的想念,后来又躲到梦的背后,只有在对泽哭诉的时候,无意识的语言才将我的境况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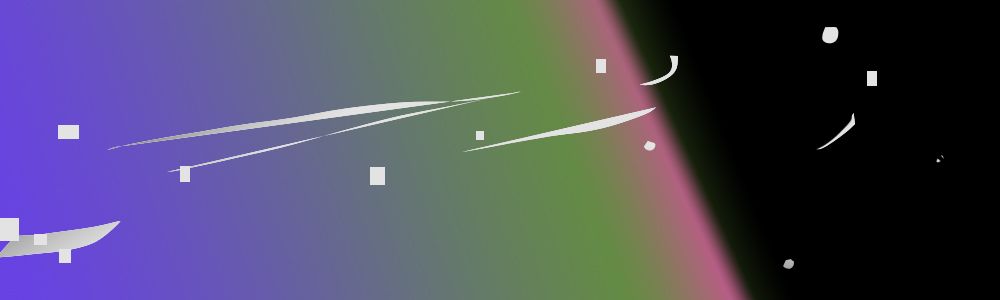
与大部分人有权威的父亲不同,我爸对我而言,他从来不是一个严厉的符号因为,他从来不着家,是缺位的。我恨了他很久,因为他带给我妈妈和我们的家庭太多伤,我曾想,他要活到八十岁,我这辈子就毁在他手里了,永远在收拾他的烂摊子。直到他得了癌症,到了末期,他开始变好了。就在我将重新开始接纳他的时候,他去世了,他终于从一个我恨的人,变成了父亲,但已经是一个实在的父亲,不可言说的父亲了。这样的父亲不存在在话语中。
当我哭喊着说:爸爸你就走吧,却在下一句用方言喊出:爸爸你带我走吧!我的无意识说出的话吓到我了。我这才听到了自己在说话,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追逐他,一个实在的他,一个不可言说的他,我一直想回到实在中去寻找他的身影。可这又怎么可能呢?最后在梦里,就卡在了那既生又死的边缘。我对他的追逐,是我的无意识所包藏的秘密。
而为什么这成了秘密呢?压抑的缘由很简单:我追逐他,就是背弃母亲。尽管现实并非如此,现实是可以相容的,但在无意识层面的逻辑,却总是简单直接的,尤其这总牵扯着童年的认知、印象。
我接受了我对母亲的背弃。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做选择是要一命还一命的,毕竟我追逐的父亲的去处,是不可说之地。这也恰恰说明了,我和母亲关系黏着程度之深:甚至我的命是与她黏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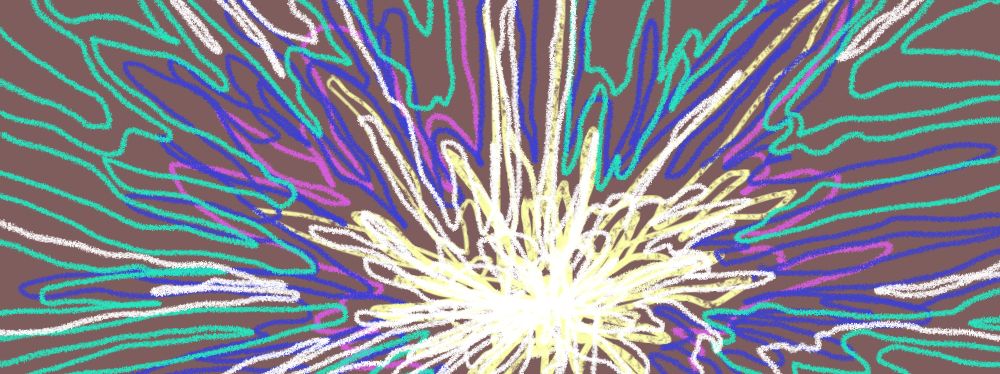
我曾梦见我带小泽回家,告诉她我谈了男朋友的事情,她很生气。现实中,她并没有生气,可是她有时候会说我,有了男朋友就忘了她。尤其我与泽来泰国,因疫情锁国的隔离后,她更常因此对我不满。我也更害怕她的不满而不敢联系她。她也因为我的联系少而更不满了。这一个负循环漩涡,我只能从我自己说起。是我没有能力去面对她对我的不满。
实际上,我非常害怕我妈妈,她若看到这句话,大概会又气又伤心,可我至今还未从儿时的家庭阴影中离开。无论我从前讲述了多少关于我与她、我与曾经的她、我与我小时候的她、我与她带来的创伤、我与她的创伤、我与她的焦虑……的故事,我还是缺乏勇气去面对她。直到此刻,在写这文字的此刻,我都还处在与她的拉扯之中。
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对我颇为溺爱。小时候,我常常生病,她要一个人带着搭车我去看病。她也没有逼迫我像别的女孩一样,学会复杂繁多的祭祀日子和细节,或者在对女儿不满意的时候给一巴掌。我小时候有好一段时间是姥姥姥爷养着的,我在姥姥村里读的小班,但也不懂如何与其他孩子交往。再长大一点,也是很久以来我对儿时的记忆,都是在野地、村子里游荡,并不记得与他人的相处。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她弃我不顾的场景。
有一次,她和全家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出去了,我醒来时,整个偌大的房子只有我一个人。我躺在客厅的地上大哭,疯狂地用方言辱骂她的生殖器,翻译过来大概是“臭逼妈妈”的意思。然后我被自己的爆发吓到了,觉得自己疯了。我的妈妈“为了我们两个孩子,撑起这个家”,我怎么能这样骂她呢?如今想起来,我骂的内容,不过揭示了我的来源之处在这父权森严的家族中卑贱的位置,而我更是在家族的权力话语中不可见、不可说的卑贱者罢了。那是无意识叫喊,是对自己不被看见的境况的爆发。是绝望的愤怒。
这类愤怒,在我无力的时候,就对着亲密的人爆发出来了,在最尖锐的时候,我会有想和泽说分手的冲动。这是一种埋得很深的应激反应,因为我想教训他,想伤害他,想让他尝尝我这滋味,这绝境,这丧失。这也是我初中时候想对我父亲做的事情,我想靠自杀来教训他,报复他,让他不再赌博,让他永远丧失,永远失去我,永远愈合不了这个伤。让他尝尝我正在承受的这滋味。让这个懦夫尝尝这滋味。

时过境迁,就如孩子对原初大他者的母亲的渴望会转移到phallus上一样,或许我对父亲的恨,有一部分也是对婴儿时对母亲的愤怒。我身体记得这无回应的绝境,但我的记忆早已消失。这比我能记事的年纪,还要早得多得多。比我妈妈独力带着我四处看病,要早得多。
我忘了我对泽说着什么,终于自己把自己引导到有记忆之前,那时,悲愤的情绪完全控制了我,我感觉我站在一个大鼓面前,门紧紧关闭。我一直哭,无力地开始锤着床,一下、一下地锤着,越来越大声,不满堆积了起来,如同击鼓鸣冤,最后我迫使自己喊了出来:看着我啊!看看我啊!
泽在旁边看着我,我却觉得他的眼睛是假眼睛,心里有要抠下来的念头——“这是假的!”,我不知道是该让他闭眼还是该让他看着我更好,但我只能哭,我锤着床,痛苦地开始发狂:你为什么听不见我!为什么听不见我!
泽问我,是想让谁听见?
我立刻就喊出来:妈妈!
我又被自己这声呼喊所惊吓,却必须直视这个答案。我不能控制自己说话,否则我听不见自己真正的声音。我听见我继续哭喊着:妈妈!妈妈!我恨你啊!我好恨啊!
我长到这么大,终于不会不被自己的恨意所惊吓了,我不再是儿时,会对自己对母亲突然爆发的恨所惊惧。我理解了恨的缘由。在我的记忆之外,我没有得到的不是父爱,而是母亲的爱。因为母亲永远在为我的父亲焦虑、悲伤。她爱他,他也伤得她很深,她结婚之后才发现一切都是谎言,但这个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地方,在这个大家族里,她处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中。或许母亲手上爱抚我,眼睛看的却是我不归家的父亲;或者由于我和父亲的相似,母亲甚至是透过我看着他,而不是看着我;或者因为我是女儿,而叹着气抚养我,谁让我不是儿子呢?原本编织好的故事、起好的名字都要推倒重来。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一开始就不存在……我就如还未降生却已经在人间生活了二十年的中阴尸。
我是不被期盼的孩子,是大家族里的异质分子,是边缘的、卑微的东西。母亲哄我时候,也常说我是沟里、垃圾堆中捡来的。我在小学时候,常常游荡于乡间,不知回家,如今知道了更严重的游荡的孩子,才知道这不过是无所系的孩子会有的症状。我唯一的那些可以证明我还属于这个家的,是我与父亲的相似。小时候我如果学他的模样走路,大人们便会一致赞赏,特别是母亲的目光也都是爱和喜悦。我与他的相像,不仅是基因,还是期盼,是被模仿的预言,是我获得位置的方式。而我与他越相像,真正的我就越不被看到,别人只会透过我看见我父亲——尽管这就是父权女儿的命运,没有父亲的名字,我们就更什么都不是了,就更不存在了,母亲没有命名的权力。可我妈妈也是这样,她的无意识之中,也很难看见我,总透着我看向我父亲。对于别的女儿而言,则是母亲在看着她自己,一种女人之间的镜像。
我曾写下的那些家务带来的焦虑、面对焦虑的绝望、身为女性的恐惧、身上父母期盼的斗争……我一点点地剖析我自己,理解其间的复杂,终于走到了这一步:认识自己并未存在的这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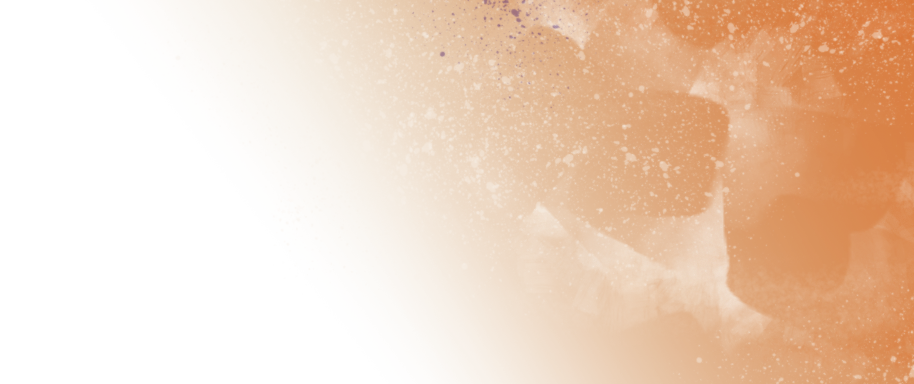
我那天哭着重新诞生了。我让泽重新喊我的名字。当我看见了自己真实的命运的时候,我只有做自己的助产士,做自己的母亲,令自己重新出生。
在那之后,我便能接受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