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Gods (上):酷儿自述,性别整合大作战
这次准备写三篇,不会特别紧凑地围绕一个主题,但是是围绕一个当前的、我所经历的结构来写的。 第一篇是关于我从小到大的性别认同斗争,最后怎样离开“男”“女”这样的二元关系。说真的如果没有泽做我的伴侣,我怕是没有幸运可以走出这样的斗争,虽然没有直说,但一个糟糕的亲密关系,对很多人的精神会是摧毁性的打击,人与人互相连接、互相看见,实在是太重要了。 其中,我一些轻微的精神分裂症状与父亲不在场的丧偶式育儿是由很大关系的,因此,我会在下一篇讲遭遇强力的、超越语言的really导致轻微发的时候,我怎样自救,以及如何重新理解我与父亲的关系。 第三篇,我打算写女性的位置。在当前的语言、话语、意识形态中,女性是没有位置、没有支持的,以至于许多女性在遭遇了不快的时候,是无法表达,即便表达了,也被冠以“无理取闹”、“敏感”“脆弱”之名。如果语言是烛光,那女性总处于黑暗之中,也被认为是黑暗大陆,可真的是这样吗?我将写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感谢:泽
图/文:ia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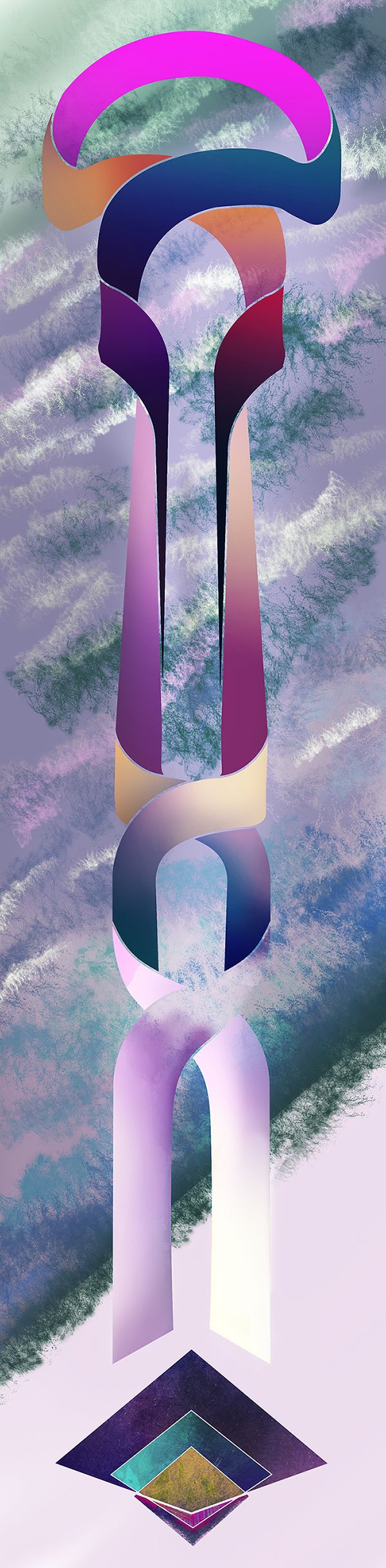
我和泽面对面坐着,他问我,我对那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无关诉求,而是,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仔细仔细地感受,却觉得胸口有一团灰色的迷雾。
这又是一个熟人性骚扰的case,放在我心里很久了。我想,只是被亲一下嘴而已,我甚至在第一时间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也看到了看到这一幕的人惊愕的眼神,也笑了笑没当回事,转身亲了一下泽,还是忍不住,擦了擦嘴,就走了。
我想了想,说:我好像也并没有想让对方道歉。
泽说:不是让对方做什么,而是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的位置在哪?去哪了?如果你自己没有做到拒绝,那之前那些关于拒绝的工作坊,真的能为别人带来改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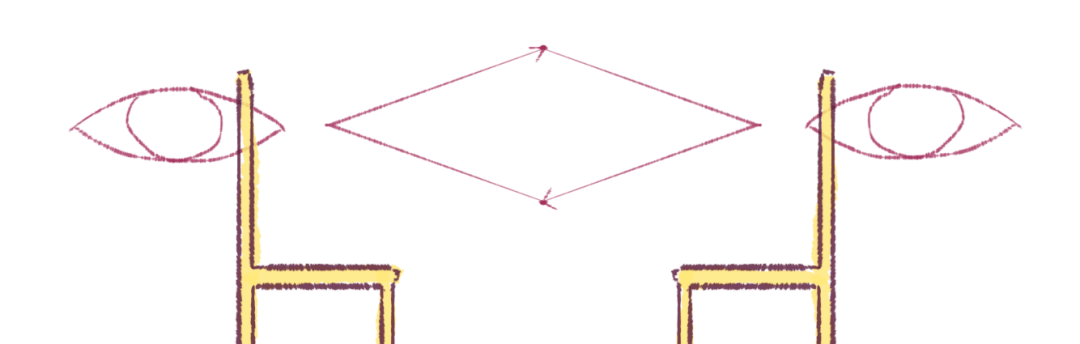
我听了很迷茫,非常地迷茫,我知道答案是:我该拒绝。可我似乎没有什么动力去拒绝。回想起这件事,我会一直想起自己擦嘴时候的动作,和那个人惊愕的眼神。可我追溯这件事,要再去做什么的动机在哪呢?
泽说:没有动力,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真的不在意,又怎么会因为说起一个梦,就又一次提起?
我知道自己身上有着一种巨大的惯性。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个文化带给我的。在那样的一种文化里,面子一定是最重要的,尤其在待客时,时常弥漫着表面的和气,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知道客人要什么。那样的一种惯性,塑造了我,也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就像戴久了的面具,也会被当作是自己的脸,当泽问我,我真实的想法时,尽管有泽这样的镜子,我依然竟只看到这一面具,而看不见自己的脸。
这件事,引发了我一个深深的问题:那种情况下,我在哪?我的位置呢?我的感受呢?我的诉求呢?为什么我只能被这样的惯性控制?我在害怕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害怕自己成为女性。
尽管我曾经认为自己是女性、尽管我的境遇是女性的、尽管女性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但当我意识到自己被推到一个被欲望的位置时,我还是害怕。
这和我的经历有许多关系,有几次的性骚扰都让我害怕女性的身体,觉得女性的身体被人觊觎的、垂涎的肉。因此,在那些经历之后,我疏于打扮,让自己邋邋遢遢的,举止还十分粗鲁。另一个是我母亲的遭遇,她惨烈地示范了做一个女人,在我们那儿,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却要始终忍受着奴役,这让我十分害怕。( 详见作品中的家务焦虑一文 )
我还记得,我小学时候还认为自己是个女孩,我爸唯一一次带我去理发店,给我理了短发,我哭了一下午。
长大后,在几次的恋爱或暧昧中(除了和泽),尽管我平时生活并不表现得像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可在一旦进入关系中,我要么都是女性的面貌,要么为了这段关系而呆在女性的位置,将自己定义为被欲望者甚至是一个辅助者,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攻击性,表现得可爱、可亲。我没法否认那时候我如何表现得和所有的“小女人”一样,并不是假装;也没法否认我剪掉长发的那天,如何松了一口气:“我终于不用再装成女的了。”
我的性别认同斗争一直伴随着我,一直到去年夏天和泽在一起后,才慢慢卸下这些包袱,不再因为自己“不像个女的”而焦虑不已。因为他不会认为,我不化妆、看起来像个男的、讲粗俗的黄段子、像大老爷们那样走在乡下的路上有什么问题。甚至,我尖锐的攻击性,在他那儿,是受欢迎的。我不需要假装可爱,不需要为了维持关系什么都不说,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承担、面对、焦虑关系中的问题。
回到那个场景里,我重新思考为什么我在被性骚扰后立刻被惯性所攫住,用一种“笑笑无事发生”的态度去处理。我回看自己,感觉自己就是面目不清的、是一个模糊的人(想想我一贯在朋友间所张扬的个性);感觉到自己被放置的位置,是让自己害怕的、女性的位置。
或许,我在无意识中,将“被性骚扰”与“女性外表、女性位置”联系起来了,把这两件事、焊接成了一个逻辑链。那时候我和泽已经在一起了好一段时间,我也确定我的性别认同是queer,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也不认为我对直男会有性吸引力。可我依然被一个直男性骚扰了。我依然被推到了那个位置。

有些女性害怕作为女性,但她们仍然能是(狭义上的)女性。我在和泽讲述我的过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长期的性别认同的斗争,并不仅是因为我的害怕,还因为我母亲会在我身上寻找我父亲的影子。
几乎大部分的人,在人生之初,是与作为原初大他者的母亲融为一体的。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的所欲的、母亲指认的,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着孩子。
我听精神分析师朋友讲过一个伟大的人,她是一个trans gander,她的身体是男的,心是女的。那个人来找我朋友,想要做分析,她说,她被生下来是母亲为了指认强奸犯的。我朋友拒绝了她,他说:她这样的情况,没有杀人、没有自杀,而是形成自己的症状(也就是否认自己的身体性别)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伟大的人了,以他的能力,没有办法给展开她做分析。不仅是这一个case,还有许多不同的case,启发我去重新发现我母亲的目光看着我,到底看向何处。
(不得不说挺悲哀的,国内父母很难将自己的欲求与孩子分开,使得孩子本身被遮蔽了,在原生家庭中,做不得自己。)
我妈妈她总说希望我像我表妹那样,在家可以帮她做家务,也早早地订婚、出嫁,成为个媳妇儿。可实际上,她一直在我身上寻找我父亲,一直在我身上看到我父亲。
她常常说:你的脚丫,从出生时候开始,大家就都觉得和你爸一模一样的。就连骂我的时候她也说:简直和你父亲一模一样。她会因为来自大舅的压力,希望短发的我去外婆家的时候化个妆、穿个裙子,并为此焦虑不已。也会拿着我的照片,跟我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拼在一起,看看这一模一样的外貌、神情。
我知道,我在两性关系上,曾经认同的是母亲的女性的位置,可我无意识中也想成为我母亲所欲的样子,这是大部分人在婴孩时期都会做的选择。
小时候我要是像爸爸那样走路,我将得到多少母亲的注视和夸奖啊。
那么,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去成为父亲呢?

小时候,每当我在妈妈承受我父亲带来的痛苦和撕裂的时候,会在无意中在捕捉着她所希望的。她会说:希望我和弟弟乖乖的。她会说是为了我们姐弟,她才没有离婚。后来,“乖乖听话”的魔咒是令我窒息的一大惯性、是她的焦虑与我联系在一起的通道,是我盘扭在我内在的一个结。小时候,我还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想可以保护妈妈,可我那么弱小,也只能做到否定父亲,如果我要“乖”,那我必须否认他,否认我们相似的脸、一样高挺的鼻子,一样形状的双手、双脚,和一样的个性。他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
终于有一年,或许是2015年夏天,我父亲的所作所为,也让我终于爆发了对自己身体中有父亲的一半基因的厌恶。这样强烈的厌恶与痛苦直接带来了幻觉的出现,我感觉到自己的一半变成了蜥蜴,冷血极了。所幸时间很短,而我赶紧地向朋友求助,通过诉说,重新编织自己的感受。
后来父亲因为癌症去世了,我也在妈妈照顾他的期间,发现妈妈其实一直很爱他,说为了孩子不离婚,是一种痛苦的说辞,尤其她并未得到过我父亲的爱情。我父亲在生前也有后悔,当然,我所知的也只有一句话。以及,他对我剪短发,大加赞扬,觉得好看极了(当然是因为我看起来更像他了,他是个自恋的人),我母亲只能接受这件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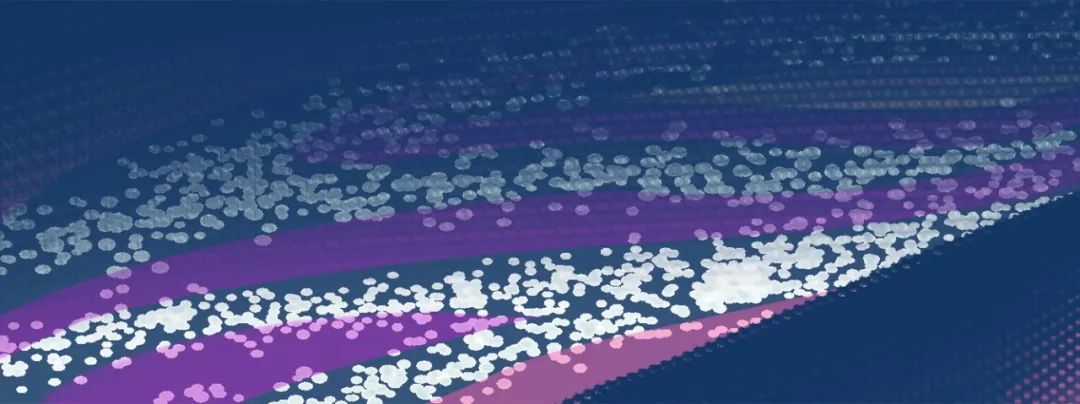
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年夏天,我十分消沉,在一些关系中,我惯性地呆在女性的位置,这使我心里不断地升起无法消解的冲突。那时,我心还未宽广,不能容纳那么大的结盘踞其中,更别说观察它们了。那天我终于起床,去照镜子的时候,被一种巨大的、尖锐的焦虑穿透了:我认不出镜子里的人是自己。可那应该是我,不是吗?我试图做些什么,摆什么表情并没有用。我只能庆幸我长得像父亲,因为在我将头发剃短之后,我借助我父亲认得出自己了,认得出那个像父亲的自己了。一样的高脑门、一样的一大一小的眼睛,一样的高鼻子,一样的大嘴巴。
我会有这样的解体,或许是因为这成长过程中,始终处在在在二元的性别结构中矛盾的指向和家庭的冲突,只能成一个四不像的、面目模糊的人所致的。我那时还不知为什么我时有要剃头的冲动,如今看来,只是想召唤父亲的返回,请逝去的他帮我稳住自己,毕竟我不能否认,他的死亡与 他在我身上的那一半血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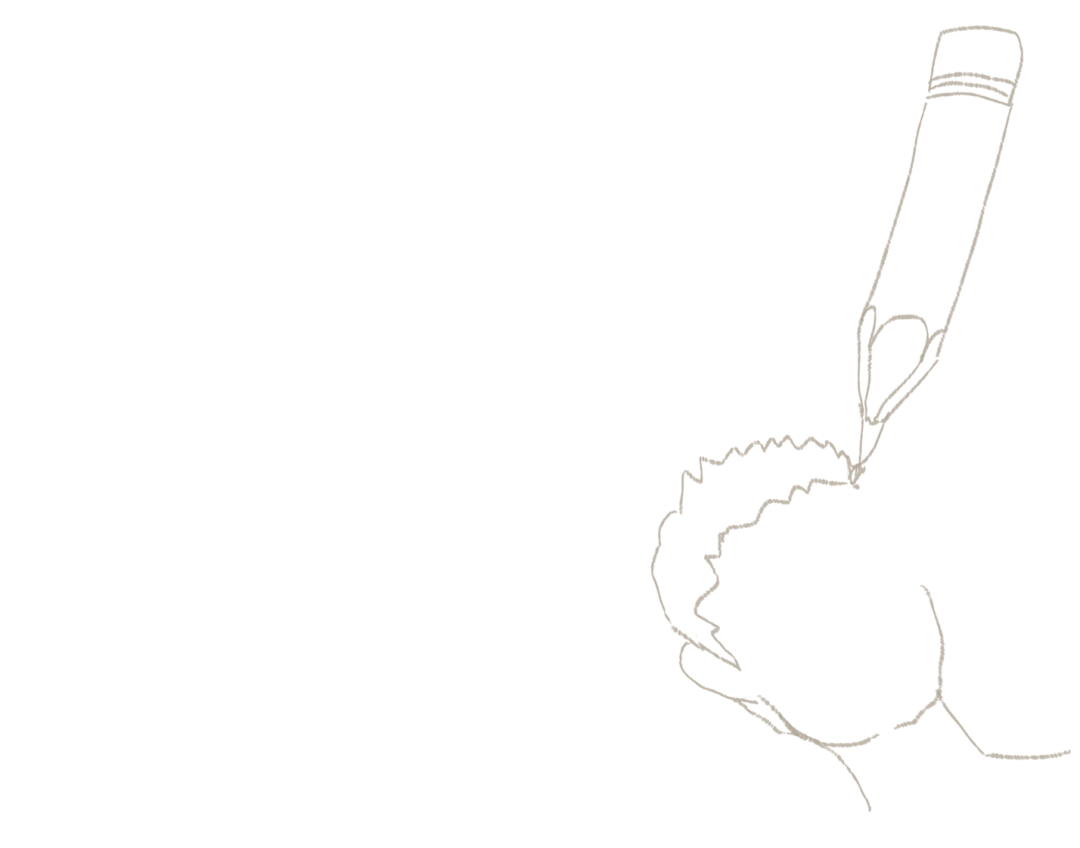
在认识了泽之后,我以为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以为我可以很明确自己了,确定自己是个queer,确定自己的偏好,确定自己可以坚定地拒绝那些性骚扰——以queer的身份。
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多年的好友:你觉得我是女性吗?她说:是吧,毕竟你没有过上男的那种生活,而是跟别的女的都一样。
她说的极是,无论我的性别认同是什么,我的境遇,依然是女性的。我依然有很多泽不会面对到的约束、礼教和恐惧。泽说了她的一个姐姐,一个出了国去了上海工作的女孩,因为父母的召唤,回到了偏远的北方小城,嫁给了当地人。她对父母的顺从的惯性,与我“一笑而过”的客气,是一样的。也和那些为了场面,从不做任何看起来“有伤和气”的人身上的惯性,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惯性,是一种麻药,轻轻松松的,让我们不知觉的时候忽视了自己,麻醉了自己,也成为了自己摘不下的面具,也成为了酒席压迫、酒席性骚扰的共谋者。还让我们,会害怕、会恐惧,会对成为焦点感到惴惴不安,会害怕那些真诚的表达、害怕就事论事地说话。而我,想把这样的惯性从自己身上撕裂出来。
我在跟泽讲完了我的性别历程后,感觉到了一种彻底的离开。我不需要成为我母亲所欲的,也不需要认同母亲的位置。男或者女,这种二元的位置是可以破除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也已经没什么好执着的了,这是我曾经的经历,是父母的事情,之于我只是一个起点。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