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 | 撐起傘,陪他走一段
四、五年的專科訓練,能讓一位年輕的內外科醫師成為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但精神科醫師的訓練能給你一次機會,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阿布
《萬物皆有裂縫》是阿布寫自己作爲一介凡人,如何理解凡人,理解各自生命中的裂縫,以及艱難。雖然完美的同理並不存在,但阿布透過挖掘自身的經驗,來試圖接近受疾病所苦的人。
《萬》也寫阿布作爲精神科醫師的存在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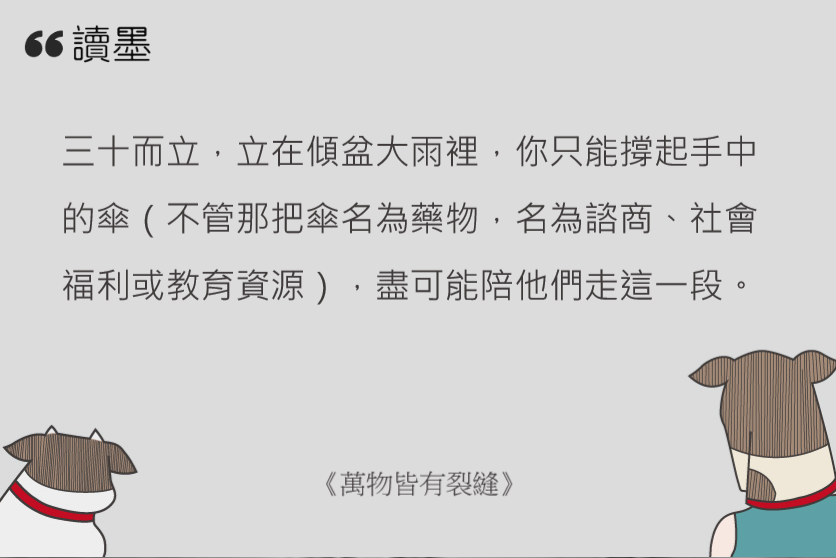
他寫自己如何運用精神醫學去陪伴疾患。可以的話,他想成爲微小的光,滲透進萬物的裂縫,也希望自己能像水一樣的,溫柔地浸潤每一處心靈。通過這本書,他帶著我們瞭解他人,瞭解疾患,而不是獵奇。他想讓讀者更理解精神醫學和醫師的作用和局限。
阿布是作者,也是個精神科醫師。這樣的身份難免帶著拉扯。書寫要如何介入而不涉入,如何保持距離卻又不疏離,一直是他思考的問題。
寫出《萬物皆有裂縫》之前,他以實習醫生之眼,寫出了《實習醫生的秘密手記》(2013年出版),另一部與醫療有關的,是替代役時期寫的《來自天堂的微光》(2013年出版)。
如果說《實習醫生的秘密手記》和《來自天堂的微光》是帶著距離寫作的,那《萬物皆有裂縫》則是阿布當上精神科醫師,貼近而涉入個案的種種經驗後,反思自己的字究竟可以做到什麽的書寫。當他人的經驗真實地呈現在眼前,不容躲避,而自己將如何傾聽,如何理解呢?
原來,《萬》寫的不是疾患,而是醫師本身。那是阿布作爲一名凡人醫師,如何運用自身有限的經驗和能掌握的知識,去傾聽、去理解疾患,進而理解自己的書寫。

阿布説自己在2018年通過了可能是他人生中難度最高的精神科專科醫師考試。備考時經歷的不少自我懷疑和艱難,讓他想把這段日子記錄下來,於是他寫出了《萬》中〈當自己也走過一段〉。
從這篇開始,阿布挖掘自己,從自身的經驗和反思開始理解並接近疾患。當自己也走過一段卡住的時光,阿布寫:
與人生中許多意外比起來,專科考試失利根本不算什麼。考過考試,又將回到計畫中的人生,但我們很多個案是過不去的;先前的人生走到這裡,就此被卡住了。準備過煎熬的專科醫師考試,或許在未來遇到因為種種原因走不下去的人,可以想起當年被卡住的自己;讓我們能夠慢一點,在困頓的時光裡,陪他走一小段。
精神科醫師的陪伴是傾聽。可傾聽從來不易。聼的和說的人都有太多的執念和偏見。人們的耐性往往有限。對於卡住的人更是如此。
卡住的時候,腦中循環播放的,是那些過往中的傷害、懊悔、場景、已經無法挽回的現實、十萬個爲什麽。發生過的事並未真正過去。「每一個現在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無限輪迴。」作爲精神科醫師的阿布,在《萬物皆有裂縫》中這樣寫卡住的人:
遇見過一些受傷的人,生命被困在過去裡迷了路。那裡是時間的廢墟,可能性的掩埋場。在過去裡只有不斷重複受過的傷,追不回的場景,無法修復的懊悔。他們在恐懼裡入睡,尖叫中醒來,對於活在過去的人來說,每個現在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無限輪迴。
安慰來得如此遲緩而不濟。「看開點。」「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多想想開心的事。」「忍一忍就過了。」「向前走。」「不要再想了。」説這些話的人懂什麽呢?
說安慰話的人不知道,卡住的人就是卡住了,人就這樣不上不下的,過不去也回不去,只能在縫中等待救贖。卡住的日子什麽時候會過去。不知道。過不去的話,只能繼續動彈不得。永劫回歸。卡住的人知道,那些安慰人的話語,已經是最大的善意。只是無法接受。世界卻要你接受。不許反抗。
這時我想起阿布寫約束帶:「你有一指幅的自由,但當你抵抗,拘束只會愈來愈緊。」面對世界種種的荒謬,他人的眼光和偏見,你只有一指幅的自由。抵抗只會讓你更不自由。只能接受。接受世界就是如此瘋狂。而他們卻以爲你是瘋狂的。
精神醫學是危險的。醫師一個不小心,也會深陷地獄。可阿布願意走近。願意傾聽。願意敞開自己,和另一個靈魂碰撞。阿布寫:
心理治療像是兩個靈魂互相碰撞,互相砥礪磨合;在尚未對自己內心轉角與凹陷處的陰影有足夠了解之前,治療師很難帶個案展開一段柔軟且有彈性的旅程。
或許此時每位治療師所不欲面對的陰影不再來自個案,而是映照出自己的內心。也因此治療師才需要同儕的督導:有時候他人的地獄,時間久了也會成為自己的。
治癒他人之前,要先足夠瞭解自己。可我們又何曾足夠瞭解自己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如同疾患的標籤無法涵括所有人的經驗,我在這裡所描述的,無意、也無法代表每一個人去發聲。
身爲精神科醫師,阿布不會對他人妄下判斷,希望讀者也如此。
以上,首發于開根好。文字略有增訂。
以下碎碎念
後記
阿布是作者,也是醫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醫者有。疾患也有。要如何描述、詮釋、轉化疾患的經驗而不僭越不臆測不妄下判語?好難的。所以《萬》這本書有拉扯,有詰問,有疑惑,卻始終很溫柔。對於自己不瞭解的經驗,阿布試圖走近。不帶成見的。
醫學是依據病徵而建立的empirical studies,沒有苦痛就沒有醫學。醫學本就是門負疚的學科。或許文學也有這種特性。阿布說。
無論多想將自己還是他人的苦痛化成真誠的文字,終究還是會負疚和存疑的吧——記憶到底可不可靠?講述起來會不會失真?若是他人的故事,旁觀的人是否有權描述、詮釋、轉化甚或挪用?
不能寫的時候,他用傾聽陪伴疾患。那段日子,他重複著醫者的日常。可重複中卡住或流動的人事,他沒有錯過。他看見事物的光譜與兩面。約束帶是保護也是限制。鑰匙是權力也是責任。精神科醫師可以陪伴也可以審判。
得到病房的鑰匙后*,阿布發現病房很安靜。「 精神疾病或許是最安靜的病了」。可這樣的安靜和沉默底下藏著什麽?
阿布知道,關於疾患的書寫,「 永遠都不是只有一個人能完成的故事。」
但他試著從自己的經驗開始,試圖接近與陪伴疾患。就這樣一晃5年。
在「傾聽」和「挖掘」之後,他準備好「呈現」了。
那些沉默底下的暗湧。那些卡在縫中的人。
那樣的日常教會他的事。他都可以寫了。
讀完後你會明白,They are Us. 如果你也曾卡住。
*不是意象。住院醫師要記住每一個病人的名字才能得到病房的鑰匙。
又
這篇文很硬。
有些字寫得斬釘截鐵。有些地方在繞。
可文字騙不了人,無論是顯露或隱藏的部分。
這篇聼Enno<就算我放棄了世界>:
Btw讀了這本書我才發現嗅覺可以喚起深埋的情緒。
阿嗅這個筆名算是取對了。( 都看到這裏了就讓我跑題自high一下 )
什麽時候我也可以如實面對和呈現這些和那些情緒呢。(詩人假牙說:到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