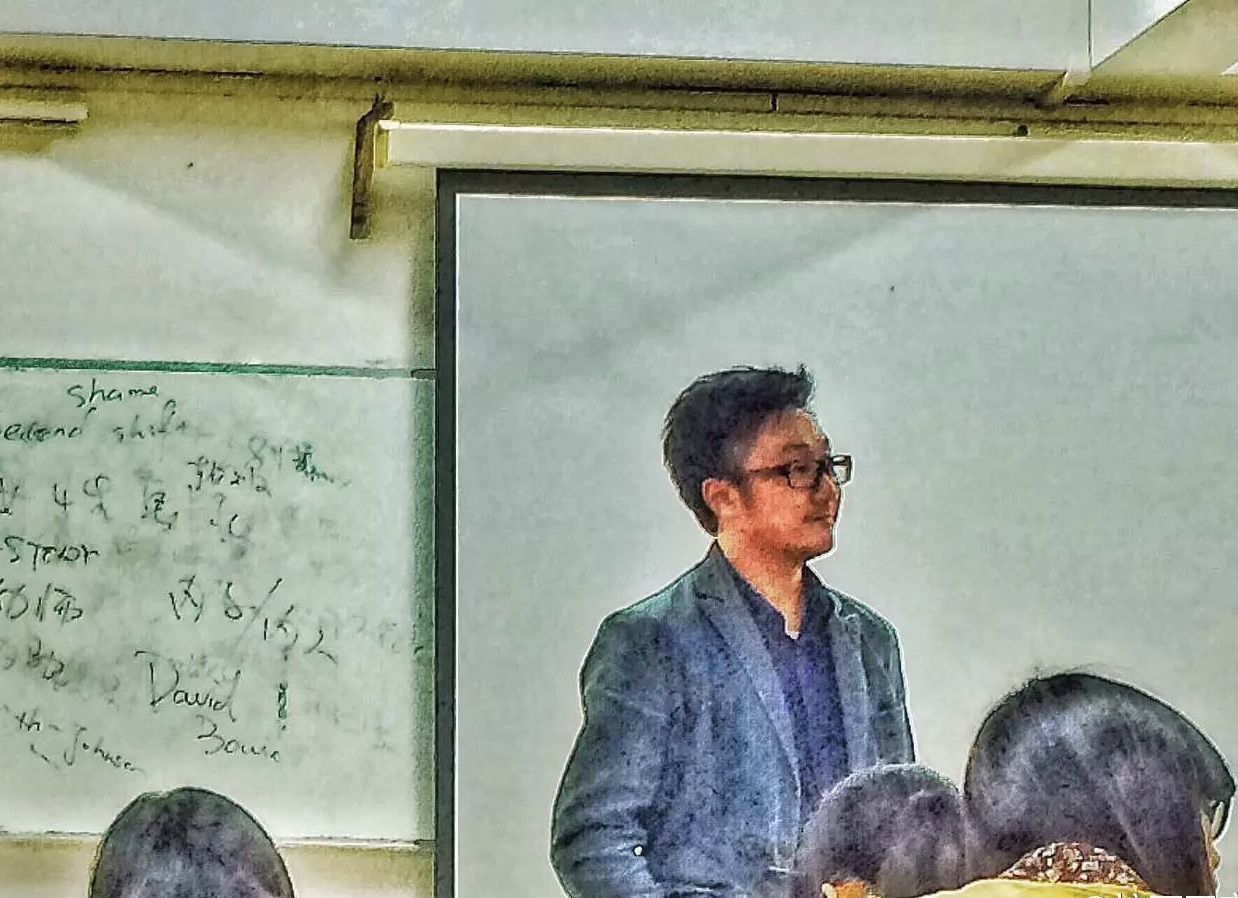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科学的描述是完全中立,还是渗透价值?
科学与女性主义
我们今天越来越有意识地去纪念那些曾经被排斥和被遗忘的女科学家。科学界开始承认她们的重要性,流行电影如《隐藏人物》和Google Doodles的居里夫人诞辰等,也提醒我们去记住她们。对女性在科学中的贡献的承认和重视,与女性主义运动分不开。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科学史研究者记录下历史上科学从不间断地排斥女性的证据。对科学学科形成有重要贡献的女性手工艺生产者和参与者一直被科学体制边缘化和排挤;直到上世纪中后期,女性一直极少被科学界和大学的科学专业接受;就算获得科学承认,女性科学家在各个领域中都是少数。[1]像法国科学院当年竟然拒绝获得诺贝尔奖的玛丽·居里加入,就匪夷所思。
科学实践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实在过分常见,在训练、研究、重视程度等等方面,女性都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科学之外。因此,女性主义运动的首要批评正是科学体制对女性的系统性不平等:科学的体制结构、科学实践、研究议题等等,都充斥着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价值和预设。这些问题涉及科学对女性的公平问题,所以女性主义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也被称为“公平性批判”(the equity critiques)。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公平性批判尽管也受到很多争议,但这些批评只关涉科学中“外部”问题,并没有影响到科学的内容,似乎也较容易让人接受,毕竟这不只是科学的问题。
然而,当科学实践充斥着性别歧视,我们很难不去担心,科学不仅仅只是制度和实践上充满男性中心预设,而是内在地性别主义。我们会担心,科学在内容上,从科学方法到科学结论,都充满系统性的性别偏见,因此科学不仅仅只是在外部问题上,甚至其内部都受性别歧视影响。于是,女性主义不仅对科学进行公平性批判,还希望对科学进行内容的批判,质疑受性别偏见影响的科学知识的可靠性。
女性主义运动对科学的这种批判引起更大的争议。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会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应该远离科学。流行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处理的是事实,是真,这是科学得以获得权威地位的基础;而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价值,是“应该与否”的问题,这正正是科学应该避开的问题,因为科学需要中立于社会和政治价值。于是乎,对于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内部批判和影响,大家会保持质疑态度,甚至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就应该远离科学。
女性主义科学批评和女性主义科学
女性主义是不是应该远离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内部批判或影响是怎样的。
既然对科学的担心主要集中于其所可能包含的性别偏见,女性主义的影响和介入也可以根据其如何对待这些偏见或者权重(bias)进行分类。根据Elizabeth Anderson的说法,女性主义对科学的介入可分为两类,女性主义科学批评(feminist science criticism)以及女性主义科学(feminist science)。Anderson认为,如此分类也符合女性主义对各个学科介入的历史:从对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预设、理论等进行批判,而后也建立起自己在该学科的方向。[2]按此说法,女性主义科学批评首先是对科学中的性别偏见进行审视和批评,而女性主义科学则是通过对性别的不同权重创建新的研究主题和方法。
女性主义科学批评主要集中批评科学中因为存在男性中心和性别主义偏见而导致的错误,一般来说,包括以下五种主要的批评研究[3]:
- 研究科学中因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科学家而导致对科学进步的阻碍。例如,因为密苏里大学并没有给予Barbara McClintock支持,甚至在教员会议中排斥她,没有提供她职称、资源,甚至没有提供获得研究生的渠道而导致她发现基因转座(genetic transposition)的突破性研究推迟进入生物学研究主流。
- 研究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如何对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造成损害和不平等对待。例如,优生学,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中通过为男性提供比女性更多的训练和资源而强化性别等级。这些问题很可能源于这些学科中的种族偏见或者对女性的工作(包括家务工作)对经济贡献的不平等看待。
- 研究科学如何忽略女性和性别,并且研究科学如何可以通过关注这些因素而获得更好的理论。例如Hays-Gilpin和Whitley所编的《性别考古学读本》中所记载的例子,以及Pamela Paxton发现,在政治学关于民主与选举的研究中,投票者常常默认为男性选民,忽略女性选民,进而对民主发展的研究产生偏差。[4]
- 研究所谓“男性”思维模式如何损害科学研究。例如Carol Gillian的研究对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发展模型的批评,指出Kohlberg的对道德成熟的模型基于一个全男的样本总结,认为他们才是道德成熟的标准模式。她认为,Kohlberg得出的研究结果忽略了人类道德发展的重要部分,那就是女性的部分。[5]
- 研究进一步增强了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的对性别的科学研究如何没有达到科学的标准。例如著名的所谓“狩猎者-采集者”(“hunter-gatherer”)区分,不过是重复性别二元区分所带来的刻板印象,研究表明,应用这种区分的很多研究采取很多双重标准。女性在到处收集的过程中,不仅为集体带来占总食物近70%的猎物和植物,在收集过程中获得的动物猎物会被描述为采集,而男性同样行为获得的动物猎物则被称为狩猎。[6]
女性主义科学批评尝试表明,许多科学中所包含的偏见常常会引致错误或不被证成的结论。而女性主义科学则尝试通过论证某些合法的(legitimate)女性主义价值权重,为科学研究带来新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方法上的新发展。
比如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与传统不同的研究方法。许多女性主义科学家认为,既然以往的研究方法常常忽视社会中重要面向,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法或许贡献更大。例如,采用短暂证据——日记、私人作品等非公开档案;采用非标准方法——如在惯用定量方法的领域使用定性研究(对女性的经验报告只使用定性报告而拒绝概括是其中一例[7]);在理论选择中,除了准确性、简单性、内在一致性等等标准外,使用一些来自女性主义理论的标准,比如本体论多样性(ontological heterogeneity)——强调科学取样和观察中对象在本体论上的多样性,用以允许对组内差异的观察,以及抵制将差别(difference)直接看作为异常(deviance),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对分概括,允许正常值具有范围;又或者关系复杂性(complexity of relationship)标准——用以允许理论具有更有解释力的因果模型,例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应该表征人类的各种潜能,能够解释不同个体因应理解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行为等等。
女性主义科学家是科学实践者,所以她们并不只是对科学研究采取失望和放弃的态度,而是通过提出新的方法来提高不同科学学科的可靠性。
不管女性主义科学批评还是女性主义科学,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主义价值被带入科学之中,作为价值标准来评判以及指导科学实践。这些价值对科学的直接介入,正好是很多学者呼吁女性主义运动远离科学的原因。
事实与价值
反对女性主义价值介入科学的第一个理由,来自哲学中最著名的一个区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在哲学中,价值判断都是规范性的(normative),是关于“应该与否”的判断,它们采取的形式是“事情应该如此这般”。另一方面,事实判断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采取的形式是“事情如此这般”。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同类的两种判断,我们不可能逻辑上有效地从“事情应该如此这般”推出“事情如此这般”。
同时我们似乎普遍接受,科学关注的是事实和真,科学中的结论和判断都是关于世界的描述性判断,这是科学之所以具有权威可靠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判断之所以可靠,在于科学判断是通过逻辑有效地从证据获得的,要表明一个科学命题为真,在科学中就是要去展示,这个命题得到证据的有效推导。
因此,就算公平性批判是恰当的,女性主义对科学内容的介入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女性主义价值并不能够有效地推出任何科学的事实判断,当然也就不能在证成或反证一个科学理论中起作用,否则就会如Susan Haack所说在科学中出现想当然(wishful thinking)[8]。
这个论证十分常见,其关键在于我们似乎普遍接受的前提:“事情应该如此这般”不蕴含“事情如此这般”。然而,这论证是值得质疑的。且不说在规范研究中,我们同时也普遍接受“应该”蕴含“能够”——从规范判断有效推出关于能力的事实判断,这一前提最多能够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仅仅价值判断本身不能推出事实判断,因而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证据和辩护。但是,如果结合一系列背景预设,比如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世界观,从“事情应该如此这般”自然能够有效地推出“事情如此这般”;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皆带有向地的目的,因此物体应该往下跌,于是乎,放手后物体自然跌落地上。
当然我们未必会接受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世界观,不过,这不等于说科学背后的预设中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根据Quine的不充分决定论题(underdetermination thesis),任何科学观察只有在与背景预设结合时才能成为某个科学假说的证据,如果改变背景预设,同样的科学观察可能会支持另外的不同假说。所以,在证据同样充分的情况下,不同的背景预设之间是平等的。于是乎,科学家在选择不同的背景预设时,她们被允许甚至需要使用各种价值作为选择的标准,比如简单性:(其他条件不变)选择认知上最简单的理论。同样地,科学家也被允许根据女性主义价值去选择科学理论的背景预设,比如本体论多样性:(其他条件不变)选择本体论预设更多样的理论。
除此之外,Hilary Putnam认为,在信念网络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运作并无二致,价值判断会在背景预设中为事实判断提供支持,反过来,事实判断也会在背景预设中为价值判断提供支持。在信念网络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整合在一起,并没有明确区分。[9]因此,事实与价值在科学里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明显二分。
借助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来反对女性主义对科学的介入事实上并不成功。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至少发现,科学理论的选择和辩护实际上留有空间足以让价值在其中占据角色。
真与科学的目标
反对者或许会承认,科学理论的选择的确会为价值留有空间,不过这些价值并非女性主义所倡导的道德和政治价值。Thomas Kuhn认为,根据证据选择理论的时候,的确需要援引价值,不过这些价值都是认知价值(cognitive values),比如上文提到的准确性、简单性、内在一致性等等[10]。所谓认知价值,通常指的是一些技术性价值,用以帮助理论更好地获得真。在这些价值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证成和否定科学理论。而女性主义价值包含的是道德、政治价值,按照Quine的说法,这些价值不在经验控制(empirical control)之下,所以不能在它们之间做出事实或理性判断。
这个论证也常常被援引来为所谓“科学的价值中立”提供支持。很多人认为,科学理论不应该蕴含或者预设任何非认知价值,科学也不为某种非认知价值服务。科学以求真为目标,因此,科学应该保持中立,并且在各种非认知价值的冲突之间保持不偏不倚,否则,正如我们在各种极权社会中所见到那样,科学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奠基在这个论证下面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念,即科学以追求真为目标,以追求事实为目标。我们应该将科学理论的目标限定在厘清真与事实,而非认知价值判断对这个目标没有任何作用。[11]
这个反对女性主义介入科学的论证看似有力,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这个论证对所谓非认知价值的看法是可疑的。道德、政治等价值判断都会涉及各种事实判断,并且常常以事实判断为基础。对行动是否符合道德原则的判断,自然与关于人的能力的判断相关;对正义的讨论也离不开对社会环境的事实判断。我们批评那些天马行空的价值判断,理由也多出于其与实际相差太远。Quine对价值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似乎将价值完全置于理性范畴以外。价值并非如Quine所说完全脱离于经验控制。
另外,介入科学的女性主义道德或政治价值同时也具有其他认知价值的作用。比如Helen Longino认为,作为政治价值的权力分散(diffusion of power)在科学中也具有认知价值的作用。[12]权力分散指的是将权力/力量转移到更多参与者身上,比如在国际政治中让更多力量或影响较小的国家参与到本来只有少数几个大国决策的领域,又如在国内制度中让更多少数派代表参与到以往仅几个大势力玩家的决策程序之中。在科学理论的选择上,权力分散的作用可以跟简单性做比较。权力分散和简单性都不是导向真的价值,但是它们都能够使理论变得容易被认识,使理论容易被理解。符合简单性标准的理论拥有更少的理论假设,因而更容易被掌握。同样,符合权力分散标准的理论可以让不同条件下的认知者通达获得,因而理论更容易被认识到。又例如上文提到的本体论多样性以及关系复杂性,作为认知价值可以让理论拥有更准确的科学分类以及更准确的解释模型。[13]
女性主义当然不反对科学以求真为目标,这是科学很重要的内容。不过,以求真为目标并不排斥其他的价值同时成为科学的目标。科学不仅仅只是事实的堆砌。科学理论会对事实进行挑选和整理,用以表征研究的现象。如何挑选和整理,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本身需要价值。
假设一个关于奴隶制的理论,里面包括所有有关奴隶的事实陈述,这不会是一个关于奴隶制的好理论,反而会将奴隶制的重要事实掩盖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细节里。同样,一个关于奴隶制的好理论,也需要包含各种道德价值和道德判断,譬如,一个描述奴隶制的好理论对于使用“鞭打”还是“劳动动员技术”必须作出选择,而这选择不可能中立,没有价值判断,否则不可能是关于奴隶制的好理论。[14]所以说,排除价值的理论,也可能是不能获得真的理论。
又例如关于失业率的研究,同样预设不同的价值。通常来说,失业率计算的失业者是那些没有从事有偿工作但正主动寻找工作的人。为什么不包括例如那些已经因失望而放弃找工作的人呢?标准说法是因为只有主动寻找工作的失业者才能为工资水平(wage rate)带来下降压力。失业率也反映出这种与工资水平的因果关系。这个研究显然与政治价值和追求相关,同时也会导致其他的价值预设,例如贬低非全职工作、贬低家务劳动的价值,或者同时排除那些只进行最低工资报酬的低技术工人,或者反映出一种“失业但应得到帮助”的模范。[15]所以说,科学理论需要不同的价值来决定其研究方向,并且预设不同的价值。
科学以真为目标,并不能够得出,其他价值目标必然会对科学求真产生竞争,因而影响科学求真。科学求真,同时也是追问问题的答案。科学并不是事实和真的随机组合,科学研究需要有研究的问题,价值在此可以为研究提供方向,并且,如上文所述,提供挑选和整理证据的方法和标准。女性主义价值介入科学,并不等于会替代了证据、逻辑等等的认知作用。价值和证据可以在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在科学中充当不同的角色,价值并不必然与证据竞争决定结论。
所以,Anderson提出了一种二元科学证成标准。科学理论需要满足知识论要求,例如明确的科学分类标准、合理的因果解释、充分的证据等等,同时科学也需要满足非认知价值的要求,比如认真审视其预设的非认知价值,理论是否能够与这些价值一致等等。科学理论的证成需要同时在规范性和证据性层面进行。[16]
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请女性主义运动远离科学的呼吁并非那么容易可以获得辩护。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外部批判或者内部介入,都有着很坚实的论证支撑。或许更准确的应该是关注女性主义如何介入科学是最恰当的。
进一步关于女性主义与科学,包括不同的具体女性主义科学家在实践中如何根据女性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女性主义对科学中的客观性概念的批判和反思;包括女性主义对更具体的科学方法的批评,例如对证明标准、科学分类、科学叙事等等的反思。同时,女性主义如何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恰当使用和带来成果,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女性主义与科学的讨论,似乎远未结束。
[1]Londa Shiebinger, 1989, 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2]Anderson, Elizabeth, 2015,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3]Ibid
[4]Paxton, Pamela, 2000, “Women’s Suffrage and the Measurement of Democracy: Problems of Operationaliz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5]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6]Crasnow, Sharon, Alison Wylie, Wenda K. Bauchspies, and Elizabeth Potte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7]Stanley, Liz & Sue Wise, 1983 Breaking Ou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
[8]Haack, Susan, 1993,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s of an Old Feminist,” Reason Papers
[9]Putnam, Hilary, 1981, “Fact and Value” in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See also Nelson 1993, “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
[10]Kuhn, Thomas, 1977, “Objectivity, Value Judgment and Theory Choice”, in The Essential Tension
[11]Anderson, Elizabeth, 1995, “Knowledge, Human Interests, and Objectivity in Feminist Epistemology”, Philosophical Topics
[12]Longino, Helen, 1994, “In Search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Monist
[13]Anderson, 2015
[14]Anderson, 1995
[15]Ibid
[16]Ibid
本文先发于立场新闻 哲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