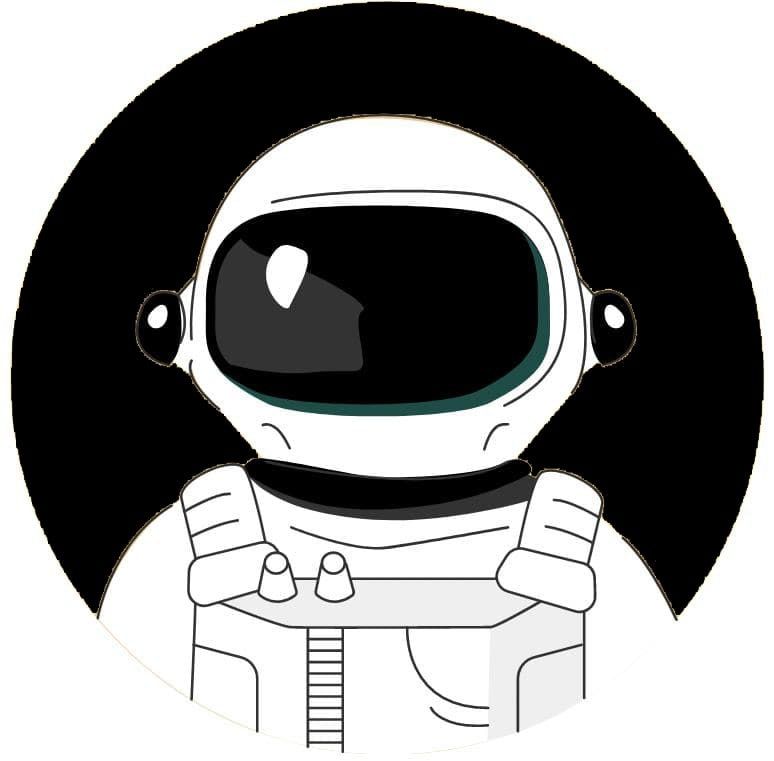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馬祖駐村筆記|離離島,移移人——飄浪者的東莒

「每個東莒人都有離家的經驗。因為東莒沒有中學,小學畢業後,就要去西莒讀國中,接著去南竿讀高中。或是從小學開始就在台灣讀書了,像我就是⋯⋯」她望著蔚藍的海面,眼底是一幅用海洋串連的世界地圖。
與我們對話的當下相反,這片海洋並不平靜。要橫渡至彼岸,得克服的困難太多了。我們像是兩枚漂流的瓶中信,隨著季風和洋流起伏盤旋,偶然在東莒島金色的沙灘邊上,擱淺。
我是個以旅行為業的寫作者,在一趟趟旅程的縫隙中,飛馬文學基地的計畫主持人問我:「有沒有興趣試試去東莒駐村兩週?」我看了一下行事曆,剛好有半個月的空檔。
「好啊,沒去過,去看看。」這是旅行者共通的口頭禪。在地圖上越是空白陌生的地點,越值得去挑戰。而東莒島被稱為「離島中的離島」,在Google map上連定位都定不準,道路與地點,全都在海裡。意思是,唯有靠肉身實際走過,才能理解東莒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沒想到,是一個連出發都很艱難的地方。
送關島,存機票
「買馬祖,送關島。」是往來馬祖的人常用來自嘲的順口溜。十年前第一次去馬祖,我就因為碰到颱風,必須滯留南竿。本以為所謂關島不過如此,卻忘了馬祖有四鄉五島,能飛得到南北竿,還只是第一關;有沒有船能到東西莒,才是魔王級關卡。
四鄉五島,以南竿島為中心,連結北竿、東引、東莒、西莒四座島嶼。北竿雖然也有機場,但要去其他島嶼,仍然得搭船到南竿轉運。重點是,不管去哪座島,船班都很少。以我要蹲點的東莒為例,一天三班船,沒趕上下午兩點半從南竿出發的末班船,就只能明日請早。
只要船有開,這些都是小事。尤其在東北季風吹拂的時節,風浪大,南竿至東西莒的航線停駛是常態。
我正巧趕上了颱風加上東北季風。預計出發日的前兩天,因為颱風山陀兒即將來襲,我在東莒的民宿主人柯爸打電話來,通知我往東莒的船會一路停航到颱風遠離,建議我留在台北,不然就算飛得到南竿,也得在南竿關島直到船班恢復。
待東莒船班恢復航行,已經是原訂出發日的五天後。我找到船公司的Line群組,通過審核,便開始每天緊盯群組訊息的日子。
颱風後的機票也是個難關。停飛多日,急著來去的人很多,機位一釋放立刻被搶光,堪比搶演唱會門票。我搶不到立榮,只好買華信,沒想到抵達松山機場、拿到登機證時,地勤人員告訴我,請靜候廣播通知,航班可以飛的話會通知掛行李。
一小時後,航班確定取消。這是我人生頭一遭,登機證都拿到了,航班卻被取消了。
還好在機場遇到同樣被取消航班的朋友,以及馬祖的在地支援小群組,他們指引我如何「圍剿式候補」:接下來的航班全部登記;不只是南竿,北竿也要,因為北竿的起降標準比南竿寬鬆。總之,先飛越台灣海峽再說,其他問題,入境馬祖後再來思考!
我很幸運地補上了北竿復航第一班班機。而最當初因為颱風被取消的立榮機票,以及當天臨時被取消的華信機票,就這樣成了某種不會增值的資產,存在航空公司的系統裡。
「這次用不到沒關係,之後再用。每個常常要往來馬祖的人,都因為航班問題,在航空公司存了很多張機票。」朋友說。
「存機票」大概可算是中華民國交通史的奇觀吧?退票當然也可以,但要加收10%手續費,不如存著慢慢用。
「每次折騰都可能加買好幾張票,那信用卡額度要很高耶?」
「信用卡額度還是小事,最麻煩的是,買到後來,自己都不記得存了多少張票在航空公司。總之一定是用不完的。」
我心焦地守著電子看板,等候復航消息、等候候補通知。這一天,馬祖交通關鍵字在我的耳邊大爆發:「關場」、「能見度」、「側風」、「起降標準」⋯⋯,夥伴們一一解析每個字詞在馬祖的意涵,這些對我來說極陌生的知識,對馬祖人而言,卻是再日常不過的基本常識。
「看天吃飯」,四個字說得輕巧,實際上卻無比沉重。

看天吃飯:沒船,沒人,沒飯吃
作為一個觀光客,常會有「當地怎樣與我無關」的心態。那是掠奪式的,只想拍到能被同溫層讚賞的美照,買到能向親友交代的特產,吃到大家都說要吃的當地美食,就算是來過了。觀光客的所見所聞,要傾訴的對象,是他自己的生活圈,所以當地實際上有什麼困境、發展脈絡是什麼,蜻蜓點水般知道一下就好,不知道也無妨,反正待一下就走了。
對東莒而言,我是個觀光客無誤。雖然逗留的時間比半日遊或一日遊的人稍長,理論上也是個不涉入當地現實的人。
但不可能不涉入。乘船到東莒,船一靠近猛澳港,人人都會看見四個大字:「同島一命」。
都說是同島一命了,只要來到這座島,就得與這座島死生相依。原因無他,這裡的所有物資幾乎都得從南竿轉運過來,沒有船,島上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給觀光客。
暑假的旅遊旺季結束,當東北季風開始吹拂、船班因風浪時常停航,觀光客不太來,物資補不上,我感覺到的就是兩個字:淡漠。就連淡漠本身都很淡,淡悠悠地。山羊淡悠悠地吃草,雞群淡悠悠地打盹,路上的人與車,稀疏得近乎零。原本島上的居民人數就少,一百多人,恆常經商的更少。隨著這個淡字,許多居民如侯鳥般東遷台灣,商店鐵閘深鎖,可以賣東西給觀光客的人,就是那麼幾位。
我的體質麻煩,煎炒炸辣寒涼甜一概碰不得。在其他國家旅居,只要是在城市裡,通常付出貴一些的價格,仍然有不少餐廳可以選擇。但在一座習慣自耕、自漁、自炊的百人島嶼,獨旅者要找到食物,就是個大挑戰。上島兩天,我將島上能供應一人份餐食的餐飲店都走遍,腹瀉隨即纏身。
為什麼要吃得那麼油?其中一間餐廳的老闆告訴我緣由:「這是我的猜想啦,這裡的菜都是家家戶戶自己種的,沒有用什麼化肥。台灣不一樣,生產量大,菜剛長出來一兩週,還嫩嫩的就採收,用水燙一燙就可以吃;但我們這裡要等菜長大,可能要一個多月,菜會比較老、比較硬,要用油炒,口感才會嫩。」
而以炸為主的料理方式,則是求快。賣餐給客人,最重要就是快。島上恆常需要外食的消費者以阿兵哥為主,年輕體壯,喜歡重口味,求的是一個爽快。慢條斯理的功夫菜,那是家裡才有的,是父母為子女悉心料理的愛。
「而且你來得不巧,剛剛好颱風剛過。」老闆說:「颱風前菜都採收了,現在剛種下去還沒長出來。而且貨船很久沒有來,大家家裡的備糧可能也沒剩多少。如果你要饅頭、蛋這些食材,可能要一家家去問,看有沒有人願意賣給你一點。不然就是問問看誰願意幫你一起從南竿訂。」
老闆講得實在,在我聽來卻是天方夜譚。
身為一個初到島上的陌生人,如何向居民請求協助訂購物資?如何說服對方出借家裡的廚房給我用?
我感覺自己正在和這座島學跳舞,而我是那個不懂跳舞的笨學生,左腳右腳前進後退轉圈,拿捏不到互動距離,抓不準節奏,踩著自己的裙擺或鞋子跌倒。
東莒的呼吸:船班、潮汐、垃圾車
要抓到一個地方的脈動節奏,先抓呼吸。吸氣時緊,呼氣時鬆,尤其不要在對方氣喘吁吁時打擾。住在島上的吞吐口猛澳港旁,對於呼吸的感受會特別明顯。
從南竿到東莒,一日三班船,早上七點、十一點、下午兩點半,雙月先東後西(先到東莒,再去西莒),單月先西後東,東西莒之間的船程大約十分鐘,南竿至莒光,大約四十至五十分鐘。少量物資與遊客,都靠這三班船運來。
這三班船,可說是東莒島與世界連結的命脈。船班一斷,島上就等於封鎖,退回自給自足的農漁時代。
我的身體也學著習慣與這三班船共舞。由於從南竿到東莒時,漏了點東西在南竿,夥伴幫我用「寄船」的方式隨著客運船送來,讓我見證這三班船對島民的重要性。
整點從南竿開船,二十分準備去碼頭,除了拿貨,也要送客人去買船票,或是在碼頭候客,接來客上車、租機車、收回客人歸還的機車,諸如此類。隨著潮汐漲落,船隻停泊的位置也不一樣,有高有低,得先盤算一下潮汐時間表,看看水位,才知道船隻會停在碼頭上哪個位置,看是銜接低樓梯,讓乘客向上走;還是銜接高樓梯,讓乘客向下走。
我抵達的那日是大潮,原訂發船時間的水位太高,東莒猛澳港沒有適合的樓梯可以供乘客下船,所以推遲了一小時發船。一開始我聽不懂為什麼大潮要延後一小時開船,也聽不太懂夥伴的解釋:「南竿福澳港有浮動碼頭,但東莒沒有,正在蓋。」在島上生活幾日,我終於看懂潮水與碼頭樓梯的關係。的確,若碼頭能隨著水位升降,潮汐變化就不會影響到船班了。
客船決定了島民的生活節奏。接客、領貨,帶客人走景點,安排住宿、用餐,下午兩點半送客,大約三點左右,本日的最後一班船開走,島上才逐漸安靜下來,恢復成東莒人的東莒。
我喜歡在三點之後在島上轉。這個時間點之後,島上靜極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Me Time」裡。大坪街上的商家敞著門在追劇,靠海聚落的人們,種菜的種菜,捕魚的捕魚,若適逢退潮,便到潮間帶挖花蛤、抓石狗公和小螃蟹。

潮間帶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之一,即使菜鳥觀光客如我,每天看著看著,也多少能掌握個大概。「初三十八大潮水,早上低潮中午滿,晚上起漲人煮飯。初十二十五,早晚滿潮中午低。」這是東莒潮汐的記憶口訣,以初三、十八、初十、二十五為基準,每日漲退潮的時間都會推遲一小時。像我抵達東莒那天的中午十二點正逢大潮,以此為記,用手指就可以數出今天什麼時候能夠下到潮間帶。
居民進入潮間帶的目的是漁獲,我則是想看看潮間帶裡有什麼、可以在退潮時走多遠、退潮對地理環境的影響有多大。
東莒周邊散佈著許多小島與礁石,退潮時露出淺灘,如同短暫出現的橋梁,可以沿著平日走到人跡罕至的區域。島的南端有一處大埔石刻,標記著明代名將沈有容擒獲倭寇的古戰場。四百年前的戰地已無遺痕,下到石刻下方的潮間帶,卻遺留了大量冷戰時期的反登陸裝置,像是玻璃刀山、軌條砦等。軌條砦經過長年海水浸泡沖刷,早已鏽蝕歪頹,挺立的孤枝看起來反而像是舉著無刃之劍的枯骨。玻璃刀山的玻璃被拔走或磨平,剩下固定玻璃碎片用的水泥團塊,猶如一張張猙獰人臉。
在馬祖的朋友說,那是釣客磨掉或拔掉造成的,釣客重塑了馬祖的人文地景。
坐在玻璃刀山的大礁岩旁,我望著灰濛濛的天、墨綠色的海。浪花隨著東北季風獵獵作響,潑濺在臉上,結成薄薄鹽霜,黏黏的,分不清是海水還是汗水。東莒日照毒烈,即使是陰天,身上仍然會被陽光炙得燥起來,我想起了金銀花,本地人拿它煮茶去燥,我的祖輩也有這個習慣,那是好幾代以前,遠從珠三角帶出來的習慣。
我的祖輩一代代南移,因為明亡,因為鴉片戰爭,因為甲午之戰,從珠江口和長江口,沿著邊界分批向南遁逃,最後走向全世界,我的父母則流離到了台灣。我很討厭戰爭,出生的時候,家裡一屋子都是戰爭難民,他們抵達台灣的時間,只比我早了一個禮拜。家裡的氣氛終日惴惴不安,不知道逃往哪裡才能安全定居。
而我眼前的這片淺灘,四百年前是戰場,四百年後,戰爭猶在。邊界在這座島嶼上的存在感很強烈,只是戰爭的主角換了人。誰是王,誰是寇,在這片海域,其實很曖昧。
東北季風常帶雨,在潮間帶遊走,往往等不到落日,雨雲便當頭澆下大水。急急回到村子裡,下午四點多,垃圾車的歌聲響起,居民也急匆匆騎上機車趕著丟垃圾,這是三點之後,島上最騒動的時刻。
反登陸裝置已廢,但我們著陸了嗎?
上島的時候,我注意到島上有一些「外國人」。他們是移工,像是我下榻的民宿,有一位印尼妹妹幫忙打點裡外家事;民宿隔壁棟則住著一些泰國男子,應該是在碼頭工作的,傍晚時分會簡單煮一些食物,坐在門口,播放曲風熱鬧的泰國民謠,配著啤酒吃起來。每次我停機車的時候,都很擔心會打擾到他們,會提早把大燈關掉,盡量慢慢靠停。
語言不通,我們靜靜觀察彼此。
印尼妹妹已經在島上待了一年,會講一點點中文,有時我會用Google翻譯印尼文和她聊天。她總是害羞不多話,赧赧地笑。和大部分印尼移工不同,她來自首都雅加達,台灣的移工主要來自爪哇北海沿岸。
「我在雅加達,工作的地方很糟糕。」問她為什麼來台灣,她這樣回答。「還適應這裡的生活嗎?」她點點頭:「這裡只有我一個人,但我有很多印尼朋友在台灣。」
齋戒月的時候,她靜靜地一個人執行守齋;開齋節的時候沒有慶祝,但也沒關係。她很喜歡在這裡生活,一個人。母國的糟心事太多,在這裡很好:「阿嬤教我煮菜,阿公教我種菜。」自耕自食,自給自足。
民宿主人柯爸柯媽各有傳奇,柯爸是老鄉長,柯媽是島上的廚神之一。拜雙十國慶連假之賜,柯媽要幫團客備餐,我也分到幾餐神級美食,果然名不虛傳。這套手藝就由印尼妹妹傳承,當柯媽回台灣,妹妹每天都會幫我準備蛋餅當早餐,餅敦厚、蛋香濃。後來我才知道,「柯媽媽的蛋餅」是東莒名菜,我很有福氣,一連吃了好幾天。
每天每天,她陪著柯爸柯媽過生活,早上五點起床,去碼頭接送客人、種東西、打掃屋子,煮飯洗碗,晚上七八點就睡了。她很少用手機,走在路上甩手吹風,神情一派輕鬆。碰到我的時候,會甜甜一笑。
她的「一個人」,是安適的。有時我會想,為什麼她可以這麼安然,我卻緊張兮兮的呢?
也許,因為這座島的島民,是「一家人」。每一戶之間都有著深深淺淺的親族關係,在島上行走,我總有一種闖進人家家裡的尷尬感。
我很害怕打擾別人。在這座島生存,卻不得不去造成他人困擾,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被恐懼與歉意緊緊綁縛。
返鄉的本質可能不是回家,而是旅居
抵達的第一天,我無法辨識哪些是商店,哪些是住家。大坪村的核心就是兩條商店街,上街和下街,但這些商店看起來與一般民宅無異,門都是關起來的。門內幽暗,看起來都像是人家家的客廳,看不出什麼商業活動。我轉來轉去,終於鼓起勇氣,拉開國利豆腐店的門,進門左手邊是豆花、甜品櫃,以及結帳櫃檯;中間靠右擺了幾張桌椅,確實是一間店,我鬆了口氣。

「老闆,有客人喔!」櫃檯內無人,正在吃豆花的客人,幫我往屋內喊主人。
這也是馬祖日常。島上人少,每個人都是一人身兼多職,常常不在店頭,此時就由客人幫忙顧。在島上的第二天起,我也成了顧店小幫手,老闆出門去忙,我就幫忙引導客人入座稍待、簽收包裹什麼的。大多數的時候,一個客人也沒有,我就看一會兒書,或是用手機處理自己的事情。
這種情況放在台灣可能會很奇怪,但我做得很開心。能替島上分擔一些工作,會讓我覺得比較自在,不再是一位闖入者。
L在台灣生活四十年之後才「返鄉」創業,說是回家,可能更像是來到異地。
「以前住在台灣,一年就回來個幾次,待的時間也很短。每次回來,都是跟著爸爸媽媽,大人忙著團聚,我們這些小孩只能尷尬地坐在旁邊發呆。」
我深有同感。因為我的母親是香港人,每年寒暑假都要跟著她回香港探親。雖然是回外公外婆家,無形中卻好像有許多作客的規矩要遵守。面對大家族,太多的應對進退要顧及,要練習講陌生的母語,要努力記住陌生家人的臉孔與名字。好不容易稍微熟悉了一點,還來不及讓自己放鬆一些,又得回台灣了。半年後,同樣的困境再走一遍。
一遍又一遍,身體在物理上「回來」了,但心靈卻好像靠不了岸,兩頭都不到岸。
「而且小時候看到的東莒,和現在完全不一樣。」L說。我用力點頭,是的是的,我對香港也是一樣的感受。
曾經熟識的人可能大多離開了,島上的一切不只是物是人非。香港急速奔向前衛與進步,而東莒則是聚落空置、房舍頹圮。重建之路不是復舊,而是要弭合這幾十年的時空斷裂,讓舊屋保存一些當年的家族回憶,功能卻必須符合二十一世紀的使用需求。
因為要回台灣陪小孩,她即將離開東莒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碰巧搭同一班船「離島」。離開前一晚,她帶著我去參觀在大埔聚落的舊家。那是一個曾經人丁興旺的漁村,閩東式石頭屋鱗次櫛比。我每天都會去大埔走走,卻一直沒有機會走進當地人家裡。
「這是大埔唯一的木構造石頭屋。」她將祖輩的故居重新佈置起來,原本的棟架因為白蟻嚴重蛀蝕,全部換新,一開門,福州衫的香氣撲鼻而來。她指著那些無法利用的牆面,因為背後就是山壁,得留著空間透氣透水,讓房子呼吸。
家,是人、房子、食物聚合的地方。每一個環節,都是學問。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去認識這座島、認識島嶼上的家人,用自己擅長的方式重詮自身與故鄉的關係,其實很糾結。

移人眼底的灰藍色,不是冰冷,而是等待
雖然返鄉維艱,但我好羨慕她。同樣是往返各地的移人,她在故鄉有個長期定錨的地方,可以定義自身,可以居住、工作,被熟悉的鄉音圍繞(即使自己說得並不流利,但沒關係),有餘裕去思考怎麼將島上的特產,轉變成適合現代人的健康飲食,介紹給不認識這一切的來客。
我更像個失語者,母語說得坑坑巴巴,每次開口都羞愧;要講述自己的文化是什麼,卻都是斷簡殘篇。即使費盡心思做足準備,主流族群覺得與己無關懶得聽,母文化的族群則嫌我外行,像是永遠都在走鋼索,永遠擺盪,永遠下不了那條鋼索。
認清這一點,我早已放棄「著陸」,放棄融入任何族群。花了很多年,我明白自己也屬於一個非常龐大的族群,這個族群叫做「移動者」。
東莒被稱作離島中的離島,可能是中華民國行政區劃中,距離核心最遠的一座島,連鄉公所都是設在西莒,而非東莒。而我自己的觀察是:東莒島上的人,可說是移人中的移人。
移徙的人有個特質,和定居者不太一樣,你會在他們眼中看到一抹灰藍。這抹灰藍輕輕淺淺,我們在這層如煙的灰階之中,試探著彼此,等待交集。
這抹灰藍並不是一道高牆,只是每個人都有他離開的節奏。島上的人會離開,你我也會離開,有些人會再回來,有些人不會,當下一切都難說。不必涉入彼此太深,因為可能很快就要告別。但只要多相遇幾次,那抹灰藍就會消失,誰的移動軌跡或心路歷程與自己重疊,那重疊的部分,就是開關。
大埔聚落有一個社造組織,叫做「大埔Plus+」,我上島的時候,這個團隊剛巧結束上一個計畫離開東莒,直到我離開的前三天才回來。團隊成員都是從台灣過來的,領頭人強妮已在此深耕六年,其他人有的在島上是待一兩週就回台灣,有的則是資深的「半島民」,每到淡季都會回到東莒生活。這群人被東莒居民暱稱「大埔小朋友」,有的是藝術家,有的是食農工作者,各種身份都有,每日三餐共煮共食,互相支援各自要進行的工作計畫。
大埔Plus+提出了一個概念:「新家人」,希望為東莒島培養長期粉絲,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東莒,願意來到東莒生活。藉由這個過程,讓人口大量流失的偏遠島嶼,逐步恢復生機。
在島上的最後幾日,我常去大埔Plus+的魚寮跟他們聊天,聊聊各自對這座島的體會與心得。每個人「著陸」的途徑都不同,有的人是無意識、很滑溜地滲透進島上的居民圈,有的人則是從某一位居民開始,逐步被帶領、深入這座島的氣象萬千。
雖然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計畫來到島上,卻都擁有一雙澄澈、誠摯的眼睛。他們熾烈的好奇心,撥開了人們眼中的那抹灰藍。
東莒島上的人們,都很習慣聚散。再聚首是開心的,而告別亦是日常,珍惜相聚的當下就好。林志炫有一首歌叫做〈離人〉,其中一段歌詞是這樣唱的:「有人說一次告別,天上就會有顆星,又熄滅。」
望著東莒沒有光害的滿天星斗,我想,這裡的歌詞也許該改一改:「有人說一次告別,天上就會有顆星,再綻放。」
感謝這座因為離別而燦爛的島嶼,感謝每一位在旅途中照顧過我的人。我們下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