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台灣和香港:建立力量的新方向
中國勢力迫在眉睫:香港和台灣的抗爭者必須找出彼此之間以及與世界聯繫的新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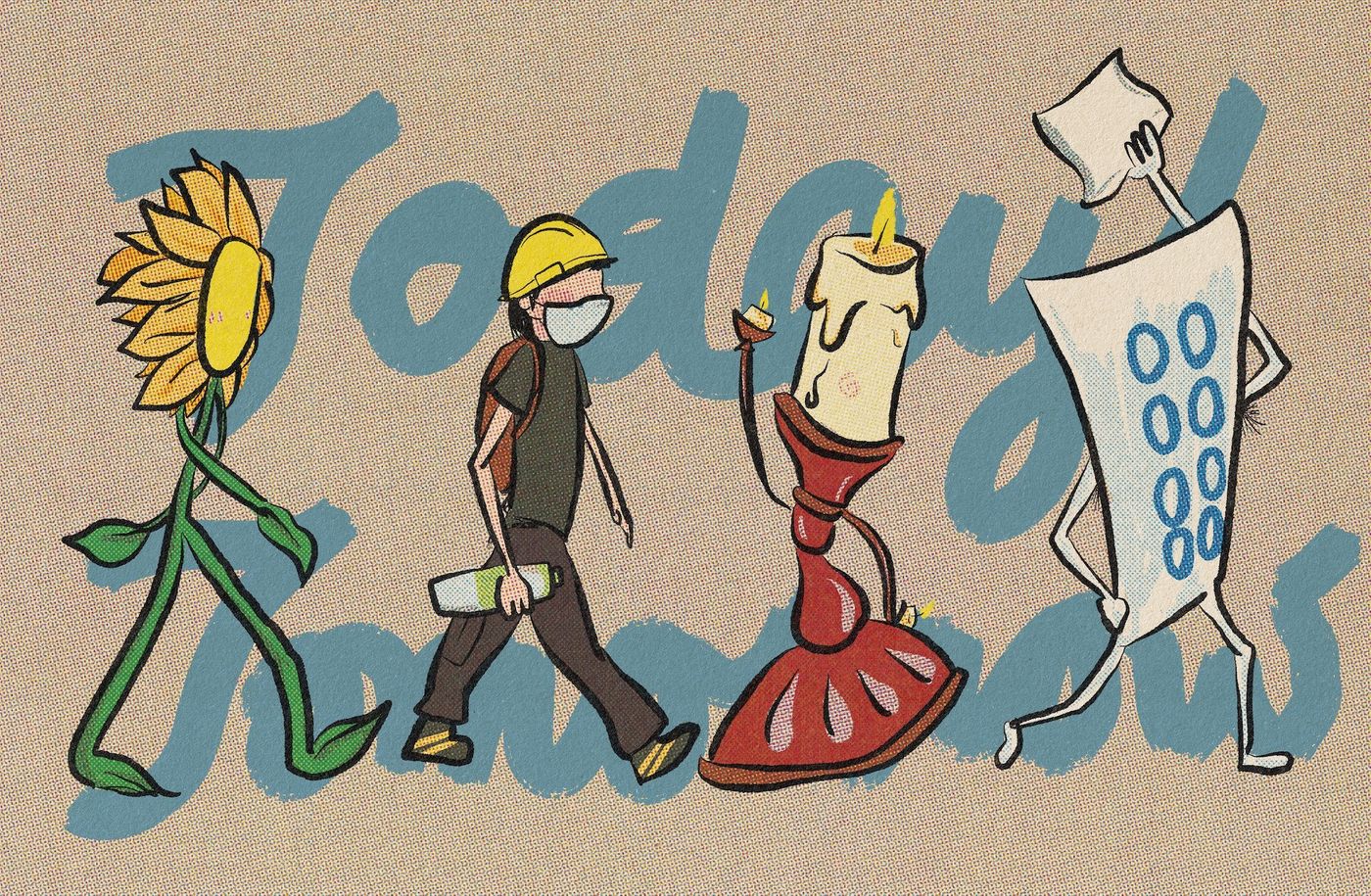
英文原文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Mary L., NN
台灣交響黑金屬閃靈樂團於2019年舉辦的音樂會,在台北自由廣場設置了喧鬧的衝撞區,吸引了三萬名參與者。這也是一次政治集會:社運人士、立法人員和政界候選人,如閃靈樂團的主唱林昶佐和賴品妤,都在談論抗拒鼓吹兩岸統一的國民黨,以此保衞香港的民主。許多與會者以流行的抗議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來回應。
自從反修例抗爭活動開始後過去的一年來,台灣與香港之間的這種公共和創作上的互相支持不斷增加。但其實我們也可以退後一點,了解台灣和香港在政治上的過去和未來怎樣息息相關。的確,兩地的行動者早已看到彼此之間的共同之處。台灣和香港都一同面臨來自中國政府對兩地民主自由的威脅。多年來,社運人士一直在台灣和香港之間穿梭,觀察或參與抗議等重要的政治活動。台灣和香港行動者之間的聯繫可以追溯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之前。當時,很多在香港和台灣之間旅行的學生團體都互相建立聯繫,希望彼此學習。
香港與台灣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不僅涉及策略上的交流,也涉及論述以及歷史和政治概念框架上的交流。探討這些交流可以闡明雙方政治上的自我理解,以及台灣與香港在未來建立力量的前景。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台灣和香港的行動者經常將兩地的關係概念化為一種時間關係。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以來,「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成為台灣示威中不斷出現的標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如果台灣失去了民主自由,就有可能變成香港這種黯淡的未來。這表明對於台灣人來說,香港就像一塊可以投射他們對台灣潛在的政治後果的擔憂和憂慮的畫布。
香港和台灣向對方投射政治想像的行為是雙向的。例如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機制和進步性政治上,香港人一直以略為烏托邦式的框架去將台灣和香港作比較。也就是說,台灣有時會被視為一個香港已失去的歷史可能性,亦即假如歷史改變了,台灣就是一個可期望的未來。可是,香港人將台灣浪漫化和台灣人將香港浪漫化這種思維有可能會妨礙大家互相真正理解兩地的本地脈絡。
讓我們研究一下其中一個最常見,現在被禁用的抗爭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之中的「光復」一詞。將香港「光復」到以前一個比現在更好的狀態,暗示了一種時間性的概念。廣泛來說,「光復」一詞意味著以一種進步的方式重奪過去。有些人則對於口號所暗示,重返英殖狀態的香港是理想的想法抱有懷疑,畢竟香港在英國殖民之下,都不算民主。
香港人將台灣浪漫化和台灣人將香港浪漫化這種思維有可能會妨礙大家互相真正理解兩地的本地脈絡。
然而「光復」一詞也是國民黨意識形態中的核心概念,有強烈的中國國民黨涵義。在台灣,異常多的街道和地方都被稱為「光復」。它們是其中一些在國民黨到達台灣後不久,根據其意識形態原則或被神化的政黨領袖去進行改名的地方。在這裡,「光復」一詞指的是國民黨在軍事上從中國共產黨中奪回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目標,亦即「光復」大陸。
但是,「光復」也可以是指國民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在台灣掌權,結束台灣的日本殖民時期,並把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帶到台灣後,把台灣「光復」為中國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辛亥革命有時候會被稱為辛亥光復,暗示國民黨控制的中華民國政府的興起和清朝的衰落一同「光復」了中國,把中國從滿族人手中奪回給漢族。
不管怎樣,這種「光復」的概念都展現出台灣與香港之間有強烈的相似之處。香港一些示威者堅持在示威中揮舞英國殖民地旗幟的事實暗示,他們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以過於樂觀的眼光來看待英國殖民時期。可是,在台灣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很多台灣人在國民黨來到台灣後,對日本殖民時期有很多懷舊的想像。
人們對當前狀況的不滿會促使他們渴望一個其實沒有存在過的過去。
這些例子反映出新殖民政權的進入會令人們把之前的殖民政權浪漫化。人們對當前狀況的不滿會促使他們渴望一個其實沒有存在過的過去。把過去浪漫化定必會限制我們的政治想像,因為它會將我們對現在有什麼可能發生和有什麼是可取的視野侷限於一個先前的政治秩序。如果「光復」暗示的是要恢復先前政治秩序的條件,那麼建基於積極尋求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改革機會就會被大大限制。
在香港,把「光復」用在「光復香港」很大可能有助於台灣傾向獨立的泛綠陣營挪用這個本來標誌著國民黨的用詞。最近,進步主義的民間社會團體領導了一場罷免運動,成功罷免屬於國民黨的高雄市長韓國瑜,而在運動中他們所用的口號正是「光復高雄」。
運動組織者WeCare高雄和公民割草行動將「光復高雄」的英語翻譯為「重置高雄」(Reset Kaohsiung)。這樣使用「光復」其實是十分顛覆性的。這裡暗示的觀念,就是與其尋求恢復之前的政治秩序,不如徹底把黑板上的所有東西擦走然後重新開始。也許這是唯一一個重新詮釋「光復香港」,而不帶懷緬英國殖民主義的一例。把「光復香港」重新理解為「重置香港」而不是「光復香港」,這個口號要求我們對香港的未來進行徹底的重新想像。

昨日台灣,今日香港?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口號示意了,台灣若然要失去其民主自由,那香港就正處於台灣未來的某一時點。同時,也有一些香港示威者將香港現時發生的事件定位在台灣的「過去」。
在香港,越來越多人使用「白色恐怖」一詞來指稱大規模逮捕,以及有關個別曾參加示威活動人士的失踪和神秘自殺的報導。但是,「白色」政治恐怖是台灣所特有的,因為白色,連同藍色與金色,是國民黨的政黨顏色,所以「白色恐怖」是指國民黨在戒嚴期間所進行連續數載的政治打壓。這段時期曾經是世界上歷時最長的戒嚴時期。有人認為,不斷惡化的政治環境可能導致一波香港人逃往國外,就像在白色恐怖期間許多台灣行動主義者逃往海外一樣。流亡海外的台灣僑民最終在台灣民主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人推測並希望香港也會是如此。這些共鳴使台灣過去的「白色恐怖」在後國安法的新恐怖氛圍中,在香港人之間產生了情感共鳴。
但是,從某些方面來說,在香港出現「白色恐怖」一詞在某程度上是很不尋常的。國民黨實施的「白色恐怖」在冷戰反共主義的主持下得以正當化,當中國民黨亦聲稱其所監禁和處決的都是忠於中國共產黨的間諜。相比之下,中共恰恰是香港抗爭者所抗衡的政治力量。香港政府的行動背後是來自遠方的中共的指示。雖然許多暴力襲擊示威者的人士在施襲時都身穿白色衣服,諷刺的是運動話語空間廣用的詞語是「白色恐怖」,而不是「紅色恐怖」。
類似於台灣的「白色恐怖」,香港的一些政治團體試圖在香港使用台灣民主運動的口號。例如,最近解散的香港眾志曾將言論自由殉道者鄭南榕的口號「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改成「100%自由」。《自由時代周刊》的出版人鄭南榕被關在雜誌辦公室,被警察圍困了七十天後,於1989年4月自焚。
一些抗議行動則取自台灣較近期的抗爭史。在七月一日企圖佔領香港立法會期間,立法會會議廳的牆壁上寫上了「Sunflower HK」字樣,指向2014年太陽花學運圍繞台灣立法機關長達一個月的佔領。
有的香港人甚至可能在台灣歷史裡尋求如何實現自決的答案。曾赴香港大學並自此成為台灣和香港社會運動之間聯繫的台灣行動主義者江旻諺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提到,有香港朋友對二十世紀台灣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史明(所謂的「台獨之父」)的作品和他以左翼角度對台灣獨立的理論闡述表示興趣。江認為對史明作品的興趣主要來自主張香港自決但又希望避免本土主義的指控的人士。
這是香港和台灣之間的比較中一件有趣的軼事。香港的行動者將今日的香港與台灣的過去相提並論,正表示他們希望,像台灣一樣,香港最終可以通過社會運動抗爭實現民主化。同時,當今香港的情況與台灣並不完全類似,主要是因為香港跟中國的距離很近。
在中國人口移民,甚至軍事干預的威脅等問題上,香港必須直接與中國抗衡中國。這是台灣未曾有過,現在也沒有的情況。香港與中國僅隔河相望,而台灣與中國則為台灣海峽相隔。正如台灣無政府主義的民族認同理論家吳叡人在《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中指出,即使當代台灣身份認同傾向於公民民族主義而不是族裔民族主義,如果台灣面對相當於香港的中國移民水平,那麼台灣針對中國人的仇外心理和族裔民族主義情緒可能會大大提高。
在香港,要試圖超越族裔民族主義的排華視野,需要找出某種方式來解決。台灣未必可以就如何避免本土主義提供答案;那可能僅僅是由於台灣在地理上的偶然性,剛巧避免了導致強烈的本土主義出現的條件。而且,我們應該記住,公民民族主義仍然可以不可預測地演變為族裔民族主義。世上從來沒有一種不包含族裔民族主義某些元素的「純」形式的公民民族主義,反之亦然。

空間作為建立力量的阻礙
如果台灣和香港的行動主義者是以時間性來概念化他們之間的關係,其實空間性才是現今兩地之間行動者建立力量的阻礙。
的確,當前運動的根源與台灣和香港之間存在爭議的司法空間緊密相關。當初極具爭議性的引渡法案是在潘曉穎在台北被男友陳同佳謀殺後引發的,而兩人都是香港人。由於香港和台灣缺乏引渡協議,所以陳同佳未能被引渡到台灣受審。因此,香港政府提出了一項引渡法案,允許香港與其他地方,包括台灣和中國之間移交逃犯。
這個案件反映了台灣和香港之間的關係是怎樣過分取決於各自的司法地位和主權。但儘管存在這些重大的分歧,香港和台灣仍然共同面對著大大影響他們政治處境的「中國因素」。台灣主要的政治分歧在於傾向獨立的泛綠陣營和傾向統一的泛藍陣營之間,跟香港泛民主派與親中派之間的分歧十分相似是意料之內的事。這反映出本地的政治問題跟對中國關係的外交問題密切相關。如果避免正視台灣和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這個基本的問題,會限制我們的政治想像和採取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有很多台灣人都在香港的運動期間前往香港參加遊行抗議。2019年6月示威開始,以及在中國國慶日2019年十月一日前後的示威活動中,都有特別多台灣社運人士前往香港參與示威。結果在2019年十月,就有報導聲稱有台灣人在香港國際機場被搜,特別是當中年輕的男性,搜查行李內有否含有防毒面罩、頭盔或其他示威裝備。
同樣,台灣的民間社會和宗教組織看到香港防毒面罩、頭盔和其他示威用品的短缺,便承擔了向香港寄送示威裝備的任務。當中有些組織更後來參與協助或給予庇護一些來台灣避難,希望避免示威相關刑罰的香港人。
但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關係,台灣人目前難以前往香港。雖然香港的邊境仍然是開放的,但飛往香港參與示威的台灣人將必須在香港隔離14天,然後返回台灣時又再隔離14天。因此,任何想要參加示威的人都必須願意犧牲一個月的時間進行隔離,而這不是必須要工作才能生存的人能夠負擔得起的。
而隨著港區國安法的通過,中國政府很大可能針對支持台灣獨立人士為煽動的對象。進入香港的台灣人,甚至只是通過香港國際機場過境的台灣人都有可能受到國安法的制裁。去年至少有一位台灣公民在香港參與遊行後進入中國大陸時被捕,而大眾質疑還有更多類似的案件尚未被揭發。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爭先恐後吸引因安全問題尋求離開香港的金融業人士。而往往都是那些已經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之間隨意遊走的商界精英們最容易獲得在台灣的居留權。當別人都指控香港和台灣的運動是資產階級的親資本主義運動,以及只是因為要保護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才害怕中國,其實在運動最前線的人都幾乎沒有逃走的辦法。
當別人都指控香港和台灣的運動是資產階級的親資本主義運動,以及只是因為要保護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才害怕中國,其實在運動最前線的人都幾乎沒有逃走的辦法。
當台灣現在已封關禁止外國人進境,香港人根本沒有辦法前往台灣尋求庇護。在前太陽花學運行動者的施壓下,包括為了呼籲政府採取加強協助港人的措施,而很大可能得罪了黨內聲音的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蔡英文政府最終設立了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來協助港人在台灣獲取居留權、讀書、尋找工作、投資或尋求庇護。
除了協助香港人在台灣尋找工作、讀書或投資,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也會處理香港人的庇護申請。調查發現在考慮離開香港的港人當中,台灣是首選的目的地。雖然辦公室設在台北而不是香港,但人們也擔心香港政府會對台灣駐香港辦事處的職員進行報復。儘管蔡英文政府設立了新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但也不見得他們打算通過立法為香港人建立一個申請台灣庇護的正式程序,寧願繼續根據個別情況來處理每一宗庇護申請。
確實,在台灣或其他地方,有關難民的問題經常激起人們對邊境的憂慮,而為香港人通過庇護法案的想法也因此引來批評;有人認為這會製造機會讓中國間諜混入香港人而進入台灣。可是這個憂慮是荒謬的,因為很多中國人根本已經在台灣生活、工作和讀書。這個想法卻也許跟某些試圖在「黃色經濟圈」和「只招待香港人」的餐廳中排斥中國人的香港人有相似之處。在我們過去幾年對台灣與香港之間交流政治論述時的觀察,我們看到這也涉及到民族主義論述元素上的交流。例如,來自香港的「左膠」一詞就被進口到台灣,用來詆毀台灣的政治左翼份子。雖然「左膠」一詞源自香港,但諷刺的是,這個用詞卻在台灣被用來詆毀當地的左翼份子,批評他們過於關注像香港人庇護之類的崇高事情,而不專注於台灣內更實際的國家安全問題。
我們也應該留意,來自香港、中國和澳門的學生其實只是最近才被允許重新進入台灣。雖然持有外僑居留證(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s, ARCs)的外國人被允許進入台灣,但因為中華民國把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包括在自己的領土之內,所以來自這些地方的人都因不算外國人而不能夠申請外僑居留證。因此,即時疫情在香港和中國很多地方都已經受控,開頭的幾個月台灣都不允許這些地方的人前往台灣。這個情況被批評為一項歧視性的教育政策。
無論如何,即使疫情完結,而台灣的邊境再次重新開放之後,台灣和香港(更不用說中國)行動者之間的交流空間也將越來越被收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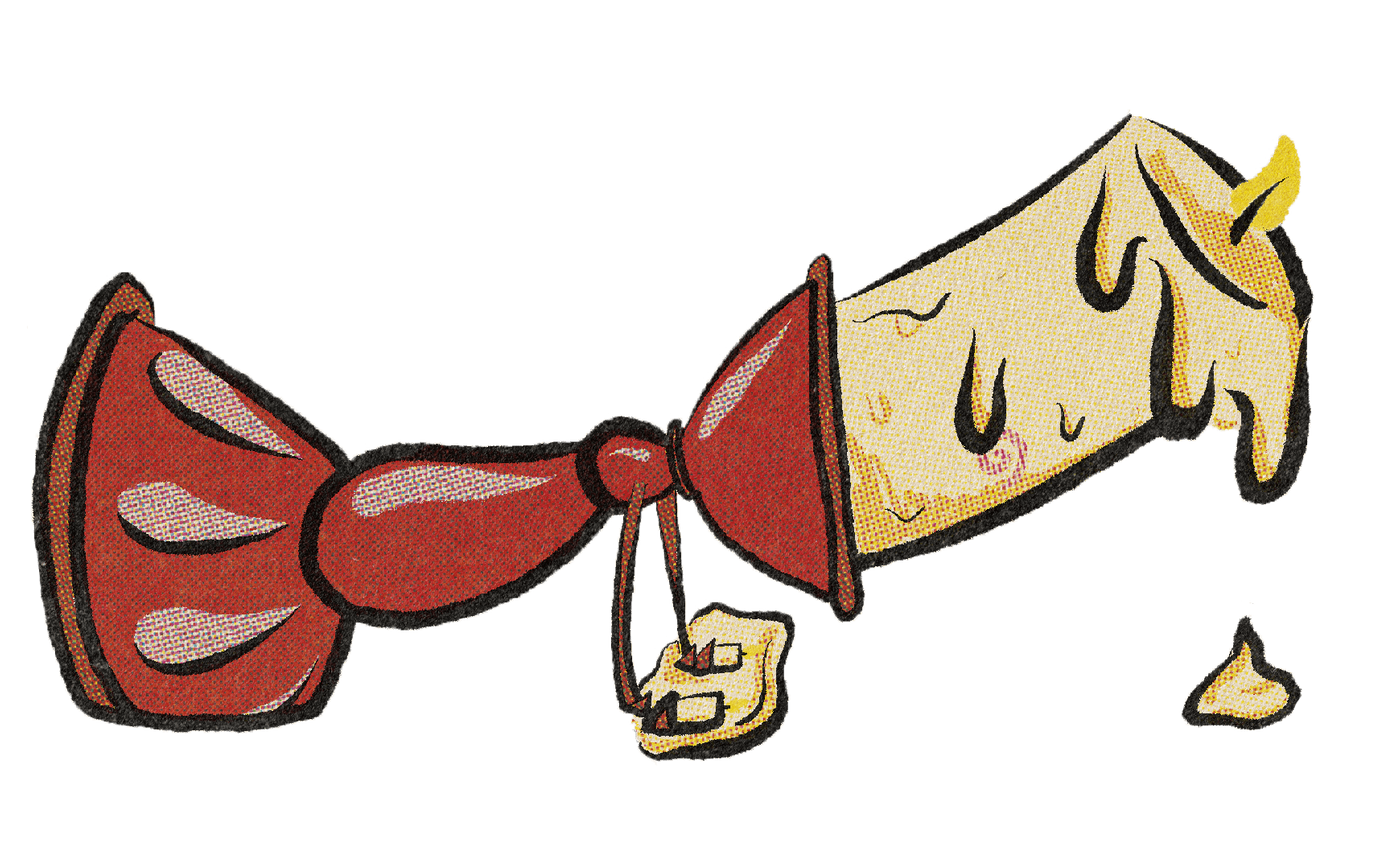
壓迫的新時代、建立連線的新途徑
台灣理論家吳介民在其2012年的著作《第三種中國想像》中曾提出一種現在看似烏托邦的觀點:台灣、香港和中國的行動者團結起來打擊他們的共同敵人:中共。然而,隨着而中國的旅遊封鎖以及對台灣和香港的行動者的危險增加,台灣、香港和中國的行動者之間要進行實質的交流已變得越來越困難。
過去一年來香港旅遊的風險水平急劇上升。國家安全法可能會大大提高台灣行動者前往香港的風險。儘管台灣政府或會願意允許中國人或香港人進入台灣,而中國政府雖然禁止個人赴台旅遊,中國行動者仍然有一些合法的方法進入台灣,但中國和香港政府仍有責任阻止行動主義者離開中國或香港邊境。
因此在將來,團結或越會需要在遙遠的地方發生。明年情況是否如此尚待觀察。但是,正如預料中的香港將會繼續發生示威遊行一樣,台灣與香港之間的政治交流也有望繼續進行。但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台灣和香港的行動者除了提供情感支持外,又如何能夠找到互相幫助的方式?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如何以一種超越現今香港被視為類似於台灣威權歷史或是台灣可能面臨的敵托邦未來的二元框架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台灣與香港之間的關係。借用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措辭,這兩種框架都是「將整體自由撕成兩半,但是它們並不能彼此相加在一起。」
台灣和香港的行動者除了提供情感支持外,又如何能夠找到互相幫助的方式?
實際上,在這兩種框架中,台灣和香港之間的關係就是一方面成為另一方面的背幕,根據當地情況來投射自身的政治焦慮。台灣和香港之間的投射導致了共同的使命感,其根本原因是中國這「大他者」。換句話說,與中國的隱性「對比」經常構成比較香港和台灣的基礎,實際上劃出了我們可以想像的政治行動的邊界。去否定該框架又不被此「中國因素」所限,將是未來幾年台灣和香港作家與行動者的巨大考驗。
我們對此前路應該認知到的是,香港與台灣之間的政治投射並不太可能有助於真正建立國際左翼的跨國連線行動。隨著這兩個地區的解放之路越來越窄,鎮壓的確定性越來越高,如何應對中國因素仍然是一片烏雲,籠罩著在台灣、香港與其他地區之間建立跨國聯盟的努力。因此,我們必須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交流歷史,留意我們當前和未來的挑戰,超越投射和預期,建立力量。
文/ 丘琦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