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人(下)|川西行(八)
lee昨天发了个视频,用了很多心思和时间,做得相当精致,介绍川西秘境。短短半天,转发过千。但是其中有个评论,应该是噶古菩提林的修行者,语气不是太和善。他纠结良久,最后隐藏了视频,说有点内疚。我说唉呀我也写了游记,只是我没你那么红,传播力没那么广,他们没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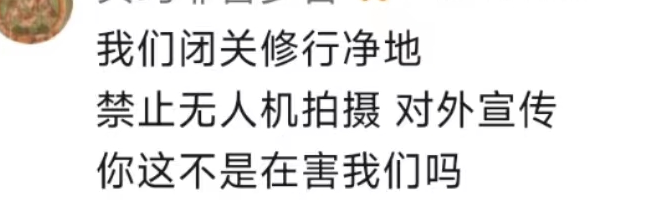
这真是很难的事,多数人看到美好的事物,很自然地想要和人分享。对那些商业运作的东西来说,这种分享是很重要的。君不见前半年火得不行的淄博烧烤,就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但对于噶古菩提林的修行者来说,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TA们想要清修,想要不被看见,不被打扰,就不需要这种“宣传”。
然而,话说回来,把自己的开心、喜悦,所见所闻分享出来,又是不是属于自由的范畴呢?而这个禅修院的所在,又属不属于隐私呢?
在石渠的色须寺,我们还遭遇到一位“上师”的冷语。他们在寺庙的院子里举行某种像是“谢师”的仪式,我们在旁边看。那位受”谢“的喇嘛,开始时用有些严厉的眼神瞪着我们,后来仪式结束,他走过来,对朝他讲”扎西德勒“的N导说了句话。我没听清,问N导,N导说他讲的是”出去。“
我们于是乖乖结束了那天在色须寺的行程,没有人背后批评他没礼貌。
你说他有礼貌吗?确实没有。做为一个”得道高僧(目测)“,待人接物不该是那样的。
可是我们好像也觉得,自己的到来,打扰到了寺里的活动。人家辩经,我们在旁边看戏,看又看不懂,还要不时拍拍摄摄,假如我是当事的僧人,也会不舒服。
谷歌色须寺,看到一篇文章,讲这里的僧人之前曾发动保护母语活动。真假没有考证,但通过那”高僧“的行为,我相信是有这事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哪天,我的母语遭遇外力干预,岌岌可危时,我也会讨厌使它消失的人,或者事。

写到这里,又联想到香港。假如我哪天去香港,有人冲我说,”回你的大陆去“,我的态度会不会像在色须寺这样淡定?
应该不会。但这二者于我的区别在哪里,我还没想通。
大多数普通人,是友善的。
在石渠城外的经墙边,偶遇一位转经的老人。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头发花白,戴眼镜,穿红色线衣,另披一件黄色的藏式”半氅“,半边红色的上身露在外面,拄根自制的拐棍。我们想给他拍照,不好意思。正在彼此怂恿间,他主动搭话,走,一起转。
在转经途中,我请他教我一句藏语,他欣然应允。”翁、巴、扎,萨、都、轰“,一字一句,教地很认真。可是那个”扎“字后面,有个很华丽的弹舌音,我发不来,每次都卡在那里,就大笑,他也跟着笑。N导不管弹舌音,一切就很顺利,得到老人的表扬。大概在语言学习上,追求完美是会拖后腿。
每走几步,他又会一字一句重复那句话,我们也一字一句跟着念。我问他翻译成汉语是啥意思,他听不懂我的问题。我夸他汉语说得好,他说是小学学的。临走前,我跟他保证说我会好好练习。他很开心,说已经很好了。

晚上在石渠的火锅店,我们向店员请教那句话的意思,她说是”愿为祈福“。我想,大概是”祝福你“的意思。
在松格玛尼石经城遇到的小孩,就更有意思。
一男一女,十来岁,鼻子脸的主要部分涂白,额头和下巴裸露在外。我以为是当地人的特色装扮,问他们,说是防晒。他们指导我们停车,以为要收停车费。没有,是想让我们请他们代为磕头,一圈二十块钱。我们没有信仰,我们不磕头。那给一块钱可以吗?我们没有现金啊。那有吃的吗?最后给了些饼干和巧克力,立马开心地吃起来,并且带我们去他们的姑姑家上厕所。厕所是用木板架在矮墙上,悬空,踩上去有点担心断裂。
从石经城出来,他们俩还在门口,旁边还有一群孩子。女孩大声招呼,你们要走啦?那再见啦!汽车发动的时候,又追来说,加个微信吧。天哥笑问,加微信干嘛?说朋友一场嘛。我们在车里笑,这孩子好社牛,快成精了。
我说大概都是汉人带的风气,请人代磕头。N导说不一定,本地人也不一定都虔诚。Lee说,想想,他们挂经幡、撒龙达的意思,都是想让风代替他们念经,好成就自己的修行,那么,按这个思路,花点小钱,请小孩子帮自己磕磕头,是不是也不算不虔诚?我一想,唉呀,你怎么讲得这么有道理!
应该还是汉族人,不然那些孩子不会围着我们转。我想。
打开窗子,蚊子就会进来。一直关着,空气又糟。这真是难办的事。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