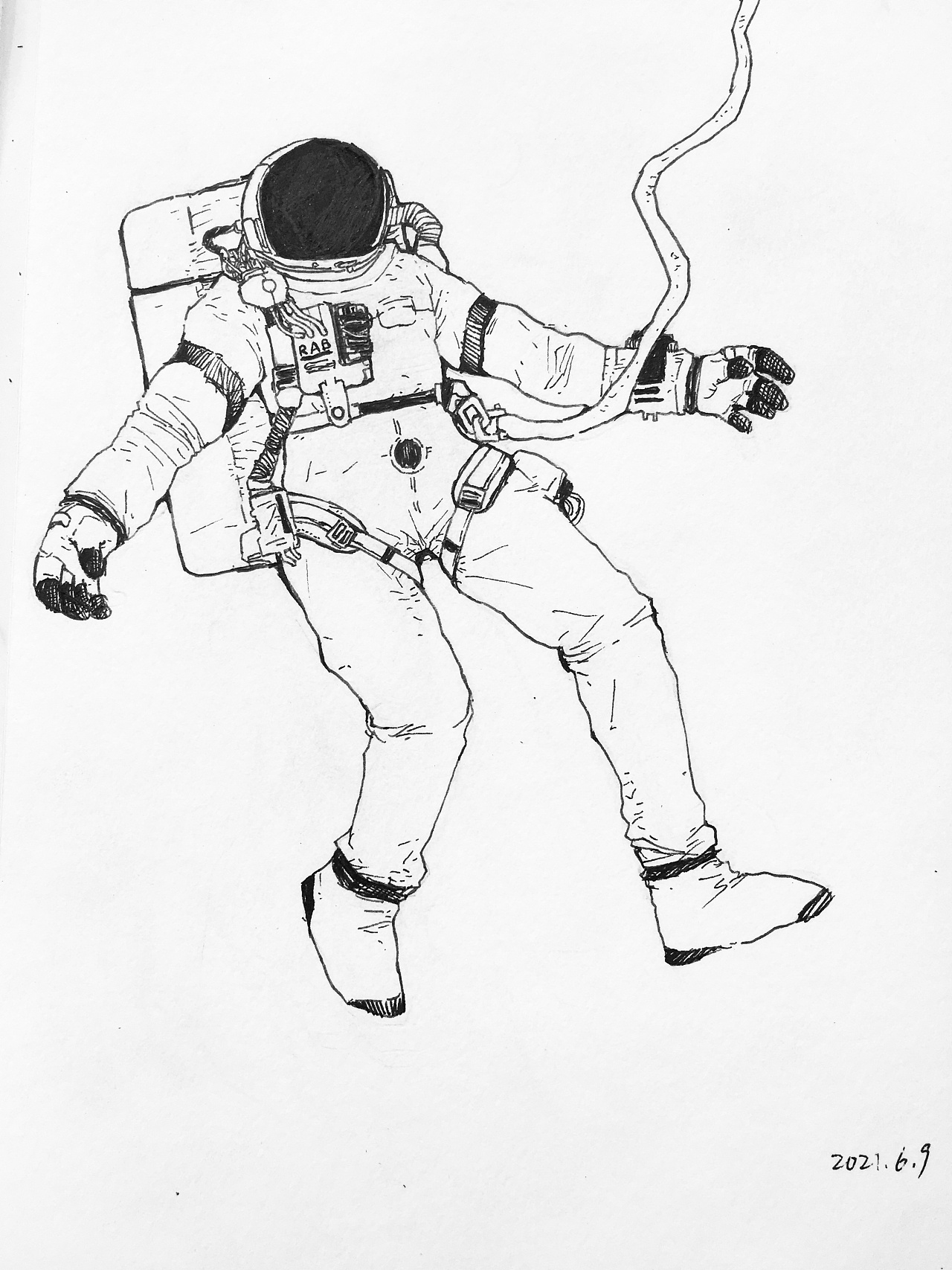電影|許鞍華《詩》

英文中有個詞組,「crystal clear」,用來形容許鞍華的《詩》,我想是再合適不過了。
許鞍華說,我想要拍這樣一部關於詩的片子,於是我就來拍了。不同於《他們在島嶼寫作》,《詩》沒有要為任何詩人加冕的野心。除了廖偉棠的詩歌課堂,片中沒有任何「專業評論」,譬如鏡頭中詩人的歷史地位、文學成就、詩歌美學等等。唯一的「評價」,來自以「讀者」身份受訪的黃潤宇,而她哽咽著講述的,是詩歌如何撫慰身處獄中的好友,以及,「我想如果詩人還在世,見到這個情形,可能也會很開心。」所有詩歌周遭的事物被全數棄置,只留下詩歌,詩人,讀者,電影也得以輕盈透明地起飛。
影片末尾,許鞍華突然被反問拍片的緣故。於是一切靜悄悄翻轉,採訪者變成受訪者,觀看者變成參與者(「在坐的每一個人,都在寫著香港的詩」),原本拋向受訪詩人的問題,在那一刻神奇地穿過第四面牆,放在了所有觀眾面前。在放映前我和朋友回憶起一件關於詩歌的事情,高中的古典詩歌選修課,講李商隱,我坐在課室的最後面聽講,聽著聽著,流了眼淚。《詩》結束時也是如此。不論是李商隱還是《詩》,都沒有任何大開大闔、逼著你把眼淚交出來的東西。最終不過是,我們在那些「水晶般透明」的事物中,辨識出了那個愚笨的、污穢的自己,為此一哭爾。
放映十一點半才結束,和朋友坐半夜的香港地鐵,窗外黑沈沈一片,偶有零星路燈掠過,恍若置身《千與千尋》的海上列車。到大學後邊聊天,邊爬上新亞。夜色如酒,總喜歡讓人說許多胡話⋯⋯
202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