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切割、綻放、生命樹的救贖——《植物人》選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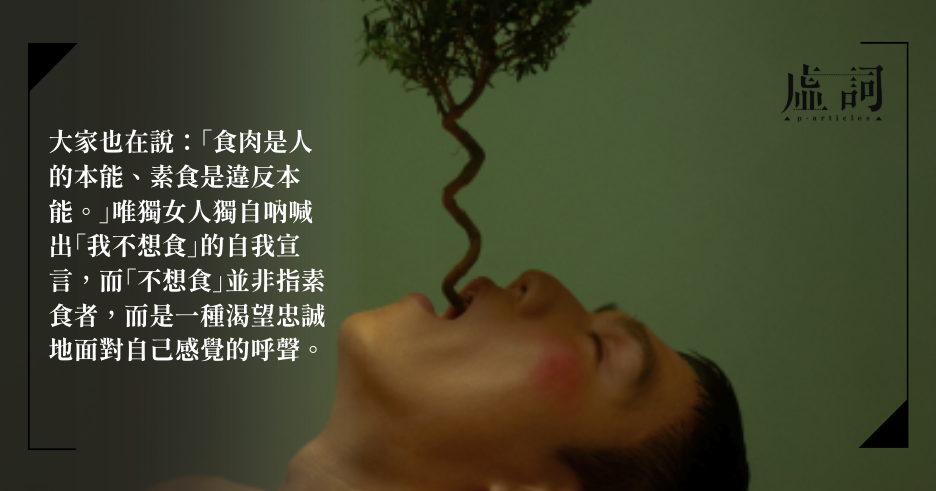
文|張紫敏
去年年尾看了在西九自由空間由本土中小型劇團「藝君子」演出和編導的《植物人》,大量的劇句、畫面、聲音一直在心中縈繞不去,在youtube反覆重播植物思人「植物誘讀」《植物人》的劇本。在語言碰撞之間,重新回溯一次現場觀賞時的心悸與戚然,假如記憶是載體,萬物也會如樹影婆娑,擁擠、影影綽綽而深刻。在導讀劇本和實時演出的時空穿插間,簡易歸納《植物人》的三條記憶線索。
第一根漣漪線是《植物人》中女人的自我切割與流露。女人有日夢見自己成為了「不吃肉的野獸」,在夢中她看見意象:「自己在漆黑的森林中,不論臉、手腳、睡裙都沾滿了血,夢見牙齒咬入怪獸的身體,撕開、咀嚼,雙手嘴角都是鮮血,地上佈滿一片泥土,天上倒吊一棵樹,一切變成草綠色。」夢境醒來以後,女人發現自己並不能再吃肉,家中從此不可再有肉、雞蛋、牛奶、芝士的製品,與丈夫的生活方式從此走向極端。不論在丈夫同事和家庭飯局中,女人望著大家咀嚼般的嘴巴,大家也在說:「食肉是人的本能、素食是違反本能。」唯獨女人獨自吶喊出「我不想食」的自我宣言,而「不想食」並非指素食者,而是一種渴望忠誠地面對自己感覺的呼聲。當大家都毫不保留地否定和嘲笑女人,皆因面對誠實的流露,心存善念的人會襲擊自己,惡念和貪婪纏身的人會對抗、操控和消耗與自己不一樣的人。即使女人解剖不吃肉的內在誓言,那美其名高舉「誠實」的旗幟,卻散略了誠實的本質在人類社會具有一種危險性,若那份「誠實」非為世所容,也注定面對來自家庭、親朋戚友萬箭穿身、千刀萬剮的下場。

第二根漣漪線是女人與姐夫(外甥)纏綿與憐憫的契約。姐夫(外甥)是攝影藝術家,看著女人為世界終極的沉默者發聲,以割開乳房的方式表達內心對自由的渴望。姐夫(外甥)深信女人會引領他創造超越人類的藝術。他說:「自殺不是因為衝動而是筋疲力盡。」直控對世界毫不留情的否定,但是女人並沒有表示自己在自殺,只是因為心口鬱悶。女人說了各樣對身體的形容:「西蘭花像自己下體的陰毛」,思維清晰果斷。姐夫(外甥)像得到了往生的力量,他把各式各樣的花朵投影在女人身上,任由她感受身體上的花,解放身體的鬱悶。女人開始合上眼地擺動身體每一寸肌膚,表演者也在不自在地配合著女人的律動。姐夫(外甥)看著綻放的女人,說出:「細妹的身體帶領著白天、夜晚的牽牛花、當花留在身體也許可以不再發夢。」姐夫相信自由,也同時排斥了原來創作必須重視每一個個體的意願,那企圖以藝術之名來行道德綁架之實,被表演者當頭棒喝稱自己比自己想像中保守,隨心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要求結束拍攝,離開現場。餘下女人與姐夫時,女人說:「下面太濕」,長久的靜默,女人說自己最驚人,要滋潤的是花不是人。姐夫以象徵葉的綠色油漆塗滿全身,與被花瓣覆蓋的女人進行各式各樣光合作用的交合,姐夫(外甥)說女人身體盛載著所有的秘密,她是奇異之花,要吸乾所有馨香的水份。所有交合的儀式都進行過後,攝影機一直在拍攝與記錄,女人再度發夢,在夢間她既是兇手也是受害者,那對象是最親近的人,以斧頭一直劈,一直劈落腰,碎裂和拉扯,毫不溫柔地進行毁滅。

最後一根漣漪線,是姐姐的告白與懺悔。姐姐說從小到大都把妹妹的存在當作一種襯托,只要有妹妹在,姐姐永遠都完美無瑕,由外至內,毫無可比擬的空間,姐姐卻一次也沒有為被爸爸打的妹妹發過聲。劇尾妹妹在精神病院斷食多時,被眾多醫護以粗暴的方式結束妹妹異於常人的綻放,姐姐從旁監視醫護進行灌輸,「妹妹望著姐姐」、「姐姐望向妹妹」沉默一番,嘶吼聲遍達全身,姐姐恨丈夫、恨妹妹,卻發現自己責無旁貸。姐姐把佈滿鮮血,在被灌上營養液的妹妹身軀中,拔除最致命的喉管,直插喉嚨,以轟烈的方式了結生命,在血肉模糊的創傷轉移儀式中,告白對妹妹抱疚的愛,同時懺悔「姐姐」這個身份給予一切懦弱與罪疚感,悄悄地保留相依為命的私心,渴望同歸於盡是一種解脫和到達生命樹的橋樑。或許在人類社會中,還沒有研究結果證實植物擁有痛苦的感覺,所以枯萎與摧殘植物並沒有爭議。妹妹:「點解不可以死?」 姐姐:「你亂說什麼,天黑了,要回家。」假如能捉緊如姐姐對妹妹微弱的愛,誠實地與妹妹交換來自穿插人類肉身的疼痛,姐姐關閉了雨傘的保護罩,回到「無口、無舌、無耳,無目、無嗅、無形」空相的狀態。此生再無執念,化作修渡人。

結尾是對存在的拷問,讀劇中姐姐與妹夫重逢,說在鄉下有棵核桃樹,五十年前那根傷害核桃樹的釘子,在風吹雨打,被眾多男人出盡力用斧頭砍掉了上半身後,發現那根釘子並沒有消失,只是成了身體的一部份。傷口不會走,但生活卻悄悄把傷口埋葬,在埋葬的過程,為了袪除這種恐懼,就是刻意到達恐懼和傷口出現的地方。一如女人有天在夢中醒來發現自己毫不喜歡吃肉,肉除了盛載罪惡的起源,也是人類生活的慣性,那份並不如主流般一樣,自我變得格格不入,那種在胸口切割的瞬間,由外到內解剖痛苦,任由不曾醫治的感覺記憶在某個時刻襲擊,或許就可盛載起埋葬在混濁的土壤,那份連根拔起的軟弱與碎裂,獲取生命的眷養與自在的救贖。

筆者很慶幸能趕及尾場,總覺得近數年的社會氣氛一直有種鬱悶的內傷,無從訴說也不斷訴說,是深沉的集體哀傷連續劇,也許即使無從訴說,安靜地修補自己,填充他者,滋養治療的氣味也未嘗不可,生命還得在創作中時時更新、滋長與創造。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