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闇与幽光—对弗洛伊德《释梦》的理论解读(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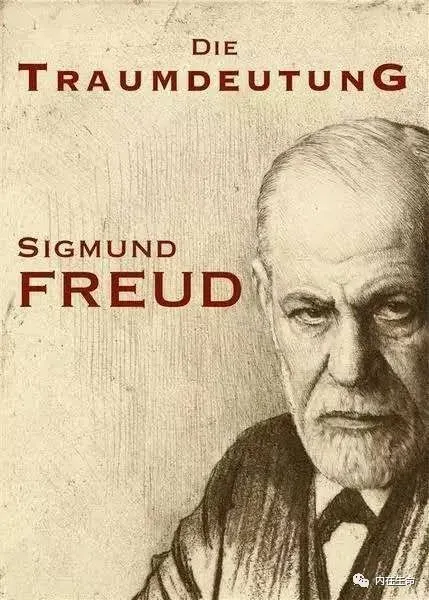
原初与继发 压抑
之前的描述一定在某种程度令读者眼花缭乱, 但这不全是我的问题,尽管我也反复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接近弗洛伊德的愿意? 究竟有没有恰当的表达出来? 对于梦这一晦涩深奥的东西,我只能遵从弗洛伊德的建议,将其拆分,大致描述各个顺序过程,再试着组合起来。 还要提醒读者们,绝不能真的认为梦过程有固定顺序。 为了说明释梦理论在精神分析中的基石地位,我也不厌其烦的把梦和异常心理综合加以考虑,关于这点,弗洛伊德自己也抱怨,他的目的本来是从梦出发再到神经症心理学,但实际工作又不得不把两者杂糅在一起。 要我说,这既是弗洛伊德的谦虚之处,也是伟大之处,他总是擅长在不同事物、不同意见间寻找共同点,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
读者们可以参阅《梦的解析》第一章导论部分,里面罗列了历史上对梦的观点,可谓五花八门又尖锐对立。事实上,经过对诸多梦的议题进行逐一分析后,弗洛伊德承认,大部分的观点都反映了梦这张复杂大网的一部分真相,所以是有一定道理的。唯有两个观点要坚决反对:其一,认为做梦毫无意义,其二,认为做梦仅仅是一种躯体过程。为了方便读者,我将这些历史观点和弗洛伊德的评论列举如下:
1、在显梦内容中发现的隐藏梦念,以及它们和白天清醒生活的直接关联,证实了 “梦是清醒生活的一种延续”的说法。
2、对梦念的分析显示,梦关心的都是对我们很重要、也格外感兴趣的事情。
3、认为梦只会捡起前一天留下来的不起眼的事件也不无道理,这是直接观察显梦的结果。为了化解与前一观点的矛盾,弗洛伊德认为,显梦是隐藏梦念伪装后的产物,在伪装过程中,重要且关心的事物被移置替换为近期发生的不起眼、无关紧要的事物,因为后者与游离于现存思想链条,不被清醒思维看重,正好能被隐藏梦念利用:于是重要但是粗鄙、不道德的内容,将它们的能量强度转移到不起眼和无害的材料上,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逃脱了稽查。
4、梦能够增强我们的记忆,并能够支配童年期的材料,这一事实已成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石之一。童年记忆,特别是起源于婴儿期的愿望,是梦的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只有找出了那个被深深埋藏的童年愿望,才算是比较深入的分析了梦。
5、睡眠中来自外部的感觉刺激可以生成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弗洛伊德强调,感觉刺激和梦的愿望的关系,就像素材和主旨的关系,它们和日间残留经验具有同等地位。梦对外部感觉刺激的反应是戏剧性和幻觉性的,这也无需否认。原因在于,梦要把这些刺激诠释为一个符合主体经验的合理故事,从而避免刺激干扰睡眠。
6、绝大多数梦都是感性的,有人认为这是睡眠时感官的主观兴奋导致的,弗洛伊德承认这一现象,但解释说这是由于支配梦的活跃记忆,一路退回最初形式所造成的知觉兴奋。
7、身体内部刺激在梦的形成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也只是相对次要的位置。诸如口渴,尿急、饥饿、性欲、疼痛等,都会被演绎为相对逻辑的剧情,梦也会活用跌落、漂浮、受禁等感觉,仿佛它们是范文模板一样,在不同种族、民族、年龄的人群中,我们都发现了这类典型的梦。
8、参照现实时间,梦的过程迅速而转瞬即逝,但就梦者的主观时间而言往往进行了很久,无论是记得的内容还是分析出来的内容都非常丰富。对此应解释为,这些内容是已经精心准备好的,后来才被意识知觉。梦的前期工作往往漫长而曲折,甚至在白天就开始预备了,弗洛伊德觉得有些复杂的梦可能需要准备一整天甚至更多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如果梦巧妙的套用了心灵世界中现存的结构,它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呈现非常丰富的素材 ,这可以比拟为电子文件的解压缩。
9、人们对梦的回忆是扭曲又残缺不全的,属实但并不妨碍我们的解析,因为梦的伪装贯穿全程,记忆的扭曲不过是最表面的一层罢了。只要我们像尽忠职守的警探一样不轻视任何细节、不放过任何疑点,再巧妙运用一些手段,相信再多的伪装也会露出破绽。
10、弗洛伊德认为自己调节了历史上看似水火不容的争论:心灵是否在夜晚也睡着了?以及是否和白天一样具备完整的功能?他说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又都不够完全。梦发生在睡眠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分析工作已经从隐藏梦念中发现了和白天一样的高度复杂的理智活动,且这些活动似乎动用了大部分精神资源。分析能发现它们 和白天思想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能否认:梦念形成始于白天,梦是白天思想的延续。于是这表明心灵在夜晚也能行使其功能。但我们也考虑过极端的情况,即睡眠时心灵和白天一样完全运转,将不会产生任何梦,可严谨的实验证明任谁都会做梦,所以又必须假定,心灵有类似睡眠的状态。所以认为“梦是部分的睡眠”也是有道理的,可这种睡眠绝非固有精神结构的解体,而是白天占据支配地位的目的性思维被调整为专注睡眠的愿望。心灵必须撤回对白天关注内容的能量投注(兴趣)才能入睡,与此同时运动系统也暂时关闭了,这非常有利于回归运动(但不是唯一因素)。
11、认为睡眠时观念流向就不受控制,这是片面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没有目的的思想。睡眠的确中断了有意识的、自主的思考与反思——这一事实往往让人不假思虑认定自己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当它们暂时离场后,立即会有先前未意识的,不自主观念占据舞台。后者受制于潜意识系统,目的往往更加单纯,从外表上却很难看出来。
12、梦中的联想关系看起来格外牵强甚至荒谬,这很常见。但这些表面联系在梦中起的作用远不止被看到的那些。它们实际上被迫替代了另外一些更生动、更重要、更受抵制的联结。弗洛伊德愿意承认 “… 梦是荒谬的….为了表现出这种荒谬性,梦动用了极其智慧的手法 ..” 【1】
【1】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47
至于历史上赋予梦的那些功能,弗洛伊德也持开放态度。梦作为心灵的安全阀门,将一切有害的事物都转化为无害,这契合了精神分析的双重满足愿望,我们认为通过做梦来满足(不被允许的)欲望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们也发现了前意识活动的功能和意义,它允许梦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发挥、自行其是。在日间生活中被压抑的原始运作方式,在梦中又卷土重来.它们密切参与了梦的构建,因此梦将心灵带回了胚胎状态,是“一个充满丰富情感和不完善思维的古代世界”( 哈夫洛克.埃里斯 1899)弗洛伊德高度赞同萨利[1893]的观点:“梦会重温我们渐进发展中的早期个性。在睡眠中,恢复我们原来看待事物的方式,回复到很久以前曾支配着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之中。”至于“梦的驱动力量来自被压抑的内容”,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设了。
梦中想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并不是梦创造了想象,而是受潜意识控制的联想过程占了梦念生成的主要份额。某些情况下在白天也处于活跃状态的潜意识活动,既是梦的诱发动因,也是神经症症状的诱发动因。但这种潜意识活动与“梦的工作”完全不同,后者要受到前意识的多重节制,因此必须区分讨论。在临床实践和理论推(精神装置的假设)后,弗洛伊德进一步确认了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将之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上。
以上论述充分显示了弗洛伊德最惊人的长处:他总是兼容并蓄,擅长在矛盾寻找共性,虽然多借鉴别人的理论和术语,却总能无缝融入自己新创的一整套体系中。关于梦的体系只剔除了少量完全错误的观点,容纳了先前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说法,对一些片面的观点进行了二次诠释,因此较先前诸理论,它形成了一个更高的整体。不过弗洛伊德也坦诚,这个体系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因为它还不能解释梦的另一个突出矛盾,即我们在梦中发现的某些过程,与清醒时的正常心智活动别无二样,另一些却与正常心智活动有天壤之别,例如,显梦中认知的错乱性和不确定性,某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元素,比奇美拉【2】还杂糅的人物形象,看起来像是好几个人物的集锦;进一步分析显示,某些毫不起眼或荒谬的元素,竟然是极为重要元素的替代。正常生活中怎么会出现这些怪异的过程呢?张三只能是张三,不可能即像李四,又像王五。现实中的人物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在梦中它们竟然能相互替换,对张三的情感会完全转移到李四身上,实在匪夷所思。这么来看,梦的确把作为心理正常指标的知、情、意一致破坏了,以至于严厉的批评梦具有一种病态、梦的过程非常原始、功能水平低下,似乎很有道理。
梦频繁的将两种非常不同的过程杂糅在一起。该如何理解这一突出矛盾呢?或者说,能不能用现有理论来加以说明呢?弗洛伊德发现这一点也行不通,所以他只能新加假设。
他首先提醒我们,先前的研究已在梦中发现了许多合乎逻辑和理性的思想,其复杂程度一点不逊色与清醒思维,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思想都起源于正常的心智生活。心智生活所具有的一切特性,也即那些标志着我们的心智属于复杂的、高阶精神活动的东西,都可以在梦念中找到….”【3】。要说梦独立完成这些过程未免夸张,这意味着心灵在睡眠中保持着完全清醒。所以,这些过程完全可能在白天就已经在运行了,但或许未能被意识觉察,梦延续了白天未竟之任务,甚至取得了在清醒时难以达到的成就。弗洛伊德继续评论说:”….最复杂的思想成就,也可以不需要意识的参与…”。
【2】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有着狮子的头,山羊的身躯,蟒蛇的尾巴。
【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48-549
【4】对神经症的分析同样可以在病态信念中,找出一些合乎逻辑的思想,它们和某些梦念一样,唯独在清醒时不能成为意识。这让我们感到奇怪,但考虑到意识的特性,或者说,成为意识的条件,或许能有所帮助。在讲愿望满足时,弗洛伊德提到梦为了突破前意识的限界,从观念回归知觉来吸引意识的“注意”,强度不够的梦在夜间蛰伏,等待逐渐清醒的注意力觉察到自己。“被意识“似乎还需要”注意”的配合,注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功能,与被刺激客体或目标发出的刺激量有关,也会因为不同刺激客体的强度而游移。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跑偏就是由于新的刺激引起了注意—从当前刺激上被动移开。我们常说的集中注意力,就是指主动将注意聚焦在某个刺激客体上,也就是说,沿着某个特定路径分配注意,保持专注,就像敌后活动一样。如果在前进中遇到了某个经不起推敲或批评的观念,就直接放弃掉;也就是说,将注意从此观念上移开——中止注意的投注。可是,这些被瞥了一眼又匆匆放弃的观念并没有就此消亡,似乎还在缺少注意的环境中继续发展了。在对梦和神经症分析过程中,我们不禁好奇,这些观念后来是如何获得力量迫使意识再次注意它们的。弗洛伊德评论说:“….一个思想如果一开始就因被判断为错误或对眼前的理智活动无用而被(有意地)拒绝,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它将在不受意识注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直至睡眠时才被意识到…”。或许我们可以用明暗交替的隐喻来理解这一精神现象,那些值得注意的思想进程得以在阳光下继续发展,而不被接受的进程则遁入暗影,等待重见天日的时机。
这一思想即“前意识的思想”,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但某些观念进程不一定符合主体目前状况或违背社会道德,因而有可能被中止、压制,不再允许成为意识。一个目的性观念出现后,引起了注意,于是”…一定数额的兴奋刺激便被移置到这一观念所选择的不同联想途径上。【5】这种兴奋就是我们所谓的“能量投注“(cathectic energy)。因此,“被忽视”的思维过程没有接受到能量的投注,而“被压抑”或“被贬斥”的思想,就是指投注在其上的能量被撤回了….”【6】这里出现一个疑问,因为弗洛伊德假定所有驱动力量来自潜意识愿望,那么前意识何以拥有力量甚至反过来约束潜意识呢?对此不太严谨的假设是,前意识是通过与现实和语言符号系统的密切联系获得力量的,或许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就有力量,但弗洛伊德没有明确讨论过【7】。后来他把前意识和意识系统(甚至包括一部分潜意识系统)合二为一称为“自我”,说自我是它的“大型能量储槽”【8】,不过后来的研究者还是在两者的从属性上发现了漏洞,此处不做讨论。
有时候,某些目的性观念思想(例如症状)成功引起了意识的注意,并因其效应获得了额外甚至过多关注。分析表明它们曾在很长时间内遭到压抑和拒斥,显然在这一时间段它们无法再获得前意识额外的关注,只能靠自己剩余的能量独占发展。弗洛伊德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或经历了什么变化后,这些思想再度成为了意识。
【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549
【5】这一观念就像枢纽,联系着许多联想路径,它激活的是一系列联想网络。
【6】方厚升译《梦的解析》550
【7】雅克.拉康发展了这一思想
【8】参见《自我与它》
显然,前意识的思想序列有两种命运,即可以自发中止,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对于第一种情况,弗洛伊德假设这类思想序列所具有的能量沿着联想网络扩散,就像火光在暗处辐射一样,暂时的激活了思想网络并持续一定时间(照亮黑暗),但由于缺乏前意识额外的投注,它的能量很快就耗尽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从寻求释放的兴奋变成了静止的投注(即停滞状态)。人们常常会遇到这种尴尬:方才想的事情,转瞬间就完全忘了。有时候脑海中灵光一现,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再也看不到了。(对那些依赖灵感创作的作家、艺术从业者来说尤为痛苦,以至于有些人常常主动服用致幻剂,试图找寻所谓的灵感) 如果出现这种结果,这些注定要被耗尽、注定要被废弃的思想就不能再对梦的生成有贡献了,除非,它们能找到支援,或者找一个新的安身之所。
如果再把精神装置的地质模型拿出来,可以很形象的比喻,这些失去关注的思想,从意识和前意识的交会区域一路下滑,越来接触底。这个过程中它会遇到另一些前意识思想,它们在空间上与潜意识极为接近(即我在上一章所说的潜意识——前意识交会区域),在形态上是极为活跃的潜意识愿望衍生物,失去关注的思想会被它们吸引,从而与其背后的潜意识愿望建立了联系,这些失去关注的思想也可以成为移情对象了。这样,被压抑和拒斥的思想就能继续维持活力了,但它负荷的能量还不足以使之上升进入意识。形象的说,潜意识尽管在前意识内安插了代理人,但仍需蛰伏静待机会。它们还见不得光,只能继续在暗中、在地下积蓄力量。这就是弗洛伊德说的“这些前意识思想被拉进了潜意识”。确切的说,被拉进了潜意识和前意识交会的区域。
在梦或症状形成中还有其他的思想联结形式 ,前意识思想可以先与潜意识愿望结成同盟,再被居于主导的目的性投注拒斥。或者某一潜意识愿望由于某些原因(可能是躯体性的)进入兴奋状态,主动的在前意识中寻找合适的代理人,转移自身的能量【9】。
【9】 参见《性学三论》
不论哪种情况,最终结果都是在前意识——潜意识的间隙产生了一种思维过程,它不从前意识系统获得能量,但能得到潜意识愿望的支援。从它被“拉入潜意识”的那刻起,它就不得不服从潜意识的规则了,经受一系列面目全非的变化后,它再也不能被视为正常的精神过程了,而应被视为病理性过程。
弗洛伊德列举了下列令人费解的转变:
1、单一的观念可以代表由它联结起来的许多联想链条,用一个元素代表许多相互联结的元素,这些元素原先附着的能量都汇聚到一点,形成了一个负荷巨大强度的代表观念。这一过程即是我们熟悉的凝缩作用。梦中那些结合的、不协调的人物形象便经过了凝缩,它尤其令我们惊讶,因为在正常的、有意识的精神生活中找不到相似物。的确,我们能发现另一些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复合物,例如一段滴水不漏的应答,一句承上启下的妙语,它们既可以是整个思想链条的枢纽,也可以是思想的最终结果。但它们既不作用于内在知觉,其重要意义也不是通过醒目的感性形象直接刺激知觉才获得的。总之,它们的知觉特征不会因为精神意义变得更突出。除非,人们在说话时故意提高某些字词的语速和语调,或在书写时刻意把某些字写的与众不同。凝缩作用比上述例子要极端许多:原本复杂有逻辑的精神联系都被简化为直观的内容强度.例如梦中显赫的复合人物,这些人物和主体的、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化约为某一突出的视觉特征——A的头发,B的脸型、C的五官、D的形体、E的衣着、F的动作。相对而言,人物间的差异则被淡化或模糊了,似乎是在保持或增强共同特征,但整体却是不协调的。例如弗洛伊德的伊玛打针之梦,那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三甲胺的分子式,特别醒目”。我不禁想到在游戏中,精英怪物总是比普通怪物更大,装饰或武器也更加精良,而且常常被缺乏特色的大众脸簇拥在正中。这正是对古代雕塑手法的效仿:用大小、位置、精细程度表示人物地位的差异:国王的形象最初要比侍从或手下败将大很多,仿佛侏儒中的巨人;后来的雕塑更加写实,但目的不变:精雕细琢的帝王形象位列正中,傲然挺立,他的敌人则匍匐在脚下。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当代下属向领导鞠躬行礼的现象,可谓是古代表现原则的余音。凝缩作用的方向(或目的)要受到两种因素制约,因为它生成的梦念,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前意识内听觉、字词、文字间的真实关系。但在梦念向知觉的回归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潜意识中视觉回忆的吸引,于是凝缩作用的目标就在于聚集足够的感性强度以突破知觉—意识系统(吸引意识的注意)。这里要澄清一点,即不能把凝缩视为一种摘要,因为根据显梦的内容可以推测多种隐藏梦念,后者又分别衔接更多潜意识元素,涉及到精神装置的不同层次(跨系统),而摘要则是在意识的层次概念化某些含义。
2、由于观念、意象之上的能量可以自由转移,带有妥协色彩的中介物就会形成,后者暂居于潜意识和前意识的交会区域,可以上升到前意识。例如在朵拉第一个梦中,珠宝盒【10】—珠宝—女性性器的一连串联想,珠宝作为“童年对母亲的嫉妒、性交分泌物、自慰的污秽、以及当前的诱惑这些潜意识思想交汇的十字路口”。弗洛伊德说这在正常的观念进程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正常观念进程要求精确选择适当的元素,拒绝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就是有一说一,就事论事。这里可能有人会反对,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使用双关语、话里套话等方式,好让旁人揣摩。对此我的看法是,这些方式当然不是正常的。有时候说话人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言外之意,或者明白直说是不合法或不道德的,只能用隐喻旁敲侧击。毫无疑问,这样避开令人尴尬、危险或不快的方式,和梦的伪装极为相似。另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口误,前意识内相互矛盾的观念争相要表达出来,就制造出混合妥协式的结构,说话人稍后才意识到说了不该说的东西,只好用不小心来掩饰。
【10】参见《朵拉—癔症病人的分析片段》
3、作为上述现象的结果,可以相互转移能量的观念或意象,就以一种非常松弛的形式联系在一起。把它们串联起来的联想,往往遭到主导思维批评或现实制约,只能通过笑话、俚语或艺术手法来暗示,如常见的同音联想或双关联想,它们用表面联系取代了真正的联系。这可以解释许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病理现象,如在强迫症中,病人因为观念A而悲伤不已,尽管他感觉非常荒谬,却不能自控。分析发现,真正导致病人悲伤的是另一个观念B,如果把B作为病源核心的话,A充其量是附带情境。病人却对其中关系一无所知,尽管观念A是产生强迫的观念,但其强迫力量却来源于B。
4、我们通常用水火不容来形容某些不相容的思想,但在很多场合下,这些思想居然能携手并肩,而不是尖锐排斥,令人深感意外。矛盾似乎被弭除或达成了妥协—某些在台上义正言辞做反腐报告的人,背地里却大肆收受赃款;医生可以大谈吸烟的害处,自己却一根接一根吞云吐雾。某些思想,人们对它绝不容忍,高调反对、严厉打击—却放任它支配行为。在朵拉案例中,朵拉的父亲勾搭上了克劳斯夫人,他们亲密的举止引来许多好事者的流言蜚语。但朵拉却完全视而不见,她非常崇拜K夫人,视为密友,【11】即使女家庭教师很直白的说出父亲的秘密。后来因为某事,朵拉突然打开她的双眼,看清了父亲和克劳斯夫人友谊背后的真相,她于是激烈的攻击父亲背叛家庭,贪图享乐出卖了她,对她不管不顾,奇怪的是,对那个勾引父亲的女人,她却恨不起来。
在任何精神异常现象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原本正常却变异了的思想。我们也发现,以正常方式形成的梦念在梦中经历了多种异变,以上4种最为显著。弗洛伊德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中发现了惊人的共同特征:…这些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其全部重点在于使贯注能量能够自由活动并得以释放,反而其具体内容和意义,倒无关紧要了…”,【12】正常思维有方向有目的,能量受到约束,而异变的思想只求自由释放。两种形式的能量释放可以类比生活常识 :汽油很容易被引燃引发爆炸,但也能经过一系列复杂进程,有序的释放能量推动精密的机械运作。前面我们说过梦的视觉表现力话题,如果梦要完成将思想转化为图像的任务,使某些感性材料更醒目,那可否认为凝缩、妥协形成是专门为知觉回归服务的?弗洛伊德提醒说,还有一类完全观念的梦也具有凝缩和移置的进程,和意象的梦没有区别。
以上事实让弗洛伊德“….不能拒绝这样一种假设,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过程参与了梦的形成,其中一个过程产生与正常思维等价、完全合理的隐藏梦念,另一个过程则以最令人费解、毫无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些梦念…。”【13】这第二个过程就是《梦的解析》第六章讨论的“梦的工作”,严格的来说就是凝缩和移置过程,(象征指的显梦元素和潜意识内容的先验关系,润饰作用发生在前意识和意识之间,严格来说不能算梦的工作)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些机制的起源呢?
梦的研究无法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另一个领域,即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那些匪夷所思的异常思维过程(我们对此知道的仍不多)决定了症状的形成,随着分析愈加深入,一种合乎逻辑的正常思维便愈加清晰可辨。它与意识思维等价,完全可以理解,但起初完全被异常思维感染了。精神分析从看似毫无关联的病态思维中提取出合情合理的思想、重构病人的心智和历史,就如同从荒诞不经的梦中提取隐藏的思想一样。看起来,原本正常的思想遭到了异常的处理,“…. 通过凝缩作用和妥协形成,经由遮掩矛盾冲突的表面联想,逐渐沿着回归作用的通道,这些正常的思想最终转化成为症状….“【14】弗洛伊德再度提醒我们,症状形成其不遵循着和梦的工作同样的道路?两者岂不具有完全等同的特征,以至于把对神经症的研究应用在梦身上,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弗洛伊德从神经症理论中借用了下列命题:”….一个正常的思想,只有当一个源于童年并一直被压抑状态的潜意识愿望移置其上时,才能经受上述异常的精神处理….”【15】也就是我反复提到的,正常思想成为异常思想的代理人。关于构建释梦理论的基本假设,弗洛伊德如是说,“…作为梦的驱动力的愿望永远源于潜意识….”【16】 这一点已经无需多加论证了,不过,对于前文反复提到的“压抑“一词,必须进一步明晰它的原理和运作机制。
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精神装置的假设中去。已知这一装置遵循着基本的反射原理,目的是为了避免兴奋在机体内积累并尽一切努力保护自己免受刺激的影响,当刺激来临时,它试图通过逃避、战斗等运动方式卸除。但这些应对方式只适合外在的刺激,对于内在刺激(欲力)的“需求”却无能为力,除了“满足”这种需求,使刺激降低外再无他途。婴儿的原初满足经验只能通过哭喊唤来养育者的特定行动才能实现,这种原初高峰体验产生了一种难以估量的精神结果——与满足、快乐有关的一连串联想,【17】包括自身的行为和对象的反应,都会被印上最深的烙印。我们已经假设,兴奋刺激的累积,将会被体验为不快和痛苦,【18】精神装置力求回复到初始的平静状态,降低刺激水平,重建满足的快乐的经验;并且说精神装置内部这种起始于痛苦,终止于快乐的兴奋流向就是所谓的“愿望”,断定它是唯一的动力来源;我们认为精神装置内部过程自发的受到痛苦和快乐的调节;“愿望”第一次出现时,企图凭空再现原初满足的高峰体验知觉,“愿望满足”即把能量完全投注在满足记忆上(此时的记忆以不连贯的动作、图像、感觉存在),把满足的记忆完全复制出来,产生幻觉并进一步开启运动之门。(如婴儿吸吮自己手指的行为)弗洛伊德进一步推断说,知觉的最初形式都是幻觉。精神装置面临的困境是,维持幻觉性满足需要不断的消耗能量,而需求仍在呼唤,那虚妄的快乐能够持续多久,能否一直抵消需求高涨引发的痛苦?看起来,除非为幻觉耗尽所有能量,是无法停止需求的,也就是说,主体无法长久维持愉悦感,终将认识到幻觉满足并非真正的满足。【19】
【11】 参见 参见《朵拉—癔症病人的分析片段》
【12】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2或车文博译本p370
【1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3或车文博译本p371
【1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3或车文博译本p371
【15】同上
【16】同上
【17】即上文描述的精神装置内部的通路
【18】大多数情况下。但在性爱的预备阶段或受虐倾向中,兴奋的累积产生快感。
【19】 无疑 痛苦在此得到了最大化
上述过程可谓精神装置的原始运作方式,由于和生存之道相违背,必须被调整为更符合现实的模式:一种继发性的活动:它依旧要搜索记忆,但绝不允许对记忆投注全部的能量,以阻止记忆变成知觉,过去覆盖现在。曾经是自由的能量被束缚,被引导指向某一具体方向。由需求引起的兴奋现在被导向一条迂回的途径,最终通过自主运动的手段(特定行动,由最初的求助发展到自力更生)改变外部世界,从而抵达了对满足对象的真实知觉。在弗洛伊德那个精神装置示意图中,原始的活动和继发性活动分别代表了两个系统,即潜意识和前意识系统的萌芽,而我们常说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属于充分发展的系统。
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就指出,贸然将记忆判断为知觉,并产生某些反射运动带来的必定是愿望的落空,此时必定导致更大的痛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要有某种“现实的指标”,由它来判断记忆和知觉的差异,避免对记忆投注不必要的能量。弗洛伊德早就发现,潜意识里不存在现实概念,这一现实的指标只能存在于前意识—意识中。让我们假设一种原初的痛苦经验:由于离开母亲子宫造成的刺激积累,引起了婴儿痛苦的感觉和杂乱无章的运动表现。直到某一种运动(例如哭喊唤来了奶水)成功卸除了这些刺激,弭除了痛苦情感。除了满足经验外,精神装置还而建立起不快的感知印象和特定运动的联想关系:如果痛苦再现,重复的运动就会再度展开。我们还知道,幻觉满足可以暂时抵御痛苦,但痛苦犹如高涨的洪水,最终连堤坝都淹没,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它就完全不可遏制了。就原始的精神装置而言,刺激量的累积唤起了愿望,而刺激量的剧变变化引来了情感(痛苦是刺激量的暴增,快乐是刺激量的暴减)。精神装置必须阻止痛苦情感再现,甚至优先于获得快乐。
前意识的萌芽被赋予这一功能,我们已经说过,前意识系统依靠着与意识和语言符号的邻近关系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潜意识系统的行动能力。【20】它一方面要支配各种记忆经验,经验之间持久的联系关系,一方面要朝向外部世界,时刻留意必要的讯息。最后,它必须调动注意力系统警戒任何引发不快的记忆,不允许对后者投注能量。可想而知,由幻觉导致的愿望落空位列排斥名单的榜首,而真实满足的知觉(即那种消除痛苦的特定行动)最受主体青睐,对痛苦的知觉和对真实满足和客体的知觉构成了某种质的指标。如果需求再度出现,记忆中的满足客体也随之被投注,前意识系统必须暂时禁制能量的自由流通,暂停反射行为,直到它收到了足够的现实指标,确保这是真的,与记忆中的满足客体相符【21】。前意识系统就像一台生物计算机,不断的扩充和检索记忆,不停的认知和判断,试图找出最适宜的活动模式。
我们已经知道,潜意识系统负责提供驱动力,前意识系统行使着禁制功能,掌握着运动的钥匙,它们时而合作,时而冲突。前者力求无障碍的满足,后者必须利用自己的能量完成初步探索,直到发现目标符合预期时,才会解除禁制,让运动——释放积累的兴奋发生,改变外部世界。反之,前意识系统会撤回对潜意识愿望的能量贯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弗洛伊德假设,前意识系统需留有必要的能量作用外部世界,不能漫无目的的在所有的记忆和联想路径上做无谓浪费,因此从功效性角度,…这第二系统成功地将大部分能量贯注保持在一种静息状态,只将很少的能量用作移置作用…. 【22】弗洛伊德坦诚并不清楚这类过程的运行机制,但认为必须向物理学求助,来阐述神经元的兴奋过程【23】。以下结论是从临床实践中推演出来的:Ψ系统中,潜意识子系统的目的在于“….让兴奋能量可以自由流动释放,而第二系统通过第一系统【24】(自己)发射的能量贯注,成功抑制了这种能量自由释放,并使其转入静息状态,同时也可能会提升它的能量水平…. 由第二系统支配的兴奋释放机制,与第一系统支配的释放机制完全不同。【25】”
在我看来,这第二系统即前意识系统最初似乎是为了更有效的回避痛苦情感而发展出的。快乐往往和现实无关,但痛苦一开始就与现实关联,因为无助的婴儿必须借助外在客体的帮助。早期生活的诸多痛苦中,由幻觉性愿望落空尤为刻骨铭心。这痛苦的经验—和满足经验对立,主体绝不可能试图在幻觉中复现过去的痛苦知觉,这条路必须被封闭起来,如果类似的痛苦出现,即重复过去回避痛苦的行动。已经有所准备的前意识借助注意力系统,一旦发现有引发痛苦的可能性,立即予以消除“…因为这种兴奋一旦进入知觉,则必然会激起痛苦的感觉。或更精确地说“开始激起…..【26】”这里弗洛伊德指出“…. 记忆和知觉不同,它不具有足够的强度来唤起意识,因而无法从意识中获得新的贯注….“【27】。区分知觉和记忆,对记忆的能量投注加以禁制以防它变成知觉是前意识系统的工作,对痛苦记忆的禁制和回避是首要工作,….. 精神过程能够轻易和频繁的避开对不快经历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精神压抑的原型和最初范例。在成人正常心智生活中,基本上还保持着这种对痛苦的刻意回避……【28】
以上就是弗洛伊德关于“痛苦原则“的初步论述【29】。就潜意识系统而言,它一心只想复现过去的快乐,除了愿望再无其他,它排斥一切和痛苦有关的事物,也无法将这部分经验带入其思维过程。如果维持这种状态的话,前意识系统不能顺利活动了,因为它需要支配积淀在经验中的记忆。假设前意识系统完全不受痛苦原则影响,无视记忆的痛苦——这全然背离了事实。另一种假设是,前意识系统可以利用对痛苦记忆的能量投注,从而阻止更大的痛苦发生。注意力机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像我们发现手受伤,就会格外留意,哪怕维持不舒服的姿势,暂停一些活动,也要防止碰触伤处或二次感染,前意识系统留意并标记某个痛苦记忆的目的,是以反向投注的方式(某些观念/事物是危险的,不可行的…)阻止它复返,由此抑制了痛苦发展的方向。
【25】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5或车文博译本p372,这里两个译本有了很大分歧,即前意识的能量究竟是自己发出的,还是向潜意识借来,这其实也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暧昧不清的地方。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在《精神事件的两个基本原则》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弗洛伊德强调,从痛苦原则和能量消耗最小原则中可以推论一个假设:“…前意识系统的能量投注意味着对(潜意识)兴奋释放的抑制…. 它是全部压抑理论的关键….【30】“对任何观念进程,前意识系统都要仔细审查,只当它成功抑制某个观念释放痛苦后,才会对其投注能量,如果失败,它就投注对立的观念—先前的观念是痛苦的、坏的、危险的、不可行的【31】;按理说,任何可能逃脱抑制作用的观念进程都不可能进入前意识,因为出现就会引发排斥反应。但抑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滞后性,就像在司法领域,总是经历了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后,才有相应的法律出台。往往只有在亲身体验(只有意识才能感知痛苦)过各种痛苦后,才能在前意识中知晓有关痛苦记忆的性质、某些思维过程、目的的不适宜性。这个道理,挨过打的儿童都知道。
弗洛伊德因此发展了《科学心理学大纲》中的思想:有一类仅被潜意识系统认可的原初精神过程,以愿望满足为唯一目的。它会对愿望投注全部的能量,制造出幻觉满足继而导致痛苦的完全发展,这即是精神装置的原过程。反之,那由前意识能量投注支配的,且代表着对前述过程加以修正的继发过程,则称为精神装置的次过程。【32】
将原过程修正为次过程,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原过程追求兴奋的直接释放,以便借助于积累起来的兴奋总量建立(对满足经验的)“知觉同一性”。但继发过程却试图放弃这一意图,代之以对“思想同一性”的追求 … . 【33】 “ 为此,必须放弃最快捷、也是最无用的幻觉满足,代之以认知、判断、延迟、忍耐后的真实满足。 ” … . 思想不过是一条迂回的路径,它从满足经验出发,以此作为唯一目的,透过自己运动经验的方式,达到该记忆的相同投注 … . 【34】 “ 这条路并非坦荡,常常受到原初路径的吸引 “ … .. 它必须考虑到不同观念之间的联络通路,不能被这些观念的强度所迷惑,但很显然,观念的凝缩以及中介结构、妥协结构等,也必然阻碍着同一性的获得。由于这些过程会在不同观念间相互替代,必然会偏离初始观念的通路。所以,继发性的思想必须慎重地回避这类过程 …… 【35】 ” 痛苦原则在很多方面为思想过程提供了现实的指标,除了一点:对痛苦的过度回避会阻碍“思想同一性”的达成,“…. 思想必须逐步把自身从痛苦原则的专断调节中解放出来,并将思想过程中的情感发展控制在最低程度 …” 【36】 如此高度精巧的活动,只能借助意识和注意力机制才能实现。为此,心灵必先体验和了解痛苦,才能慢慢适应和控制痛苦。这一切的前提是对记忆的掌握,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不惜忍受较小的痛苦。这当然很困难,即使各方面都很正常的人, 其思维过程也不免受到痛苦原则的干扰而失控。
借用神话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精神装置亦有功能缺陷,导致在某些时刻,次过程反而屈从于原过程。梦和各种精神异常现象都是例证。这种功能缺陷是历史——即包括人类也包括个体历史的结果。用纯精神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的心智生活中,前意识系统成熟的较慢,很长一段时间都依附于潜意识。而用身心的观点来看,由身体根源发出(伴随着持续的生物需求)的兴奋脉冲—驱力从出生起就强横的介入心智生活。【37】“…这两个因素都起源于童年期,是从婴儿期以来所经历的身心变化的积淀…【38】”
【30】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6或车文博译本p373
【31】参见《精神分析词汇》中关于反贯注的词条
【32】参见《科学心理学大纲》《喑哑与倾听》第九章、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6或车文博译本p373
【3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7或车文博译本p373以及《精神分析词汇》对知觉同一和思想同一的词条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
【37】参见《欲力及其命运》
【38】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8或车文博译本p374
弗洛伊德指出,“原过程”这一术语让人浮想联翩,不仅仅是从重要性和功效性上考虑,它岂不意味着在时间上更加古老?的确,没有哪个精神装置只存在原过程,这不过是种假设而已,但经验却明白无误的表明,精神装置最初是以非常原始的方式运作,而那些较为成熟的方式是在生命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次过程能抑制和掩盖原过程,但这一优势往往要到壮年时期才能完全确立,在某些个体身上,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39】“…..由于继发过程姗姗来迟,因此,前意识永远也不能对我们的存在本质(由各种潜意识愿望冲动构成)——加以理解和掌控….“。【40】由于原初压抑和固着,理智的光辉永远无法照进潜意识的深邃黑暗中。“….前意识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永远地局限于为源自潜意识的愿望冲动指点一条最合理的道路。对前意识中一切后续的精 神倾向而言,潜意识的愿望都意味着一种必须服从的压力,尽管它们或许可以引开这种压力,将其导向更高阶的目标 … . 【41】 ” 。 我们知道,前意识系统和继发性过程与语言符号系统直接关联,只有到了童年期,才能较为熟练的掌握语言,构建所谓的语义记忆。 ” … .继发过程姗姗来迟的另一个结果是,很大一部分记忆材料不受前意识能量投注的影响 … . “ 【42】 。 它们存在,却无名。
那些源自婴幼儿期的愿望冲动,是无法被毁灭和阻止的,它们就像江河,不能如愿入海,必泛滥千里。这些愿望冲动的满足,常常会与继发性思想中的目标观念相冲突。过去不加掩饰,不问时间地点的欲求受到现实的持续痛击,就算得到了一时满足,所带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就像最初的幻觉满足一样。满足不被允许的愿望,不能再产生快乐情感,而只能产生痛苦了。弗洛伊德指出,正是情感的这种转变构成了压抑的本质。【43】显然这种情感转变也是继发的过程,正如羞耻、罪疚和厌恶感是在后来才出现的一样,这三种因素也构成了压抑的动因。我们知道,只在前意识可以支配记忆的情况下,情感才会受控,对不在它控制范围的潜意识愿望所支配的记忆——依附其上的情感释放是无能无力的,前意识只能尽可能远离这些情感释放。正因为如此,即使潜意识内容将自己的愿望力量移置给了前意识的思想,这些代理人也难以被系统接受。前意识系统拒斥可能引起痛苦的观念,即所谓的移情思想,引发了“继发压抑”。弗洛伊德因此说,大量的童年记忆——实际上,童年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从一开始就被拒绝纳入记忆中,这种情况就是压抑的前提。
我想,凡是那些追求精神卓越的人,都会面临来自肉体欲求的难忍痛苦。不管文明发展到何种地步,只要还留有肉体,人类就一直是动物。人可否将能量投注从前意识的移情思想上一次性、永久撤回?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完全压抑会导致不快的思想?答案自然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源自肉体的欲力——源源不断的供给能量给潜意识愿望,再交给移情思想,于是后者积蓄的兴奋便可能突出重围。器质性原因导致欲力供给无法被切断。举例来说,在俄狄浦斯期,儿童性欲会迎来一次短暂的爆发,直到潜伏期,压抑占据了上风,羞耻、罪疚和厌恶感构建起所谓的堤坝【44】。不过到了青春期,由于性器官的成熟导致了性欲的二次爆发,且青少年已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性行为了,压抑的防线再次受到严峻的考验:虽然失去前意识的支持,但由于获得肉体的支持,潜意识愿望催动它的移情思想大举进军,前意识不得不反过来强化自身对压抑思想的抵抗,加大批判力度,强化所谓的羞耻、罪疚和厌恶感。如果不对那部分思想进行升华,单纯的压抑是不可能的,这里也应考虑体质的原因。有两种压抑失败会导致症状,一是压抑被正面突破,即所谓的精神病,原过程要以生成幻觉形式再现知觉同一性。二是作为潜意识愿望载体的移情思想,通过生成神经症症状,最终以某种妥协方式突破进入前意识。症状不受控制,似乎只能逃避“….由于这些被压抑的思想得到潜意识愿望的强烈投注,同时又被前意识撤回投注,它们便只能从属于原发性精神过程,唯一的目标就是寻求在运动中释放…..”【45】,如:强迫行为。【46】
由此可见,异常心理过程只能发生在被压抑的内容中,实际上也是原过程运作的结果。被前意识所摒弃,却被潜意识收容的思想,从此就只能依靠潜意识提供的能量活动了,可以说它们被原过程感染和同化了。“…这些所谓非理性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正常过程的歪曲及思维逻辑错误,而是从压抑状态中解脱出来的精神装置活动模式….”【47】 代表着心灵早期的运作模式。时过境迁,我们已经认不出它们了,正如对自己童年的遗忘一样。补充说下,从前意识兴奋到运动的能量转移,也遵守与梦、症状同等的模式,那些抓住机会逃脱压抑的思想和反对思想混合在一起表达时,就会出现移置和混淆—通常是口误和过失行为,却往往用马虎大意掩饰本意。当人们试图抑制原过程活动时,就不由自主的增加活动。弗洛伊德评论说,当他致力于了解人类心灵的秘密时,发现高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凡人无法保存秘密,如果紧闭嘴唇,手指就会动个不停。每个毛孔都会泄漏他的秘密…”【48】 在某些需要活跃气氛的场合中,人们会讲一些粗俗的笑话—允许这些原过程思想进入意识,但要在哄堂大笑中释放多余的能量。
【39】 随着步入高龄,原过程似乎又夺回了控制权
【40】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8或车文博译本p374
【41】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8或车文博译本p374
【42】 同上
【43】参见《压抑》、《论潜意识》
【44】参见《性学三论》儿童性欲一节
【45】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9或车文博译本p375
【46】需要说明的是,不受控制的强迫行为在诸多心理异常中都有体现,但是强迫症最为典型。
【47】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9或车文博译本p375
【48】参见《朵拉—癔症病人的分析片段》
我们已经借由神经症的研究完善了压抑理论“【49】….只有来自童年期的性欲冲动,才能为所有精神神经症症状提供动机力量,但在童年发展过程中,这些性欲冲动受到了 压抑(情感发生转变)….“, 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导致性欲冲动又得以复活:一个和先天因素有关:个体从最初的双重性欲(双性特征)发展至性体质成熟 【50】 ,另一个和后天性发展中遭受的诱惑、创伤等个人事件有关。实际上,在地质学模型中,压抑只针对性欲的力量,只有把各种性欲力量和现实因素一起考量,才能弥补压抑理论仍然存在的明显缺陷,弗洛伊德将在1915年三篇后设心理学论文中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最后,回到梦的话题中来吧,至少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不想再多讨论性欲理论、幼儿期因素与梦之间的关系了,他愿意让梦的理论保持不完美。事实上,这一理论(包括基本模型)几乎都是假设,特别是“梦的愿望永远源自潜意识”,是不可能被实证的。但是我们也没必要感到失望,至少,没别的、更好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梦与症状了。
尽管弗洛伊德用了很多篇幅来描述梦与癔症症状的相似,但他并没有更深入探讨梦的形成和在癔症症状的形成中,精神力量所起的作用究竟有何性质上的差异,毕竟当时对两者的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上文两个系统及其活动方式与压抑的讨论,虽然是尝试之一,但弗洛伊德也明确指出,我们的确在梦中发现了各式各样合理不合理的存在,与症状在本质上相同,可梦绝不是一种病理现象,也不必然干扰精神运作的平衡,不会直接造成功能缺陷。的确有那么一些人,一味老调重弹什么“从心理异常活动的材料不适用于正常人”、“从病人梦中得出的结论,不能用于解释正常人”。对此的反驳是:“….神经症症状所运用的机制并不是在精神世界受到异常干扰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早就存在于精神装置正常的结构中….”【51】
两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潜意识和前意识,前者负责提供动机力量,后者审查这些动机,试图抑制和覆盖前者的进程;它们都想成为意识并掌握运动,为此相互争斗,互有胜负,这些都是精神装置的正常结构。相对精神异常,梦为我们理解心理结构提供了一条更易于通行的途径。已有被严格论证过的理论也能说明,梦揭示了在正常人、病人身上共同存在着富有活力的被压抑内容“…..梦本身就是这种被压抑材料的表现方式之一。从理论上讲,任何梦都应如此;从经验上看,大多数梦都是如此····”【52】那些 典型的梦,不论时间、民族和文化差异,都清晰的证明了这点。在日间生活中,被压抑的精神材料遭到更强的目的观念排挤,得不到表达机会,通往内部知觉的回归渠道也被封闭。到了夜晚,这些被压抑的材料通过妥协等手段成功进入意识。弗洛伊德尤为欣赏维吉尔的一段话:“即使我不能撼动上苍,我也要搅动冥府”,他认为是对被压抑冲动的最形象描述。
因此,“….梦是通向理解心灵世界潜意识活动的康庄大道….“【53】。
对于这一伟大的发现,弗洛伊德谦虚的说,这不过是朝向认识“最神奇、最不可思议的精神装置构造”迈出了小小一步。步伐虽小,却也是一个好的开端。精神分析将梦和类似的心理结构都纳入工作范围,我们对心理疾病现在有了新的看法:至少那些“功能性疾病”不意味着精神装置的解体或装置内部发生了新的分裂。拘泥于表层症状是无益的,需要的是动力学的解释——不同系统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时而这种力量得到增强,时而那种力量遭到削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许多力量执行这正常的功能。弗洛伊德推论说,如果精神装置的两个动因或系统:愿望和稽查能够能够合作,要比单一动因生效时更完善,更具功效。对此我完全赞同,只补充一点:如果两者失衡,症状便会乘虚而入。
【49】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9或车文博译本p375
【50】 即达到生理上的性成熟,参见《性学三论》
【51】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61或车文博译本p376
【52】 同上
【5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62或车文博译本p377
为睡眠时观念流向就不受控制,这是片面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没有目的的思想。睡眠的确中断了有意识的、自主的思考与反思——这一事实往往让人不假思虑认定自己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当它们暂时离场后,立即会有先前未意识的,不自主观念占据舞台。后者受制于潜意识系统,目的往往更加单纯,从外表上却很难看出来。
12、梦中的联想关系看起来格外牵强甚至荒谬,这很常见。但这些表面联系在梦中起的作用远不止被看到的那些。它们实际上被迫替代了另外一些更生动、更重要、更受抵制的联结。弗洛伊德愿意承认 “… 梦是荒谬的….为了表现出这种荒谬性,梦动用了极其智慧的手法 ..” 【1】
【1】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47
至于历史上赋予梦的那些功能,弗洛伊德也持开放态度。梦作为心灵的安全阀门,将一切有害的事物都转化为无害,这契合了精神分析的双重满足愿望,我们认为通过做梦来满足(不被允许的)欲望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们也发现了前意识活动的功能和意义,它允许梦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发挥、自行其是。在日间生活中被压抑的原始运作方式,在梦中又卷土重来.它们密切参与了梦的构建,因此梦将心灵带回了胚胎状态,是“一个充满丰富情感和不完善思维的古代世界”( 哈夫洛克.埃里斯 1899)弗洛伊德高度赞同萨利[1893]的观点:“梦会重温我们渐进发展中的早期个性。在睡眠中,恢复我们原来看待事物的方式,回复到很久以前曾支配着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之中。”至于“梦的驱动力量来自被压抑的内容”,这种观点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基本假设了。
梦中想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并不是梦创造了想象,而是受潜意识控制的联想过程占了梦念生成的主要份额。某些情况下在白天也处于活跃状态的潜意识活动,既是梦的诱发动因,也是神经症症状的诱发动因。但这种潜意识活动与“梦的工作”完全不同,后者要受到前意识的多重节制,因此必须区分讨论。在临床实践和理论推(精神装置的假设)后,弗洛伊德进一步确认了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将之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上。
以上论述充分显示了弗洛伊德最惊人的长处:他总是兼容并蓄,擅长在矛盾寻找共性,虽然多借鉴别人的理论和术语,却总能无缝融入自己新创的一整套体系中。关于梦的体系只剔除了少量完全错误的观点,容纳了先前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说法,对一些片面的观点进行了二次诠释,因此较先前诸理论,它形成了一个更高的整体。不过弗洛伊德也坦诚,这个体系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因为它还不能解释梦的另一个突出矛盾,即我们在梦中发现的某些过程,与清醒时的正常心智活动别无二样,另一些却与正常心智活动有天壤之别,例如,显梦中认知的错乱性和不确定性,某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元素,比奇美拉【2】还杂糅的人物形象,看起来像是好几个人物的集锦;进一步分析显示,某些毫不起眼或荒谬的元素,竟然是极为重要元素的替代。正常生活中怎么会出现这些怪异的过程呢?张三只能是张三,不可能即像李四,又像王五。现实中的人物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在梦中它们竟然能相互替换,对张三的情感会完全转移到李四身上,实在匪夷所思。这么来看,梦的确把作为心理正常指标的知、情、意一致破坏了,以至于严厉的批评梦具有一种病态、梦的过程非常原始、功能水平低下,似乎很有道理。
梦频繁的将两种非常不同的过程杂糅在一起。该如何理解这一突出矛盾呢?或者说,能不能用现有理论来加以说明呢?弗洛伊德发现这一点也行不通,所以他只能新加假设。
他首先提醒我们,先前的研究已在梦中发现了许多合乎逻辑和理性的思想,其复杂程度一点不逊色与清醒思维,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思想都起源于正常的心智生活。心智生活所具有的一切特性,也即那些标志着我们的心智属于复杂的、高阶精神活动的东西,都可以在梦念中找到….”【3】。要说梦独立完成这些过程未免夸张,这意味着心灵在睡眠中保持着完全清醒。所以,这些过程完全可能在白天就已经在运行了,但或许未能被意识觉察,梦延续了白天未竟之任务,甚至取得了在清醒时难以达到的成就。弗洛伊德继续评论说:”….最复杂的思想成就,也可以不需要意识的参与…”。
【2】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有着狮子的头,山羊的身躯,蟒蛇的尾巴。
【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48-549
【4】对神经症的分析同样可以在病态信念中,找出一些合乎逻辑的思想,它们和某些梦念一样,唯独在清醒时不能成为意识。这让我们感到奇怪,但考虑到意识的特性,或者说,成为意识的条件,或许能有所帮助。在讲愿望满足时,弗洛伊德提到梦为了突破前意识的限界,从观念回归知觉来吸引意识的“注意”,强度不够的梦在夜间蛰伏,等待逐渐清醒的注意力觉察到自己。“被意识“似乎还需要”注意”的配合,注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功能,与被刺激客体或目标发出的刺激量有关,也会因为不同刺激客体的强度而游移。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跑偏就是由于新的刺激引起了注意—从当前刺激上被动移开。我们常说的集中注意力,就是指主动将注意聚焦在某个刺激客体上,也就是说,沿着某个特定路径分配注意,保持专注,就像敌后活动一样。如果在前进中遇到了某个经不起推敲或批评的观念,就直接放弃掉;也就是说,将注意从此观念上移开——中止注意的投注。可是,这些被瞥了一眼又匆匆放弃的观念并没有就此消亡,似乎还在缺少注意的环境中继续发展了。在对梦和神经症分析过程中,我们不禁好奇,这些观念后来是如何获得力量迫使意识再次注意它们的。弗洛伊德评论说:“….一个思想如果一开始就因被判断为错误或对眼前的理智活动无用而被(有意地)拒绝,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它将在不受意识注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直至睡眠时才被意识到…”。或许我们可以用明暗交替的隐喻来理解这一精神现象,那些值得注意的思想进程得以在阳光下继续发展,而不被接受的进程则遁入暗影,等待重见天日的时机。
这一思想即“前意识的思想”,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但某些观念进程不一定符合主体目前状况或违背社会道德,因而有可能被中止、压制,不再允许成为意识。一个目的性观念出现后,引起了注意,于是”…一定数额的兴奋刺激便被移置到这一观念所选择的不同联想途径上。【5】这种兴奋就是我们所谓的“能量投注“(cathectic energy)。因此,“被忽视”的思维过程没有接受到能量的投注,而“被压抑”或“被贬斥”的思想,就是指投注在其上的能量被撤回了….”【6】这里出现一个疑问,因为弗洛伊德假定所有驱动力量来自潜意识愿望,那么前意识何以拥有力量甚至反过来约束潜意识呢?对此不太严谨的假设是,前意识是通过与现实和语言符号系统的密切联系获得力量的,或许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就有力量,但弗洛伊德没有明确讨论过【7】。后来他把前意识和意识系统(甚至包括一部分潜意识系统)合二为一称为“自我”,说自我是它的“大型能量储槽”【8】,不过后来的研究者还是在两者的从属性上发现了漏洞,此处不做讨论。
有时候,某些目的性观念思想(例如症状)成功引起了意识的注意,并因其效应获得了额外甚至过多关注。分析表明它们曾在很长时间内遭到压抑和拒斥,显然在这一时间段它们无法再获得前意识额外的关注,只能靠自己剩余的能量独占发展。弗洛伊德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或经历了什么变化后,这些思想再度成为了意识。
【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549
【5】这一观念就像枢纽,联系着许多联想路径,它激活的是一系列联想网络。
【6】方厚升译《梦的解析》550
【7】雅克.拉康发展了这一思想
【8】参见《自我与它》
显然,前意识的思想序列有两种命运,即可以自发中止,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对于第一种情况,弗洛伊德假设这类思想序列所具有的能量沿着联想网络扩散,就像火光在暗处辐射一样,暂时的激活了思想网络并持续一定时间(照亮黑暗),但由于缺乏前意识额外的投注,它的能量很快就耗尽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从寻求释放的兴奋变成了静止的投注(即停滞状态)。人们常常会遇到这种尴尬:方才想的事情,转瞬间就完全忘了。有时候脑海中灵光一现,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再也看不到了。(对那些依赖灵感创作的作家、艺术从业者来说尤为痛苦,以至于有些人常常主动服用致幻剂,试图找寻所谓的灵感) 如果出现这种结果,这些注定要被耗尽、注定要被废弃的思想就不能再对梦的生成有贡献了,除非,它们能找到支援,或者找一个新的安身之所。
如果再把精神装置的地质模型拿出来,可以很形象的比喻,这些失去关注的思想,从意识和前意识的交会区域一路下滑,越来接触底。这个过程中它会遇到另一些前意识思想,它们在空间上与潜意识极为接近(即我在上一章所说的潜意识——前意识交会区域),在形态上是极为活跃的潜意识愿望衍生物,失去关注的思想会被它们吸引,从而与其背后的潜意识愿望建立了联系,这些失去关注的思想也可以成为移情对象了。这样,被压抑和拒斥的思想就能继续维持活力了,但它负荷的能量还不足以使之上升进入意识。形象的说,潜意识尽管在前意识内安插了代理人,但仍需蛰伏静待机会。它们还见不得光,只能继续在暗中、在地下积蓄力量。这就是弗洛伊德说的“这些前意识思想被拉进了潜意识”。确切的说,被拉进了潜意识和前意识交会的区域。
在梦或症状形成中还有其他的思想联结形式 ,前意识思想可以先与潜意识愿望结成同盟,再被居于主导的目的性投注拒斥。或者某一潜意识愿望由于某些原因(可能是躯体性的)进入兴奋状态,主动的在前意识中寻找合适的代理人,转移自身的能量【9】。
【9】 参见《性学三论》
不论哪种情况,最终结果都是在前意识——潜意识的间隙产生了一种思维过程,它不从前意识系统获得能量,但能得到潜意识愿望的支援。从它被“拉入潜意识”的那刻起,它就不得不服从潜意识的规则了,经受一系列面目全非的变化后,它再也不能被视为正常的精神过程了,而应被视为病理性过程。
弗洛伊德列举了下列令人费解的转变:
1、单一的观念可以代表由它联结起来的许多联想链条,用一个元素代表许多相互联结的元素,这些元素原先附着的能量都汇聚到一点,形成了一个负荷巨大强度的代表观念。这一过程即是我们熟悉的凝缩作用。梦中那些结合的、不协调的人物形象便经过了凝缩,它尤其令我们惊讶,因为在正常的、有意识的精神生活中找不到相似物。的确,我们能发现另一些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复合物,例如一段滴水不漏的应答,一句承上启下的妙语,它们既可以是整个思想链条的枢纽,也可以是思想的最终结果。但它们既不作用于内在知觉,其重要意义也不是通过醒目的感性形象直接刺激知觉才获得的。总之,它们的知觉特征不会因为精神意义变得更突出。除非,人们在说话时故意提高某些字词的语速和语调,或在书写时刻意把某些字写的与众不同。凝缩作用比上述例子要极端许多:原本复杂有逻辑的精神联系都被简化为直观的内容强度.例如梦中显赫的复合人物,这些人物和主体的、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化约为某一突出的视觉特征——A的头发,B的脸型、C的五官、D的形体、E的衣着、F的动作。相对而言,人物间的差异则被淡化或模糊了,似乎是在保持或增强共同特征,但整体却是不协调的。例如弗洛伊德的伊玛打针之梦,那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三甲胺的分子式,特别醒目”。我不禁想到在游戏中,精英怪物总是比普通怪物更大,装饰或武器也更加精良,而且常常被缺乏特色的大众脸簇拥在正中。这正是对古代雕塑手法的效仿:用大小、位置、精细程度表示人物地位的差异:国王的形象最初要比侍从或手下败将大很多,仿佛侏儒中的巨人;后来的雕塑更加写实,但目的不变:精雕细琢的帝王形象位列正中,傲然挺立,他的敌人则匍匐在脚下。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当代下属向领导鞠躬行礼的现象,可谓是古代表现原则的余音。凝缩作用的方向(或目的)要受到两种因素制约,因为它生成的梦念,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前意识内听觉、字词、文字间的真实关系。但在梦念向知觉的回归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潜意识中视觉回忆的吸引,于是凝缩作用的目标就在于聚集足够的感性强度以突破知觉—意识系统(吸引意识的注意)。这里要澄清一点,即不能把凝缩视为一种摘要,因为根据显梦的内容可以推测多种隐藏梦念,后者又分别衔接更多潜意识元素,涉及到精神装置的不同层次(跨系统),而摘要则是在意识的层次概念化某些含义。
2、由于观念、意象之上的能量可以自由转移,带有妥协色彩的中介物就会形成,后者暂居于潜意识和前意识的交会区域,可以上升到前意识。例如在朵拉第一个梦中,珠宝盒【10】—珠宝—女性性器的一连串联想,珠宝作为“童年对母亲的嫉妒、性交分泌物、自慰的污秽、以及当前的诱惑这些潜意识思想交汇的十字路口”。弗洛伊德说这在正常的观念进程中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正常观念进程要求精确选择适当的元素,拒绝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就是有一说一,就事论事。这里可能有人会反对,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使用双关语、话里套话等方式,好让旁人揣摩。对此我的看法是,这些方式当然不是正常的。有时候说话人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言外之意,或者明白直说是不合法或不道德的,只能用隐喻旁敲侧击。毫无疑问,这样避开令人尴尬、危险或不快的方式,和梦的伪装极为相似。另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口误,前意识内相互矛盾的观念争相要表达出来,就制造出混合妥协式的结构,说话人稍后才意识到说了不该说的东西,只好用不小心来掩饰。
【10】参见《朵拉—癔症病人的分析片段》
3、作为上述现象的结果,可以相互转移能量的观念或意象,就以一种非常松弛的形式联系在一起。把它们串联起来的联想,往往遭到主导思维批评或现实制约,只能通过笑话、俚语或艺术手法来暗示,如常见的同音联想或双关联想,它们用表面联系取代了真正的联系。这可以解释许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病理现象,如在强迫症中,病人因为观念A而悲伤不已,尽管他感觉非常荒谬,却不能自控。分析发现,真正导致病人悲伤的是另一个观念B,如果把B作为病源核心的话,A充其量是附带情境。病人却对其中关系一无所知,尽管观念A是产生强迫的观念,但其强迫力量却来源于B。
4、我们通常用水火不容来形容某些不相容的思想,但在很多场合下,这些思想居然能携手并肩,而不是尖锐排斥,令人深感意外。矛盾似乎被弭除或达成了妥协—某些在台上义正言辞做反腐报告的人,背地里却大肆收受赃款;医生可以大谈吸烟的害处,自己却一根接一根吞云吐雾。某些思想,人们对它绝不容忍,高调反对、严厉打击—却放任它支配行为。在朵拉案例中,朵拉的父亲勾搭上了克劳斯夫人,他们亲密的举止引来许多好事者的流言蜚语。但朵拉却完全视而不见,她非常崇拜K夫人,视为密友,【11】即使女家庭教师很直白的说出父亲的秘密。后来因为某事,朵拉突然打开她的双眼,看清了父亲和克劳斯夫人友谊背后的真相,她于是激烈的攻击父亲背叛家庭,贪图享乐出卖了她,对她不管不顾,奇怪的是,对那个勾引父亲的女人,她却恨不起来。
在任何精神异常现象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原本正常却变异了的思想。我们也发现,以正常方式形成的梦念在梦中经历了多种异变,以上4种最为显著。弗洛伊德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中发现了惊人的共同特征:…这些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其全部重点在于使贯注能量能够自由活动并得以释放,反而其具体内容和意义,倒无关紧要了…”,【12】正常思维有方向有目的,能量受到约束,而异变的思想只求自由释放。两种形式的能量释放可以类比生活常识 :汽油很容易被引燃引发爆炸,但也能经过一系列复杂进程,有序的释放能量推动精密的机械运作。前面我们说过梦的视觉表现力话题,如果梦要完成将思想转化为图像的任务,使某些感性材料更醒目,那可否认为凝缩、妥协形成是专门为知觉回归服务的?弗洛伊德提醒说,还有一类完全观念的梦也具有凝缩和移置的进程,和意象的梦没有区别。
以上事实让弗洛伊德“….不能拒绝这样一种假设,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过程参与了梦的形成,其中一个过程产生与正常思维等价、完全合理的隐藏梦念,另一个过程则以最令人费解、毫无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些梦念…。”【13】这第二个过程就是《梦的解析》第六章讨论的“梦的工作”,严格的来说就是凝缩和移置过程,(象征指的显梦元素和潜意识内容的先验关系,润饰作用发生在前意识和意识之间,严格来说不能算梦的工作)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些机制的起源呢?
梦的研究无法告诉我们答案,但是另一个领域,即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那些匪夷所思的异常思维过程(我们对此知道的仍不多)决定了症状的形成,随着分析愈加深入,一种合乎逻辑的正常思维便愈加清晰可辨。它与意识思维等价,完全可以理解,但起初完全被异常思维感染了。精神分析从看似毫无关联的病态思维中提取出合情合理的思想、重构病人的心智和历史,就如同从荒诞不经的梦中提取隐藏的思想一样。看起来,原本正常的思想遭到了异常的处理,“…. 通过凝缩作用和妥协形成,经由遮掩矛盾冲突的表面联想,逐渐沿着回归作用的通道,这些正常的思想最终转化成为症状….“【14】弗洛伊德再度提醒我们,症状形成其不遵循着和梦的工作同样的道路?两者岂不具有完全等同的特征,以至于把对神经症的研究应用在梦身上,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弗洛伊德从神经症理论中借用了下列命题:”….一个正常的思想,只有当一个源于童年并一直被压抑状态的潜意识愿望移置其上时,才能经受上述异常的精神处理….”【15】也就是我反复提到的,正常思想成为异常思想的代理人。关于构建释梦理论的基本假设,弗洛伊德如是说,“…作为梦的驱动力的愿望永远源于潜意识….”【16】 这一点已经无需多加论证了,不过,对于前文反复提到的“压抑“一词,必须进一步明晰它的原理和运作机制。
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精神装置的假设中去。已知这一装置遵循着基本的反射原理,目的是为了避免兴奋在机体内积累并尽一切努力保护自己免受刺激的影响,当刺激来临时,它试图通过逃避、战斗等运动方式卸除。但这些应对方式只适合外在的刺激,对于内在刺激(欲力)的“需求”却无能为力,除了“满足”这种需求,使刺激降低外再无他途。婴儿的原初满足经验只能通过哭喊唤来养育者的特定行动才能实现,这种原初高峰体验产生了一种难以估量的精神结果——与满足、快乐有关的一连串联想,【17】包括自身的行为和对象的反应,都会被印上最深的烙印。我们已经假设,兴奋刺激的累积,将会被体验为不快和痛苦,【18】精神装置力求回复到初始的平静状态,降低刺激水平,重建满足的快乐的经验;并且说精神装置内部这种起始于痛苦,终止于快乐的兴奋流向就是所谓的“愿望”,断定它是唯一的动力来源;我们认为精神装置内部过程自发的受到痛苦和快乐的调节;“愿望”第一次出现时,企图凭空再现原初满足的高峰体验知觉,“愿望满足”即把能量完全投注在满足记忆上(此时的记忆以不连贯的动作、图像、感觉存在),把满足的记忆完全复制出来,产生幻觉并进一步开启运动之门。(如婴儿吸吮自己手指的行为)弗洛伊德进一步推断说,知觉的最初形式都是幻觉。精神装置面临的困境是,维持幻觉性满足需要不断的消耗能量,而需求仍在呼唤,那虚妄的快乐能够持续多久,能否一直抵消需求高涨引发的痛苦?看起来,除非为幻觉耗尽所有能量,是无法停止需求的,也就是说,主体无法长久维持愉悦感,终将认识到幻觉满足并非真正的满足。【19】
【11】 参见 参见《朵拉—癔症病人的分析片段》
【12】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2或车文博译本p370
【1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3或车文博译本p371
【14】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3或车文博译本p371
【15】同上
【16】同上
【17】即上文描述的精神装置内部的通路
【18】大多数情况下。但在性爱的预备阶段或受虐倾向中,兴奋的累积产生快感。
【19】 无疑 痛苦在此得到了最大化
上述过程可谓精神装置的原始运作方式,由于和生存之道相违背,必须被调整为更符合现实的模式:一种继发性的活动:它依旧要搜索记忆,但绝不允许对记忆投注全部的能量,以阻止记忆变成知觉,过去覆盖现在。曾经是自由的能量被束缚,被引导指向某一具体方向。由需求引起的兴奋现在被导向一条迂回的途径,最终通过自主运动的手段(特定行动,由最初的求助发展到自力更生)改变外部世界,从而抵达了对满足对象的真实知觉。在弗洛伊德那个精神装置示意图中,原始的活动和继发性活动分别代表了两个系统,即潜意识和前意识系统的萌芽,而我们常说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属于充分发展的系统。
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就指出,贸然将记忆判断为知觉,并产生某些反射运动带来的必定是愿望的落空,此时必定导致更大的痛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要有某种“现实的指标”,由它来判断记忆和知觉的差异,避免对记忆投注不必要的能量。弗洛伊德早就发现,潜意识里不存在现实概念,这一现实的指标只能存在于前意识—意识中。让我们假设一种原初的痛苦经验:由于离开母亲子宫造成的刺激积累,引起了婴儿痛苦的感觉和杂乱无章的运动表现。直到某一种运动(例如哭喊唤来了奶水)成功卸除了这些刺激,弭除了痛苦情感。除了满足经验外,精神装置还而建立起不快的感知印象和特定运动的联想关系:如果痛苦再现,重复的运动就会再度展开。我们还知道,幻觉满足可以暂时抵御痛苦,但痛苦犹如高涨的洪水,最终连堤坝都淹没,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它就完全不可遏制了。就原始的精神装置而言,刺激量的累积唤起了愿望,而刺激量的剧变变化引来了情感(痛苦是刺激量的暴增,快乐是刺激量的暴减)。精神装置必须阻止痛苦情感再现,甚至优先于获得快乐。
前意识的萌芽被赋予这一功能,我们已经说过,前意识系统依靠着与意识和语言符号的邻近关系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潜意识系统的行动能力。【20】它一方面要支配各种记忆经验,经验之间持久的联系关系,一方面要朝向外部世界,时刻留意必要的讯息。最后,它必须调动注意力系统警戒任何引发不快的记忆,不允许对后者投注能量。可想而知,由幻觉导致的愿望落空位列排斥名单的榜首,而真实满足的知觉(即那种消除痛苦的特定行动)最受主体青睐,对痛苦的知觉和对真实满足和客体的知觉构成了某种质的指标。如果需求再度出现,记忆中的满足客体也随之被投注,前意识系统必须暂时禁制能量的自由流通,暂停反射行为,直到它收到了足够的现实指标,确保这是真的,与记忆中的满足客体相符【21】。前意识系统就像一台生物计算机,不断的扩充和检索记忆,不停的认知和判断,试图找出最适宜的活动模式。
我们已经知道,潜意识系统负责提供驱动力,前意识系统行使着禁制功能,掌握着运动的钥匙,它们时而合作,时而冲突。前者力求无障碍的满足,后者必须利用自己的能量完成初步探索,直到发现目标符合预期时,才会解除禁制,让运动——释放积累的兴奋发生,改变外部世界。反之,前意识系统会撤回对潜意识愿望的能量贯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弗洛伊德假设,前意识系统需留有必要的能量作用外部世界,不能漫无目的的在所有的记忆和联想路径上做无谓浪费,因此从功效性角度,…这第二系统成功地将大部分能量贯注保持在一种静息状态,只将很少的能量用作移置作用…. 【22】弗洛伊德坦诚并不清楚这类过程的运行机制,但认为必须向物理学求助,来阐述神经元的兴奋过程【23】。以下结论是从临床实践中推演出来的:Ψ系统中,潜意识子系统的目的在于“….让兴奋能量可以自由流动释放,而第二系统通过第一系统【24】(自己)发射的能量贯注,成功抑制了这种能量自由释放,并使其转入静息状态,同时也可能会提升它的能量水平…. 由第二系统支配的兴奋释放机制,与第一系统支配的释放机制完全不同。【25】”
在我看来,这第二系统即前意识系统最初似乎是为了更有效的回避痛苦情感而发展出的。快乐往往和现实无关,但痛苦一开始就与现实关联,因为无助的婴儿必须借助外在客体的帮助。早期生活的诸多痛苦中,由幻觉性愿望落空尤为刻骨铭心。这痛苦的经验—和满足经验对立,主体绝不可能试图在幻觉中复现过去的痛苦知觉,这条路必须被封闭起来,如果类似的痛苦出现,即重复过去回避痛苦的行动。已经有所准备的前意识借助注意力系统,一旦发现有引发痛苦的可能性,立即予以消除“…因为这种兴奋一旦进入知觉,则必然会激起痛苦的感觉。或更精确地说“开始激起…..【26】”这里弗洛伊德指出“…. 记忆和知觉不同,它不具有足够的强度来唤起意识,因而无法从意识中获得新的贯注….“【27】。区分知觉和记忆,对记忆的能量投注加以禁制以防它变成知觉是前意识系统的工作,对痛苦记忆的禁制和回避是首要工作,….. 精神过程能够轻易和频繁的避开对不快经历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精神压抑的原型和最初范例。在成人正常心智生活中,基本上还保持着这种对痛苦的刻意回避……【28】
以上就是弗洛伊德关于“痛苦原则“的初步论述【29】。就潜意识系统而言,它一心只想复现过去的快乐,除了愿望再无其他,它排斥一切和痛苦有关的事物,也无法将这部分经验带入其思维过程。如果维持这种状态的话,前意识系统不能顺利活动了,因为它需要支配积淀在经验中的记忆。假设前意识系统完全不受痛苦原则影响,无视记忆的痛苦——这全然背离了事实。另一种假设是,前意识系统可以利用对痛苦记忆的能量投注,从而阻止更大的痛苦发生。注意力机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像我们发现手受伤,就会格外留意,哪怕维持不舒服的姿势,暂停一些活动,也要防止碰触伤处或二次感染,前意识系统留意并标记某个痛苦记忆的目的,是以反向投注的方式(某些观念/事物是危险的,不可行的…)阻止它复返,由此抑制了痛苦发展的方向。
【25】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5或车文博译本p372,这里两个译本有了很大分歧,即前意识的能量究竟是自己发出的,还是向潜意识借来,这其实也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暧昧不清的地方。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在《精神事件的两个基本原则》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弗洛伊德强调,从痛苦原则和能量消耗最小原则中可以推论一个假设:“…前意识系统的能量投注意味着对(潜意识)兴奋释放的抑制…. 它是全部压抑理论的关键….【30】“对任何观念进程,前意识系统都要仔细审查,只当它成功抑制某个观念释放痛苦后,才会对其投注能量,如果失败,它就投注对立的观念—先前的观念是痛苦的、坏的、危险的、不可行的【31】;按理说,任何可能逃脱抑制作用的观念进程都不可能进入前意识,因为出现就会引发排斥反应。但抑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滞后性,就像在司法领域,总是经历了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后,才有相应的法律出台。往往只有在亲身体验(只有意识才能感知痛苦)过各种痛苦后,才能在前意识中知晓有关痛苦记忆的性质、某些思维过程、目的的不适宜性。这个道理,挨过打的儿童都知道。
弗洛伊德因此发展了《科学心理学大纲》中的思想:有一类仅被潜意识系统认可的原初精神过程,以愿望满足为唯一目的。它会对愿望投注全部的能量,制造出幻觉满足继而导致痛苦的完全发展,这即是精神装置的原过程。反之,那由前意识能量投注支配的,且代表着对前述过程加以修正的继发过程,则称为精神装置的次过程。【32】
将原过程修正为次过程,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原过程追求兴奋的直接释放,以便借助于积累起来的兴奋总量建立(对满足经验的)“知觉同一性”。但继发过程却试图放弃这一意图,代之以对“思想同一性”的追求 … . 【33】 “ 为此,必须放弃最快捷、也是最无用的幻觉满足,代之以认知、判断、延迟、忍耐后的真实满足。 ” … . 思想不过是一条迂回的路径,它从满足经验出发,以此作为唯一目的,透过自己运动经验的方式,达到该记忆的相同投注 … . 【34】 “ 这条路并非坦荡,常常受到原初路径的吸引 “ … .. 它必须考虑到不同观念之间的联络通路,不能被这些观念的强度所迷惑,但很显然,观念的凝缩以及中介结构、妥协结构等,也必然阻碍着同一性的获得。由于这些过程会在不同观念间相互替代,必然会偏离初始观念的通路。所以,继发性的思想必须慎重地回避这类过程 …… 【35】 ” 痛苦原则在很多方面为思想过程提供了现实的指标,除了一点:对痛苦的过度回避会阻碍“思想同一性”的达成,“…. 思想必须逐步把自身从痛苦原则的专断调节中解放出来,并将思想过程中的情感发展控制在最低程度 …” 【36】 如此高度精巧的活动,只能借助意识和注意力机制才能实现。为此,心灵必先体验和了解痛苦,才能慢慢适应和控制痛苦。这一切的前提是对记忆的掌握,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不惜忍受较小的痛苦。这当然很困难,即使各方面都很正常的人, 其思维过程也不免受到痛苦原则的干扰而失控。
借用神话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精神装置亦有功能缺陷,导致在某些时刻,次过程反而屈从于原过程。梦和各种精神异常现象都是例证。这种功能缺陷是历史——即包括人类也包括个体历史的结果。用纯精神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的心智生活中,前意识系统成熟的较慢,很长一段时间都依附于潜意识。而用身心的观点来看,由身体根源发出(伴随着持续的生物需求)的兴奋脉冲—驱力从出生起就强横的介入心智生活。【37】“…这两个因素都起源于童年期,是从婴儿期以来所经历的身心变化的积淀…【38】”
【30】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6或车文博译本p373
【31】参见《精神分析词汇》中关于反贯注的词条
【32】参见《科学心理学大纲》《喑哑与倾听》第九章、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6或车文博译本p373
【33】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7或车文博译本p373以及《精神分析词汇》对知觉同一和思想同一的词条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
【37】参见《欲力及其命运》
【38】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8或车文博译本p374
弗洛伊德指出,“原过程”这一术语让人浮想联翩,不仅仅是从重要性和功效性上考虑,它岂不意味着在时间上更加古老?的确,没有哪个精神装置只存在原过程,这不过是种假设而已,但经验却明白无误的表明,精神装置最初是以非常原始的方式运作,而那些较为成熟的方式是在生命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次过程能抑制和掩盖原过程,但这一优势往往要到壮年时期才能完全确立,在某些个体身上,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39】“…..由于继发过程姗姗来迟,因此,前意识永远也不能对我们的存在本质(由各种潜意识愿望冲动构成)——加以理解和掌控….“。【40】由于原初压抑和固着,理智的光辉永远无法照进潜意识的深邃黑暗中。“….前意识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永远地局限于为源自潜意识的愿望冲动指点一条最合理的道路。对前意识中一切后续的精 神倾向而言,潜意识的愿望都意味着一种必须服从的压力,尽管它们或许可以引开这种压力,将其导向更高阶的目标 … . 【41】 ” 。 我们知道,前意识系统和继发性过程与语言符号系统直接关联,只有到了童年期,才能较为熟练的掌握语言,构建所谓的语义记忆。 ” … .继发过程姗姗来迟的另一个结果是,很大一部分记忆材料不受前意识能量投注的影响 … . “ 【42】 。 它们存在,却无名。
那些源自婴幼儿期的愿望冲动,是无法被毁灭和阻止的,它们就像江河,不能如愿入海,必泛滥千里。这些愿望冲动的满足,常常会与继发性思想中的目标观念相冲突。过去不加掩饰,不问时间地点的欲求受到现实的持续痛击,就算得到了一时满足,所带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就像最初的幻觉满足一样。满足不被允许的愿望,不能再产生快乐情感,而只能产生痛苦了。弗洛伊德指出,正是情感的这种转变构成了压抑的本质。【43】显然这种情感转变也是继发的过程,正如羞耻、罪疚和厌恶感是在后来才出现的一样,这三种因素也构成了压抑的动因。我们知道,只在前意识可以支配记忆的情况下,情感才会受控,对不在它控制范围的潜意识愿望所支配的记忆——依附其上的情感释放是无能无力的,前意识只能尽可能远离这些情感释放。正因为如此,即使潜意识内容将自己的愿望力量移置给了前意识的思想,这些代理人也难以被系统接受。前意识系统拒斥可能引起痛苦的观念,即所谓的移情思想,引发了“继发压抑”。弗洛伊德因此说,大量的童年记忆——实际上,童年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从一开始就被拒绝纳入记忆中,这种情况就是压抑的前提。
我想,凡是那些追求精神卓越的人,都会面临来自肉体欲求的难忍痛苦。不管文明发展到何种地步,只要还留有肉体,人类就一直是动物。人可否将能量投注从前意识的移情思想上一次性、永久撤回?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完全压抑会导致不快的思想?答案自然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源自肉体的欲力——源源不断的供给能量给潜意识愿望,再交给移情思想,于是后者积蓄的兴奋便可能突出重围。器质性原因导致欲力供给无法被切断。举例来说,在俄狄浦斯期,儿童性欲会迎来一次短暂的爆发,直到潜伏期,压抑占据了上风,羞耻、罪疚和厌恶感构建起所谓的堤坝【44】。不过到了青春期,由于性器官的成熟导致了性欲的二次爆发,且青少年已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性行为了,压抑的防线再次受到严峻的考验:虽然失去前意识的支持,但由于获得肉体的支持,潜意识愿望催动它的移情思想大举进军,前意识不得不反过来强化自身对压抑思想的抵抗,加大批判力度,强化所谓的羞耻、罪疚和厌恶感。如果不对那部分思想进行升华,单纯的压抑是不可能的,这里也应考虑体质的原因。有两种压抑失败会导致症状,一是压抑被正面突破,即所谓的精神病,原过程要以生成幻觉形式再现知觉同一性。二是作为潜意识愿望载体的移情思想,通过生成神经症症状,最终以某种妥协方式突破进入前意识。症状不受控制,似乎只能逃避“….由于这些被压抑的思想得到潜意识愿望的强烈投注,同时又被前意识撤回投注,它们便只能从属于原发性精神过程,唯一的目标就是寻求在运动中释放…..”【45】,如:强迫行为。【46】
由此可见,异常心理过程只能发生在被压抑的内容中,实际上也是原过程运作的结果。被前意识所摒弃,却被潜意识收容的思想,从此就只能依靠潜意识提供的能量活动了,可以说它们被原过程感染和同化了。“…这些所谓非理性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正常过程的歪曲及思维逻辑错误,而是从压抑状态中解脱出来的精神装置活动模式….”【47】 代表着心灵早期的运作模式。时过境迁,我们已经认不出它们了,正如对自己童年的遗忘一样。补充说下,从前意识兴奋到运动的能量转移,也遵守与梦、症状同等的模式,那些抓住机会逃脱压抑的思想和反对思想混合在一起表达时,就会出现移置和混淆—通常是口误和过失行为,却往往用马虎大意掩饰本意。当人们试图抑制原过程活动时,就不由自主的增加活动。弗洛伊德评论说,当他致力于了解人类心灵的秘密时,发现高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实际上:“…凡人无法保存秘密,如果紧闭嘴唇,手指就会动个不停。每个毛孔都会泄漏他的秘密…”【48】 在某些需要活跃气氛的场合中,人们会讲一些粗俗的笑话—允许这些原过程思想进入意识,但要在哄堂大笑中释放多余的能量。
【39】 随着步入高龄,原过程似乎又夺回了控制权
【40】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8或车文博译本p374
【41】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8或车文博译本p374
【42】 同上
【43】参见《压抑》、《论潜意识》
【44】参见《性学三论》儿童性欲一节
【45】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9或车文博译本p375
【46】需要说明的是,不受控制的强迫行为在诸多心理异常中都有体现,但是强迫症最为典型。
【47】方厚升译《梦的解析》p559或车文博译本p375
【48】参见《朵拉—癔症病人的分析片段》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