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米蘭昆德拉】笑與忘,輕與重——略談米蘭昆德拉的傳世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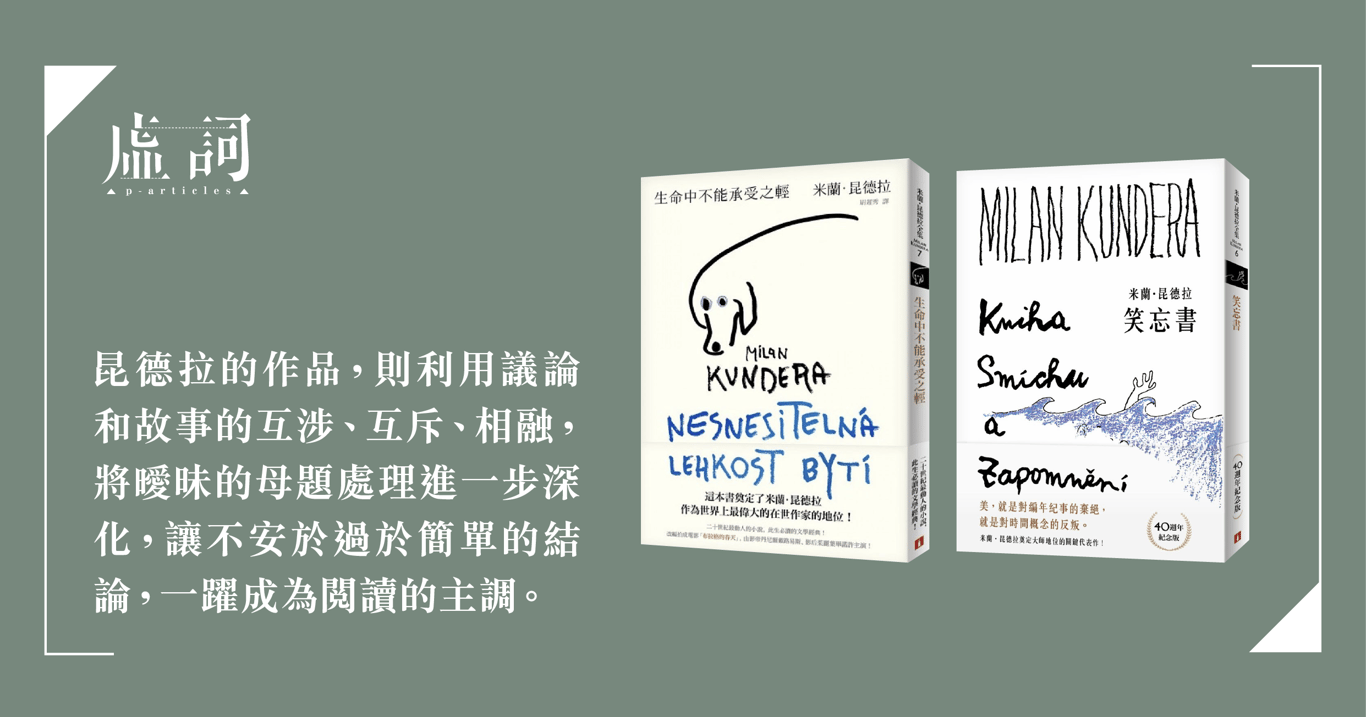
文|朗天
米蘭昆德拉高壽離世,有人唏噓,有人躊躇,而這早經消化的哀慟,大抵可促使我們更全面檢視屬於他的文化遺產。
假如說九十年代的香港文青消費範圍,是由王家衛、王朔、村上春樹、奇斯洛夫斯基、翁巴托艾可(Umberto Eco)和米蘭昆德拉共同畫下的,那麼,昆德拉與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似乎是他加倍的曖昧和複合性,而這一點,是表面閱讀未必即時領會得到的。
這樣說並非指奇斯洛夫斯基等人缺乏深度和複雜的層次(怎麼會呢?艾可啊!),而是昆德拉的複合,恰好是以其表面的膚淺而透闢,因而顯得額外辯證。
是的,原諒我用上「膚淺」這個詞。事實上,在昆德拉開始走俏的年代,我曾聽見一位詩人取笑當時出出入入人手一本《笑忘書》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我們:「原來你們喜歡這樣流行的作家!」並非偶然的是:被這位詩人視為同樣流行以至庸俗的另一作家就叫村上春樹。
當年村上「擊中人心」的時代感性呼應是顯然易見的——後八九、蘇東波、理想主義退潮,人生虛無感泛濫......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福山關於歷史終結的「勝利宣言」,讓大家覺得以後彷彿真的無事可做了,苟活與價值散失,伴隨著離散帶來亦悲亦美,頹廢而自戀的感性氛圍,讓村上筆下的中產自戀男,儼然成為不少讀者的變相代言人。
昆德拉呢?他個人的流亡書寫,對當年尚未志切體會極權統治的香港人本來有好一段距離,然而,面對九七主權移交,香港文化興起的一股離散(diaspora)想像,卻與之產生奇異的呼應關係。
今天我們曉得說,昆德拉創作全盛期所置身的東歐國度,面對二次大戰結束後的鐵幕政治,個人各式政治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布拉格之春」之後的宰制,他在作品提出的兩大主題:笑與忘,常能激發讀者的感性共鳴。
在《笑忘書》,他寫出了今天人們喜歡引用的金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表面上,忘記便是認輸,就是俯首接受謊言。反之,牢牢記著歷史,不容當權者肆意篡改,就是緊握真理以期伸張公義的不二法門。在後八九的歲月,人們瞬間即可對號入座,不難理解。
而笑的主題,則來自他對上一部著作《玩笑》。同樣是置身自由受限的處境,凡事不可暢所欲言,有時不免只能苦笑,但積極一點的,則可將生活的悲劇化為喜劇,用嘲諷和自嘲的方式尋找精神的出路、溝通的方式。
故此,笑與忘,在最表面的對比軸上,並非處於同一邊。笑隱含軟對抗,忘意味某種放棄。這是最易理解,最易進入的昆德拉,而他被判為流行與庸俗,也在於此。
當然,有耐性細心進入昆德拉文本的讀者,很快便發現他的對立書寫從來都是複合的。而為了確保書寫層次的呈現,昆德拉採取了夾敘夾議的手法,換言之,就是在小說敘事的過程中,久不久便加入角色的思考以至作者本人的議論。這些議論,有人認為正正破壞了故事的完整和敘事的暢順,當年便有評論批評這表現了作者時時忍不住「站出來」指點江山的拙劣,又或者,代表了昆德拉對說故事缺乏信心,證明他不是一個好的小說家。
故事與說理,固然屬於兩個層次,把明顯不同的層面置入角色的遭遇、他們之間的衝突、處境的變化發展等,與其說會帶來抽離的效果,鼓吹讀者進行相關主題的思考,時刻意識到敘事的意圖和局限,不如說是一種精心布置的風格。用得好的話,便宛如將邏各斯(logos)和迷思(myth)兩大人類文明的表達式,交叉運用,相互配合,宛如《莊子》所謂的兩行之道。而昆德拉在其創作黃金期(六十至八十年代),庶幾近之。
正是在這種表達風格和策略下,昆德拉巧妙地把主題透過表面最顯淺的對立,引入複雜和曖昧的思情。回到笑與忘這表面對立的設置,笑所代表的反抗有時會轉入過於輕鬆的劣義,開玩笑的消極抵抗有時成為反動的藉口,淪為笑柄;另一方面,遺忘有時則是必要的心靈保健法,《無知》裡昆德拉便充分闡述此義——假如人能記得生命中所有的細節,精神崩潰便是他唯一可迎接的命運。遺忘不止作為心理保護機制令我們免受創傷的負面傷害,它有時甚至是協助記憶,以至乾脆成為記憶的一種形式:通過忘記某事以牢記另一事,是無數人的人生常態。
昆德拉在其最引人傳誦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寫出了另一金句:「人們一思考,上帝便發笑。」但究竟此句是正面抑或反面的呢?昆德拉沒有直接作出回答。第一層詮釋:上帝對人思考發出會心微笑,祂希望人去思考,反過來說,人的思考是上帝所祝福和恩賜的。第二層詮釋(可能更符合傳統神學):每每損害信仰純粹性的理性思考,容易導致思考的人變得自以為是,自我尊大,這樣一來,在上帝眼中,不免可笑復可憐。
不錯,在昆德拉筆下,「笑」的辯證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雙重母題——靈與慾/重與輕更如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雙男女主角——湯瑪斯、杜麗莎、莎翩娜、法蘭克,雙王雙后的錯綜關係,構成了昆德拉最富戲劇性的小說推演,它後來獲荷里活青睞改編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1988),並非無因。
表面上,湯瑪斯代表慾,杜麗莎代表靈;莎翩娜代表輕,杜麗莎代表重。湯瑪斯周旋在兩重對立拉張中,最終選擇了靈和重。然而,昆德拉並沒有通過角色和故事而去終止思考和判斷。他自己本人就是走莎翩娜一路的——離開了母土故鄉,即使在蘇東波後,也沒有如哈維爾那樣,「回國貢獻」。他的選擇一方面是激進的,一方面則實際而世俗——去國四十年,甚至放棄母語,改用法文寫作,間接導致晚年難產及寫作水平下降。
世情並非非黑即白。黑與白之間,固然存在不同灰度的灰色地帶,更何況黑中往往有白,白中每每有黑?掩映間揭出來,黑與白背後原來還有藍與黃!細心的讀者閱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難發現它那雙重母題到最後其實可歸結到更基本的去與留對立。敘事上我們也可反過來說:情節上各位主角的去與留,引入我們思考(他們面對的)靈與慾/輕與重,於是今天的香港讀者又可找到他們代入共感的位置。
同樣的思考和問號可扣連到去和留的對立。不能承受的通常是重,昆德拉告訴我們,輕盈有時也是不能接受的。去國是追求自由,自由似乎是輕的;「布拉格之春」後,留在捷克要面對許多困苦和沉重的生活。可是,價值每每都是沉重的。留其實也出於自由選擇,而且還是不輕易的選擇,那麼,自由究竟是輕還是重?湯瑪斯最終關於去或留的決定,是對抑或錯?我們真的可以憑一兩句說話、一兩個故事,以至一兩批書寫,就能下出相關結論嗎?
文學之為文學,曖昧是關鍵。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便詳細討論了曖昧作為小說創作必要條件這課題。當曖昧被放入夾敘夾議的昆德拉風格書寫,它便有了更複合的辯證。一般的創作是作家不去正面肯定,交給讀者自己感受、進入敘事世界,尋尋覓覓。昆德拉的作品,則利用議論和故事的互涉、互斥、相融,將曖昧的母題處理進一步深化,讓不安於過於簡單的結論,一躍成為閱讀的主調。難怪在第一波後現代文化(1970-2000)中,昆德拉素被列為後設書寫的闖將之一了。
辯證本指理性對話模式,是中性的,後來它轉為劣義,意指超出了應用範圍而陷入困境。哲學上,黑格爾將之挽回勝義,文學上我會視昆德拉為同路功臣。
昆德拉走了,可他一早活在我們的血液裡。也許很多年之後,我們一想起昆德拉,上帝仍會發笑吧。
朗天
作家、文化評論及策劃,兼職執教大學,近作有《反復:易經新寫》。虛詞・無形網站
虛詞・無形Facebook
虛詞・無形YouTube
虛詞・無形Patreon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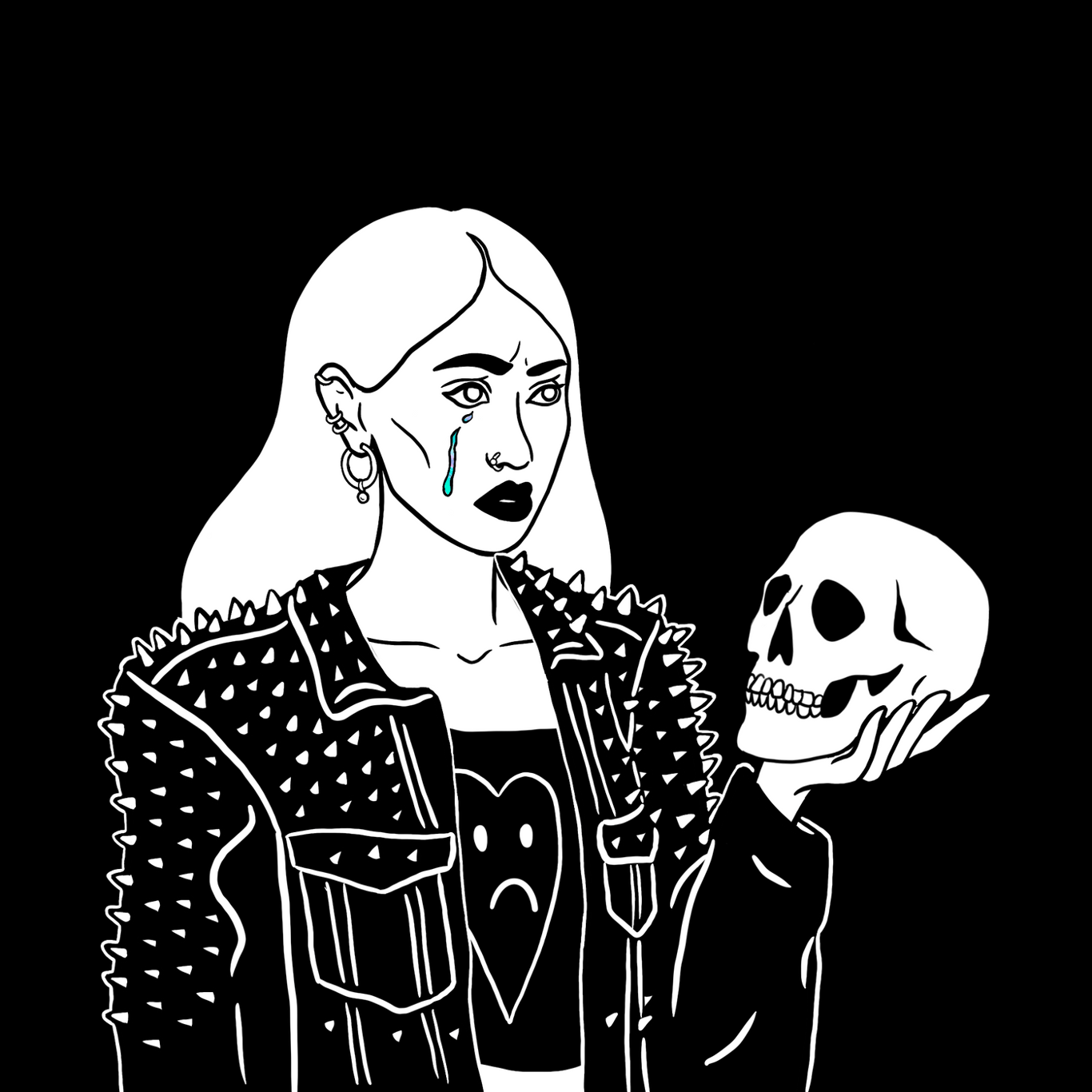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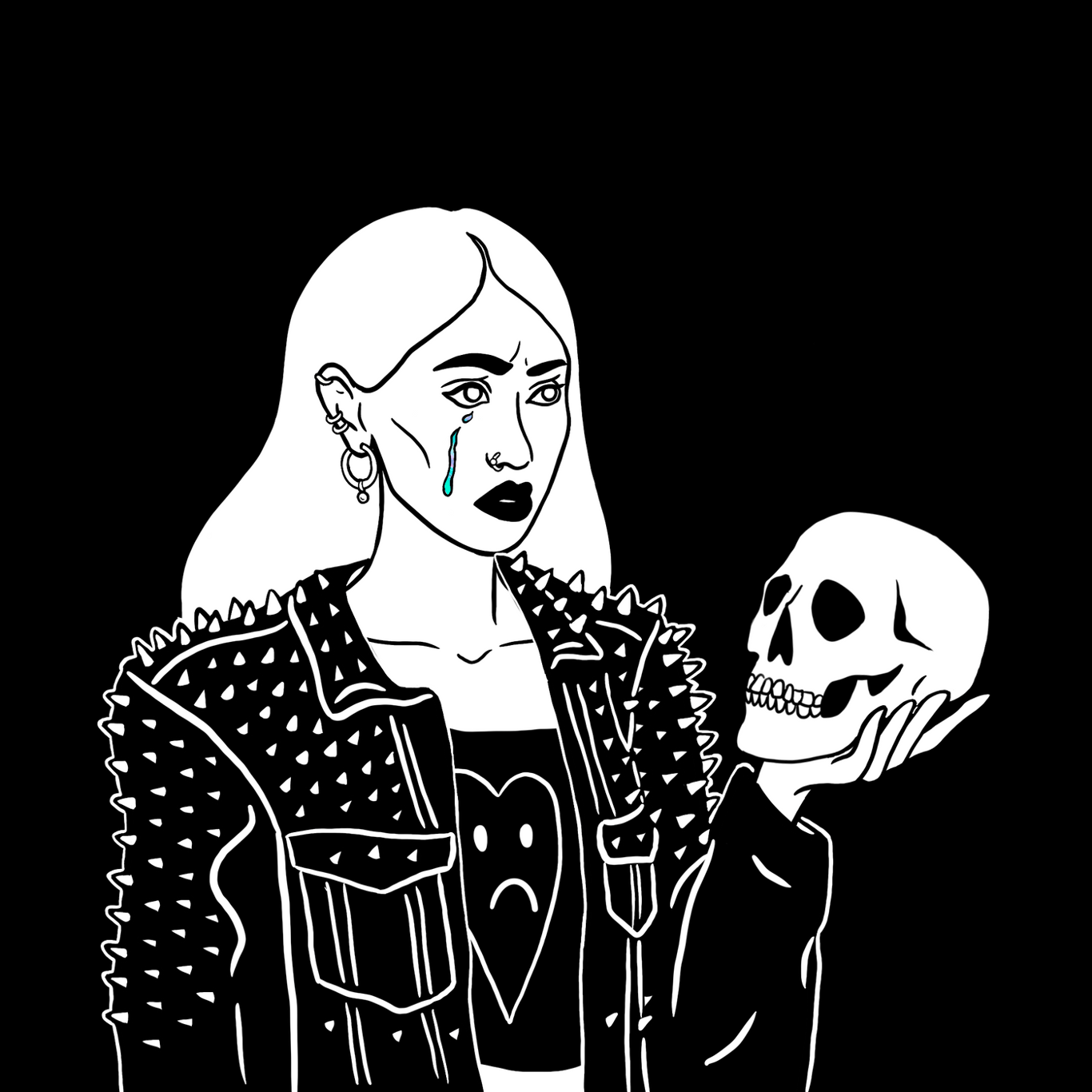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