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們都竭盡全力,嘗試在當下平靜地紀錄和敘事
該從哪裡開始寫呢。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邀請了幾位住在附近的朋友,來家裡吃「無法出門四天」前的最後一頓火鍋。雖然內心的第六感一直在聒噪,但我仍在送別朋友時,跟他們說:「四天後見。」
今天是第二十四天。
四月二日到四月三日,上海各區開始向民眾發放第一批物資。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覺察到,我們可能無法在原定的日子走出門。
四月五日,原定的「出門日」,取而代之的是全範圍的封城。人們面對已經所剩無幾的「四日糧」,開始從玩笑式的調侃轉為恐慌。那一天晚上,我在微信發了一條朋友圈:「沒聽說過哪個國家的人民是以這種方式吃不上飯的。」
封城前的三月三十日,跟國外友人笑談東西方在“囤物資”上的差異性,眾所周知西方每當打仗打颱風,商店最快被清空的永遠是紙巾,我笑說無法理解,通貨膨脹也輪不到一卷廁紙吧。當時友人還說,對啊,四天用得著那麼驚慌囤食物嗎?我還有個朋友,買了四月十二日的機票,打算一解封就回德國,他已經把家當賣得差不多了。
昨天我突然想起他口中這位家當所剩無幾的德國朋友,於是問起,他說,毫無疑問他沒坐上那趟飛機,現在還被鎖在家裡。
四月七日,我接到了身在北京,在某頭部外媒工作的朋友電話,詢問了我一些有關上海食品物資短缺的情況,並問我是否能做視頻訪問,親身說說自己的狀況。我接受了邀請並表示願意出鏡,但卻被告知我的樣本故事「不夠嚴重」,因為聽上去我家裡的食物挺多的,他們希望能找到已經嚴重食物短缺的故事。我表示理解。
四月八日,第一篇「求救」相關的文章被大範圍轉發,我身邊在上海以外城市的朋友開始慢慢注意到上海發生的事。
接下來,上海幾乎每天一變,這種變,包括防疫政策、交通運輸,還有每個人的心理狀態,每天都在發生荒唐至極的事情,荒唐到無法用任何課本上學過的知識和邏輯去解釋。最無法理解的,是這些事情,真真實實發生在上海這個超級城市,這個被人捧在手心,小心翼翼呵護了一百多年的城市。我第一次感覺到「平行宇宙」的存在。
身邊有朋友確證陽性後被警察半夜撬門帶走,有朋友因為轉發天平路白旗照凌晨兩點接到警察電話差點被請去喝茶,有朋友1歲多的孩子發燒兩天找不到醫院接收...... 面對這些事情,我一個普通人,從有心無力漸漸無心無力,所有價值體系在一瞬間被擊潰,叫我怎麼甘心呢?
開始的幾天,接收到的信息太多,我甚至無法用語言把自己的感受具象地描述出來,直到有一位朋友形容了一個大概:「我沒有感覺到苦難,苦難可能是高貴的,我是感覺很屈辱。」
是的,我收到的救濟糧裡有一隻完整的冰鮮雞,當我意識到烹煮它之前,需要把它的頭砍下來,而我又是一個半素食者時,這種屈辱佔據了我全部的情緒。對上一次感受到屈辱,是我八年前在金鐘夏慤道,跟幾十萬人站在街頭,面對民主的鮮活模樣,生在對岸的我感到無比屈辱。
這幾天不斷收到家人和世界各地朋友的問候,有關心我生活狀況的,也有向我求證網絡各種傳聞真實性的。在不能出門的日子裡,我的心理狀態一直都比較平穩,要感激人生前二十九年經歷過的那些大風大浪,起碼能提前經受苦難此時看來是幸運的。在二月中由於滑雪把腿摔骨折,所以其實我早已處於一個不能自由出門的狀態,也因此,我早早就在家裡做好食糧的儲備,也幸好,我母親二月底來上海照顧我時,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把我行動不便的消息傳遍了整個社區和菜市場,並拿到了菜攤和水果攤攤主的聯繫方式,在封控前就遠程操作我家的食物補給。在這場悲劇前,我絕對是屬於非常幸運的那一類人,冰箱一直有足夠的食物,上週水果攤老闆恢復營業後,也直接把新鮮水果送到我家樓下,使我免去了加入水果團購的步驟。
這段時間,在我們住宅樓的樓群裡,我擔任起了團長,作為老好人INFJ,還兼顧三位外籍鄰居的私人翻譯,還時不時帶帶群裡的風向:曾因為確認陽性被帶到方艙的鄰居痊癒後回樓,某位鄰居在群裡質問居委會,為什麼X0X號房有人回來了?在ta發出下一句話前,我說了一句:「歡迎回家。」接著有第一、第二位鄰居,開始加入我,紛紛對這位出艙的鄰居說:「歡迎回家。」那一刻,我覺得我做了一件特別對的事。
正因為有這些人,當我被在外媒工作的那位朋友問到「解封後你會離開上海嗎?」,我說:「我會努力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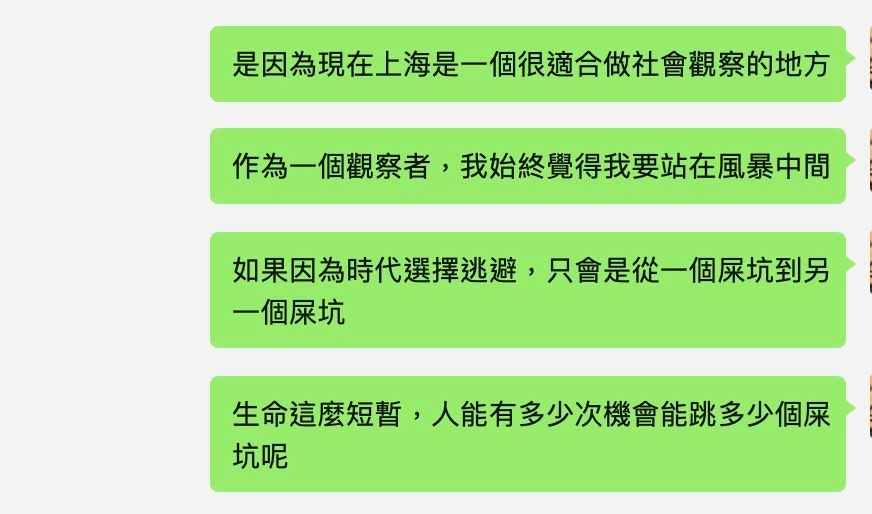
時代的悲傷從來都不是個人的錯,我怎麼能在每個人都在竭力維持生活常態的當下,去責怪這座城市呢?
全城封控下的生活早已徹底碎片化,我能做的,就是去紀錄當下。這個時候,我們不再需要宏大的敘事,記住每個微小的人,記住這些惡與善,記住這些苦難,記住這些不甘心,記住這些光亮。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