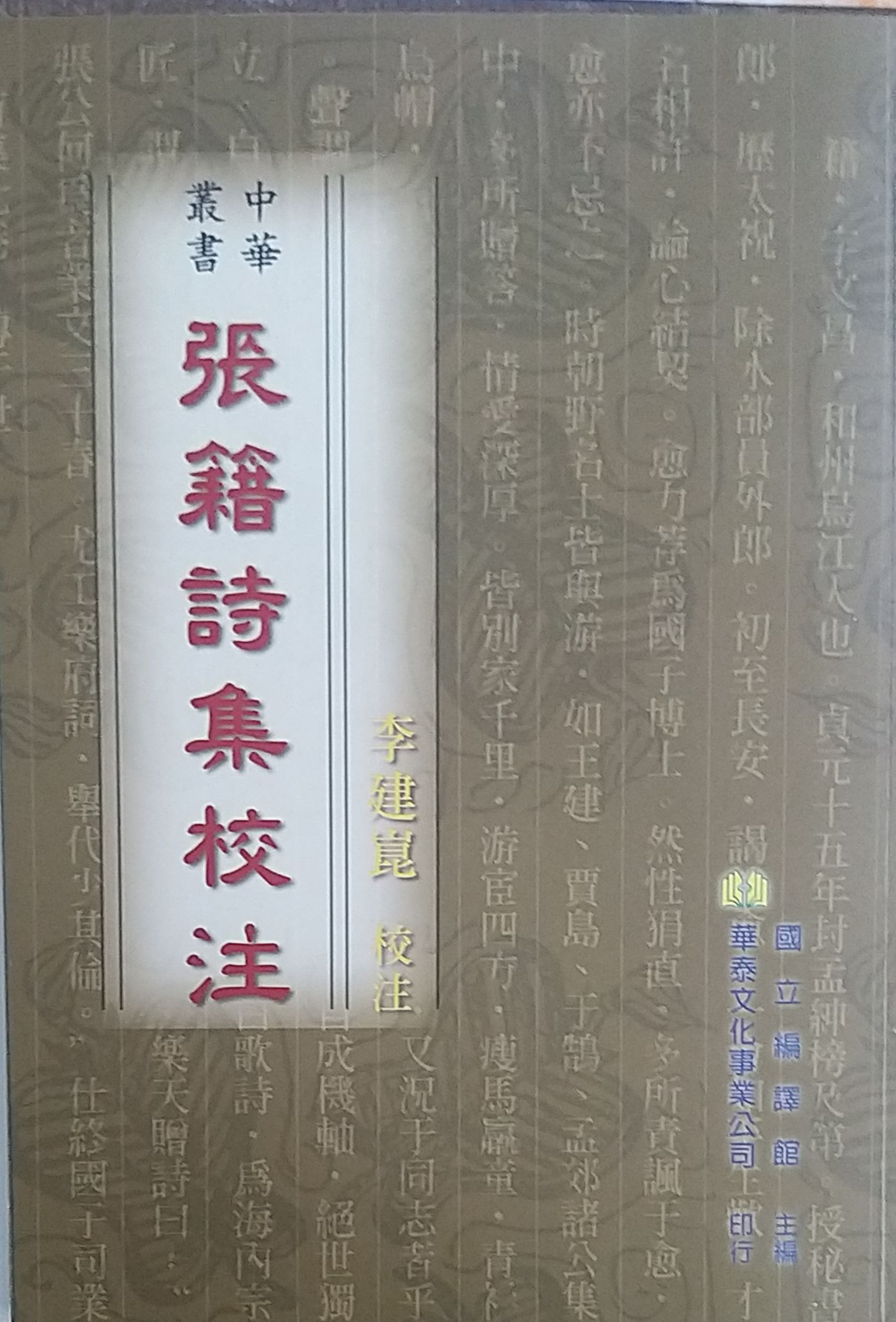悅讀張籍〈節婦吟〉
在中唐詩人當中,張籍(西元766-830年)算是重要詩人,一生歷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這幾個短命朝廷;他曾擔任太常寺太祝、國子監廣文館博士、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國子監司業,後世稱之為「張水部」或「張司業」。
張籍的詩歌創作現存473首,涵蓋各種詩歌體式,然而前賢似乎對其樂府特別重視,或許因為元和時期「歌行學流蕩於張籍」,而將張籍納入「元和體詩」;或因與王建齊名,並稱為「張王」;或者僅就五律的創作成就,譽之為「晚唐五律兩派」代表人物。若從詩人交往關係來看,張籍是韓愈的高弟,屬於「韓孟文人集團」的成員;但是就創作趨向而言,張籍實為元稹、白居易一派「新樂府詩人」的前驅者。
張籍詩流傳過程中最有趣的現象,便是存在大量資料討論〈節婦吟〉這首詩。當代人也許未必認識張籍,卻多少聽聞過「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兩句名言;尤其在小說家瓊瑤細膩的鼓蕩下,創造出「還珠格格」這位戲劇人物,使得〈節婦吟〉成為張籍流傳後世的名篇。這首詩的全文如下: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一作恨)不相逢未嫁時。
依據台灣大學中文系羅聯添教授的考證,這首詩大致作於德宗貞元21年(西元805年),而在《全唐詩》卷382題目下也有一句小注:「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經過大陸學者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考證認為︰「李師道當為李師古之訛。」
這首詩自從南宋.洪邁《容齋隨筆》提及此詩的創作本事以來,就有不少論者發表意見,至明、清兩朝已存在不下20種詩論著作論及〈節婦吟〉。當代讀者在閱讀的過程多半不去理會創作背景,大多僅就文字脈絡欣賞此詩。雖然如此,本詩僅就文字層面所蘊含的情愫來看,一個有夫之婦當機立斷,了結一段可能「陷入危險」的情緣,就足以感動讀者。但歷來有關〈節婦吟〉的討論,還至少開出三個有趣的議題:
一、對於「節婦失節」的倫理焦慮
從現今流傳的〈節婦吟〉版本來看,末句出現兩種異文。明.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所見為「恨不相逢」;至於清.葉矯然所見版本,則是作「何不相逢」。葉氏在其《龍性堂詩話》初集說道:
張文昌樂府擅場,然有不滿者。如〈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又云:「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此婦人口中如此,雖未嫁,嫁過畢矣。或云文昌卻鄆帥李師古之聘,有托云然。但勝理之詞,不可訓也。
王世貞、葉矯然所見版本雖然不同,卻都相當程度影響論者對「節婦」之觀感。其實南宋.劉辰翁的批點早已說過:「好自好,但亦不宜繫。」明.唐汝詢《唐詩解》卷十八甚至說:「夫女以珠誘而動心,士以幣徵而折節,司業之識淺矣哉!」清.葉矯然所謂「勝理之詞,不可訓也」都在言下透露出一種屬於倫理層面的深沈「焦慮感」。
由此焦慮感出發,〈節婦吟〉中的婦人,算不算是「節婦」?詩中之節婦應不應繫上明珠?皆曾引發清人熱烈探討。其中持反對立場者固然甚多,然而並非全為聲討之見,例如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一與卷三即曾提到「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二句,謂「如無此一折,即淺直無情」、「朱子譏之,是講道理,非說詩也。」這種意見十分有趣,也很值得關注。
二、對於「比體」、「寓託」的後續探索
清.賀貽孫在《詩筏》云:「此乃寄東平李司空作也。籍已在他鎮幕府,鄆帥又以書幣聘之,故寄此詩。通篇俱是比體,繫以明國士之感,辭以表從一之志,兩無所負。」這一段資料明白指出〈節婦吟〉「通篇俱是比體」,所以當然不宜望文生義。
其實明、清論者大都知悉〈節婦吟〉的寫作目的是為了婉拒李師古之徵辟,根本與節婦之懸崖勒馬、斬斷情絲無關,卻仍無法擺脫「倫理的解析角度」。例比如清.賀貽孫在《詩筏》引用黃白山的一段評語,就很有代表性:
按李司空即李師道(按:應作李師古),乃河北三叛鎮之一。張籍自負儒者之流,豈宜失身於叛臣?何論曾受他鎮之聘與否耶!張雖卻而不赴,然此詩詞意未免周旋太過,不止如須溪所譏。安有以明珠贈有夫之婦,而猶謂其『用心如日月』者?且推『相逢未嫁』之語,脫未受他人聘,即當赴李帥之召,恐昌黎〈送董卲南〉又當移而贈文昌矣。
黃白山認為:張籍雖已婉拒,但因張籍與李師古「周旋太過」以致「不只如須溪所譏」。他認為贈送明珠給已婚之婦已經不當,稱許他「用心如日月」、而且若非已婚一定受聘赴召,更是不可思議。言下失節的不是受贈明珠的婦人,而是張籍了。最後他認為:這種事情果真發生,則韓愈委婉勸戒董卲南不宜投奔河北叛鎮之〈送董卲南序〉,應該改贈張籍。可見黃白山是明知此詩為「比體」,仍對張籍的作法不予肯定。
清.沈德潛在《重訂唐詩別裁集》,明白反對選錄〈節婦吟〉,因為他認為:「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卷八)但並非所有清代詩評家都對此詩不滿,仍有王堯衢、曹錫彤、史承豫、黃周星、宋宗元等詩評家,對〈節婦吟〉一詩寓託之旨,十分讚賞。例如清.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就曾說道:
「雙明珠」,厚贈也,「君知妾有夫」而故贈之,非義處在「知」字。「纏綿」思亂貌。「襦」,短衣,非正服也。且不拒絕繫在羅襦,仰以志感,亦情之能動人也。「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此以大義曉之。高樓連帝苑而起,見非小家。「良人執戟」,侍衛明光殿裏,現是職官。「知君用心如日月」,豈不知婦人從一而終﹖「事夫」與「同生死」,乃有此非義之贈乎﹗「恨不相逢未嫁時」乃解雙明珠擲還,而酬以雙淚,蓋妾自守義而不以情屈,君雖用情當以義制,明珠之贈,君意良厚矣,然不相逢於未嫁之時,豈宜受珠﹖妾恨君逢妾之晚也。此張籍卻李師古聘托言如此。
王堯衢從「非義之贈」及「守義之行」來衡斷此詩,對於張籍托言婉拒李師古之徵辟有一段詳細分析。王堯衢認為贈者明知此婦有夫,卻仍以明珠相贈,此為「非義之贈」。至於節婦繫珠之舉,則是內心撩亂而對贈者之感激;然而一想起丈夫用心有如明月,因而對贈者曉以大義,並垂淚歸還明珠。王堯衢認為:此婦「自守節義」不因情屈,雖知贈珠者動情,仍「以義相制」,既非未嫁之時,自不宜受贈明珠。至於清.曹錫彤《唐詩析類集訓》卷七則云:
李師古自為節度使治東平郡,憲宗加檢校司空。張籍在他家幕府見聘,弗從,乃寄詩,而師道尋見夷滅。良人,夫稱。執戟,備宿衛也。明光,宮名。《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言己無私心以正師道之心,蓋以申明首句妾有夫之意。「還君」二句,此以卻聘意結,蓋以申言次韻感繫之意也。
曹錫彤從此婦無「私心」說起,認為此婦以「無私心」導正李師古之「私心」這也是很獨特的看法。此婦以有夫之身分必須「還珠卻聘」,雖曾繫珠於紅羅襦,卻有其「垂淚還珠」之必要性。也許清.史承豫《唐賢小三昧集》所云:「婉而直,得風人寫托之旨。」正可與曹錫彤之論見相發明。
三、關於「繫」與「不繫」之借題發揮
由於此婦之所以受到譏評,關鍵在曾收受贈明珠,並繫在羅襦之上。此婦應「繫」或不應「繫」,理當在受贈之初,即有明快決斷。倘若該斷而不能斷,即有瑕疵。清.黃周星《唐詩快》對此發表令人莞爾之論見:
雙珠繫而復還,不難於繫,而難於還。繫者知己之感,還者從一之義。此詩為文昌卻聘之作,乃假托節婦言之。徒令千載之下,增才人無限悲感。
黃周星認為雙珠到手不難於繫,而難在「繫而復還」,而且牽引到「徒令千載之下,增才人無限悲感」,這簡直是借題發揮之見,實在非常有趣!至於清.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也對時人摘取「繫」字,作為譴責點,不能苟同。他說:
他鎮幕府鄆帥李師道(按:應作李師古)以書幣聘之故,作是詩以卻。有謂其詞義失節婦之旨者,竊不以為然。婦未嫁時,則人盡夫耳,垂淚還珠,用心亦正如日月,至或又摘其『繫』字為訾,尤拘腐之論,若然,則柳下坐懷當何說以解?
宋宗元認為此婦如在未嫁之時,任何人盡可為其夫婿;然而既為有夫之婦,則其還珠之舉,用心亦如明月,頗堪稱許,無可指摘。所以如論者獨摘「繫」字,則屬「拘腐之論」。此種意見當然值得欣賞,只可惜宋宗元並未針對節婦之「主體自由」,有所稱揚,仍以「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傳統角度加以批駁,使其說亦不能免於「拘腐」。
綜觀明清以來論詩的方法更為精細,所見的視域更為深入。前代評論張籍的議題,都被反覆參研;其論述的規模、論析方式更為圓熟。他們對於〈節婦吟〉的批評,雖非完全對準文學角度,卻展開豐富的詮釋議題。當代學界一些專文論及〈節婦吟〉,關涉到的詮釋議題涵蓋「節婦」、「代言」、「比興」、「文本誤讀與歧義」、「倫理焦慮」等等,其實都是承繼明清論者的討論而來。一首詩能長期受到詩評家的關注,而且引發不同面向的討論,本身便是奇觀,也是張籍詩歌自有獨到成就的明證。(完)
延伸閱讀
張籍詩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