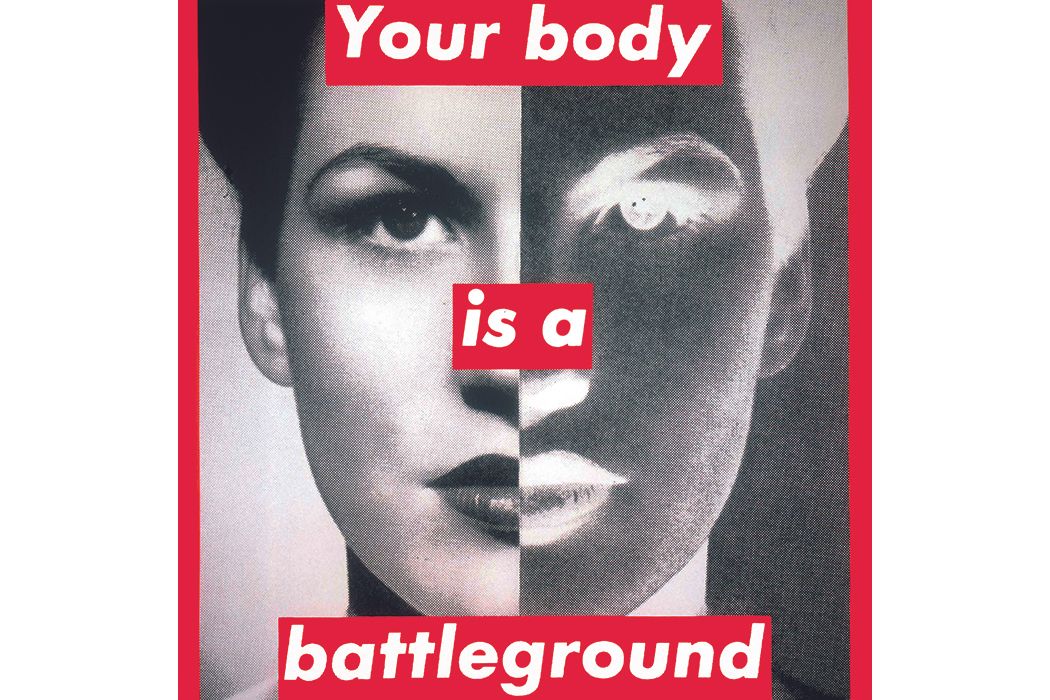吕频:女权运动如何才能存续——再论梁钰入党问题
作者:吕频
来自:女权之声
米米亚娜加注:本文在微信上被屏蔽
几天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梁钰带流量高调入党可能给女权社群带来危害。
就文章所得到的评论,首先想说的是,应坚持将争论放在女权社群内部。尽管社群不是封闭的,但认同女权主义的是与否(尽管认同本身是差异性的)仍然是重大区别。女权社群不是乌托邦,但基于男权眼光的窥视与骚扰,以及对女权争议的恶意政治性利用,会进一步让争论无解并恶化我们的生存环境。
以及,讨论是不自由和不对等的。非常悲哀。然而与不自由的言论环境搏斗,抵住它,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尽量维持讨论的公共性,是女权运动的一部分。现在想搁置对梁钰个人品行的关注,评论一个相关的,更广泛的问题,即在今天这么逼仄的政治条件下,如何理解女权运动的合法性的设置。如果说这是一个关乎应然的问题,那么,应然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如果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那么策略何在?
事实层面发生的是,女权运动从来都不是政治反对,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抗争,是以女权主义的认知将个体女性的哀怨凝聚成集体的愤怒而生成的运动力,它的目的是要解决女性在各个生命周期中所遭遇的歧视和暴力,而不是推翻政权和更换政治制度。——当然,女权主义本身主张对“政治”和“制度”的广义性理解,这和这里的狭义用词不一样。其实,这才是女权运动能一穷二白,却不断上升,主要依靠一群在父权制度下没有话语权的年轻女性,就制造出种种波澜,正在让主流社会敬而畏的关键原因。这个原因并不是什么自我设限,而在于它站在了普通人都能/敢于加入进来的立足点上,并且通过逐步扩大这个立足点,不断去连接更多人,来实现它的影响目标。如果这是一个政治反对的运动,那么它早已被失踪和不为人所知,以及,它也不可能再这么细腻地去共鸣女性的日常经验,女性大众接触不到她,也不会认同它。
我的意思是,女权主义的非政治化,迄今为止确实让它在相当程度上保有了中间地带的安全区——尽管饱受恐吓和威胁,这不应该被理解为对政治环境的实用性顺应,相反却是这个运动应该被承认的价值意义所在。我们的运动在回应人的疾苦,同时也在促进社会内在的深刻的变化,以及人的教育和转变,这好像是只有女权主义才能做的独特工作。在策略层面,这个运权运动也从来都不是“激进”的,或者说,也许一些议题的设想是“激进”的,也许一些倡议的手法是“激进的——这已经几成明日黄花式的记忆—— 但运动的目标还是尽快触动体制,将女性的诉求纳入。换一种说法:女权运动,既不是传统政治话语中的改良,也不是革命。它的诉求,它的运动轨迹和它的成就,都是在这种二元论之外。
相应地,被女权运动的发展所激活的反女权运动,其有组织的策略之一,就是不断对女权运动施以政治污名,试图将女权主义拉出这个社会抗争的中间地带,取消其合法性,让打压师出有名。因此我们看到那么多男权账号带节奏,将女权运动谥为“境外反动势力”、“扰乱社会秩序”等等。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辩论所需,也不反映事实,而是为了调动铁拳,让男权对女权胜之不武。女权男权之争,真正的困难不在于我们不会说、不会斗,而在于男权永远是依傍一个权力体制的,将他们看成是一群上网屌丝男的乌合之众是过于天真。
然而,这些男权分子已经一定程度上用他们的政治污名术绑架了女权主义者。再次,这不是因为他们操控高明,而是因为政治污名的施咒让人不敢反抗。女权主义者不乏勇气通过集体的自承其污来反转和自我赋权,比如他们说我们是婊子,我们就回以“婊子光荣”!可是,几乎没有人敢喊“我就是境外势力”或者“我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尽管女权主义就是全球性的思想,许多女权前辈也就是以扰乱来促进社会变革。从这一点来说,当下所谓“极端女权”其实不“极端”,更不好对标曾经光荣的英国女性参政论者之类。这是一场多么不公正的较量,我们的对手划定了边界和规则,并且很可怕地,将恐惧和自我审查渗透到我们心中。
和恐惧与自我审查的搏斗,不仅是被迫应对,相反,已经成为运动的主要使命。比如自2018年以来的米兔,在很少很少大众媒体报道的情况下,就是靠许多许多女权者的人肉接力,拼体力,拼时间,无数次被删除后又有更多人重新发布,才突破了一次次封锁,让米兔壮大到今天,解决了一些个案,通过尖锐的公共辩论震荡了社会观念,也推进了一些政策性的进步。这样的正在发生的历史显示,女权运动是在社会抗争的立足点上,来争取纳入更多女性和男性的中间地带,而因此扩展它的合法性。我认为必须要维护乃至扩展基于这样的中间地带的合法性,才有运动的未来可言。
这要触及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对父权国家与妇女之间紧张关系的认知,具体来说,是评估:就妇女的资源平等分配和权利保障,在目前的条件下,能通过什么手段才能促使国家改正和让步。看过去,女权运动兴起,是一场不断的娜拉出走:因为国家无限延宕回应女性的要求,而女权者不想再等待;看当下,女权运动的自我激励,则是因为体制外的集体方案——发声、辩论、震荡,艰难中仍有效应甚至进入螺旋上升。今年“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主动发表与女性权利相关的政见,和此前诸多品牌终止与B站合作,和谭维维唱出‘’极端女权“的歌曲……等等,都是这种效应已经开始向主流社会的信号。
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并没有到来,但是从社会的变化来看,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坚持下去,不妥协,国家也许会有所让步,尤其是考虑到一些宏观因素,例如人口危机;国家也许不会让步,然而坚持下去不妥协,撑住女权的存续空间,让更多人进来,做出不一样的生活选择,也是善莫大焉。然而这临界点前的时刻,一定同时也是特别焦虑的时刻不是吗?未来不知什么时候会到来,而当下的坚持却已经很累。其实,更焦虑的是男权者,所以才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正面刚,还想分裂瓦解这个运动。收编全部女权运动不可能,收编一部分,解散继续抵住的力量,也可以缓解他们的危机。
在这个阶段,要卸女权之力,最佳方案就是部分招安,这比满足女性群体的权利诉求要便宜太多。而有少数人通过招安给自己洗白政治污名的结果,必然是大多数人的污名不可解脱。再用“婊子”的比喻,有人“从良”必定恶化其他“婊子”的境遇,而所有人都“从良”且不说名额有限不可能,也不过意味着父权秩序的重新平稳。
这个仍然弱小的社群正在被分裂,不是因为我批评了梁钰,而是因为梁钰从良背叛了“婊子”的群体。她通过自己不再留在社会抗争的中间地带里,而缩小了这个中间地带,缩小了其他的多数不入党、或者没有资本搞高调入党秀的女权者的抗争合法性。这跟个人为求职求存而入党完全是不同的做法,也有不同的后果。在中间光谱上站差异的位置,这并不是本质性的问题,但女权者之间的差异,要警惕却是在完成一个父权政治的布局。是在这样的层面上,梁钰入党秀才需要基于对运动的责任而被辨析,在这个关键时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什么个人纷争——这种思路是女人对男权思想的再生产。
(吕频:我的微信号是pinerpiner, 请勿私聊。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号还能存活多久,大家随缘。)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