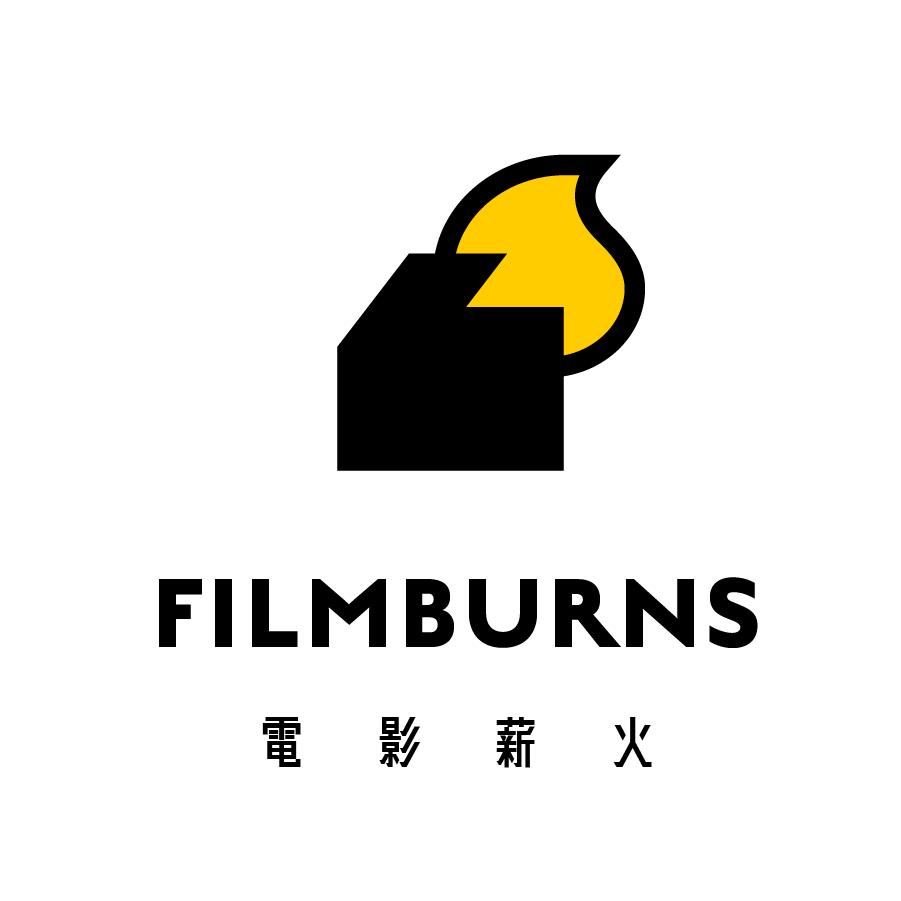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狗陣》:邊緣人不打邊緣狗

普天同慶、舉國同殤——2008 年,中國人經歷了一場跌宕起伏的「情感過山車」。5 月的汶川大地震奪走無數生命和家園。轉眼三個月後,北京奧運聖火點燃,首次主辦奧運和獎牌金榜的成就鼓舞人心,彷彿驅散了些許陰霾。那一年,巨大的悲傷與無比的歡欣同時交織著,奪盡媒體目光。然而,鏡頭未及之處,還有些被遺忘的角落。

十六年後,中國第六代導演管虎帶來了電影《狗陣》,透過一個歸鄉的獲釋犯人與一隻兇猛流浪狗的故事,聚焦當代中國被忽視的邊緣群體——那些難以跟上大時代的急速發展的人們。
故事發生在戈壁沙漠中一個虛構的西北小鎮——赤峽(實際取景地是甘肅省瓜州縣柳園鎮)。有別於繁華省城,中國西北地區多是靠近沙漠,氣候乾旱;城市化程度低,政策以「西部大開發」為導向,因此在想像地理(imagined geography)上,往往令人感到遙遠和落後。導演運用大量長鏡頭和遠景,呈現無垠的沙漠和灰暗的小鎮,成功突顯這個「邊緣地帶」的蒼涼面貌。在這片土地的頹垣敗瓦中,有學校、醫院、社區中心,更有附帶「笨豬跳」的遊樂場和動物園,破落中可見石油小鎮曾經的繁榮。
犯人二郎(彭于晏)獲釋後,事隔十年回到家鄉赤峽,家人早已搬走和離世,只餘年邁父親搬到已經停業的動物園,與動物相伴。二郎曾是鎮上紅人,當年的花式電單車高手,卻因誤殺罪入獄。他回到鎮上不受父親待見,還不斷被當年死者的家屬尋仇;而且沒有工作、和社會脫節。在快速發展的時代,鮮少說話的二郎代表著社會裡被忽視和排斥的邊緣群體。

人和動物的感情是妙不可言的。在現實生活中,人類偏愛為寵物穿上毛絨絨的好看衣服,又為牠們取名字,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這些動物身上。在《狗陣》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人類試圖喚醒自身的動物性。「邊緣人」二郎因緣際會遇到了一隻「邊緣狗」黑狗,牠是流狼狗的一員,只因以往的家犬沒有隨居民外遷,不斷繁衍下產生了流浪狗問題。面對發展出路,貧瘠的小鎮必須吸引資金設廠,首要任務是盡快整治流浪狗,沒有付費辦證的寵物犬亦不能豁免,尤其是大家口中「通緝的要犯」——那隻特別兇猛,單獨行動的黑狗。
電影中捉狗的陣法是「三人組成三角圍住狗,一頂二套三挑起」,人與動物的野性彼此較量。加入捉狗隊的二郎並沒有熱衷於此,反倒動起惻隱之心偷偷放走居民的寵物。二郎更從與黑狗最初的敵對,到最後彼此相伴,建立深厚感情。不同的邊緣群體同處艱難環境,仍能互相扶持,這一人一狗,巧妙地呼應了「二郎神與哮天犬」的神話故事。二郎在黑狗身上逐漸尋回對生活的希望和勇氣,最後重新出發,趁「天狗食日」的天文異象,與一眾動物破陣而出,離開家鄉。

二郎選擇遠走,卻有人選擇留下。電影中,二郎與遊樂場管理員的對話意味深長。二郎問:「你還沒回老家嗎?」對方回道:「回啥老家啊,老家也沒人了。我回去了人家也當我鄉巴佬。人老了,不挪地方了。」這段對白除了道出了許多現代人的心聲,也揭示了現代社會的高度流動性,「家」不再是從一而終都是同一個地方,外人眼中的邊陲之地,卻是某人生活的重心所在。《狗陣》並不是將「邊緣」與「中心」簡單對立,除了關懷邊緣群體,亦呈現了一種流動的、不斷變化的社會結構。曾經繁華的小鎮因經濟發展的轉變而衰落,昔日的「中心」日漸淪為「邊緣」。而馬戲團更是強化了流動性,除了到處巡演,身材異於常人的團員,不再是社會中被排斥的邊緣群體,反倒被成員接納,共同為每個地方帶來短暫的娛樂,邊緣與中心的界限是模糊而流動的。

比較遺憾的是,電影在女性角色的塑造顯得非常薄弱,馬戲團女舞蹈員葡萄(佟麗婭)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強調「婚姻是女人的出路」這一陳腔濫調。本來欣賞導演對邊緣群體的關懷,可惜在這部以「邊緣性」為主調的電影中,女性角色卻被推至邊緣的邊緣。
在社會急速發展的同時,邊緣群體跟不上腳步,不是出現在單一國家的現象。電影的作用正可呈現主流鏡頭未盡之處,喚醒對邊緣群體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