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是哲學還是漢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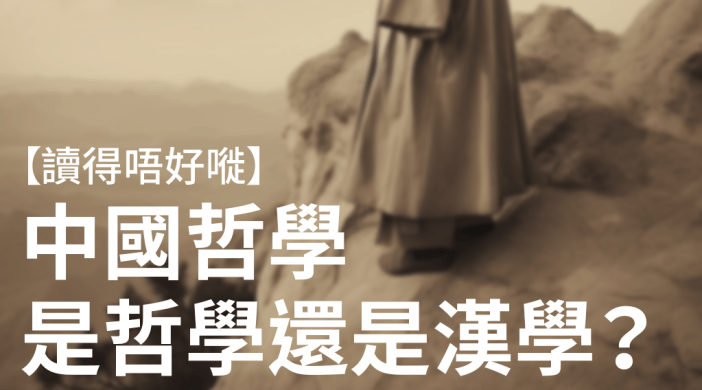
文|豬文
之前讀 Ásta 的《Categories We Live By》時,讀到一段讓我感觸很深的文字。這本書希望回答的問題是:究竟我們生活裡各種社會性質,例如:「女人」、「美國人」,是怎麼樣的存在,並且藉著回答這個問題推進社會進步。她說,這本書的研究領域處於各種範疇的交界,而開拓這個交界,是一場「空虛寂寞凍」的探索。對於形上學家來說,形上學應該研究世界的基本實相,而社會性的東西不可能是根本的,所以不值得搞。對女性主義者來說,這種離地的形上學討論完全無關於解放,不會幫助到我們批判和改善這個社會,所以是無力的。
這種兩面不是人的困境,對研究中國哲學的我,有很大共鳴。因為中國哲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到了當代仍處於一種徘徊在漢學與哲學之間的狀況。中國哲學不是研究孔孟老莊那些經典嗎?怎可能是新興的?當然,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很大部分都是過去的著作。如果「中國哲學」指的是這些經典的話,中國哲學當然存在已久。但如果「中國哲學」指的是一門學科的話,那這門學科的歷史便短得多了。
把這些著作視為哲學著作、以哲學的角度詮釋這些著作、甚至「中國哲學」這個概念本身都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產物。這是中國遇上西方文化的一種反應:當時的人用各種源自西方的學術分類去重整自身的文化資源,把著作歸類,並開始按其所屬的學術範疇審視他們。所以,中國哲學既非中國的(因為這不是中國傳統自身的學術分類),也不是西方的(因為「中國哲學」一概念往往是對住「西方哲學」去提出的)。
當中國哲學學者嘗試用哲學角度詮釋中國古代經典時,總要面對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漢學家會說:「你的所謂哲學詮釋誤解了古漢語的文法和忽略了當時具體的歷史脈絡。」另一方面,哲學家會說:「這些思想頂多是一些人生智慧,沒有嚴謹的論證,看不出他的哲學意義。」要滿足漢學與哲學各自獨立的學術要求,幾乎不可能。以我自己經驗為例,有次考試被一位漢學家突然質問我某古漢語此處的詞性,簡直嚇出尿來(是副詞,我答對了,好彩)。而當在哲學家面前講解自己研究時,又深怕被嫌不夠「哲學」(幸好搞過荼毒室,被嫌不夠「哲學」的經驗夠多,笑)。唯有跟其他中國哲學同行交流時,才比較自在,起碼不用由頭解釋自己做的事。
漢學對中國哲學的挑戰,在中國哲學經典的作者問題上,尤為棘手。哲學詮釋往往以分析文本所創造出來的哲學系統為目標,而這個抽象的概念體系又往往被預設為貫融的。例如,當《論語》裡對「仁」的想法有字面衝突時,中國哲學學者的任務則為尋找字面衝突背後貫融的哲學概念。因此,中國哲學的工作似乎預設了文本的一致性,甚至單一作者的概念。
可是,從漢學的角度看,所謂單一作者的想像,根本不符合這些哲學經典的歷史現實。很多先秦經典都是集體傳誦和書寫的結果,並非以現代哲學那種單一作者的創造模式所創造出來。以《莊子》為例,《史記》裡的確紀載過一位歷史裡的莊子。但學界的基本共識是,《莊子》這本書絕不是這個人的個人著作。《莊子》的不同篇章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筆,有些作者可能只是歷史莊子的景仰者,他們所處年代也可能相差甚遠(所謂內七篇由歷史莊子所著一講法也受到很多質疑)。如此一來,有關《莊子》的哲學工作好像失其著力之處。為什麼《莊子》會充滿自我矛盾?就此問題,《莊子》哲學研究者努力建立一個所謂貫融的莊子哲學體系,但漢學家只拋下一句:《莊子》沒有單一作者,所以有矛盾。
當然,中國哲學學者沒有輕易投降。在回應這個質疑的過程中,中國哲學學者都不斷重新定義中國哲學這門「新興」學科的本質和基本關懷。中國哲學一直徘徊在漢學與哲學之間,也一直在尋找出路。
參考資料:
Tao Jiang, The Origin of Moral-Political Philosophy in Early China, Introduction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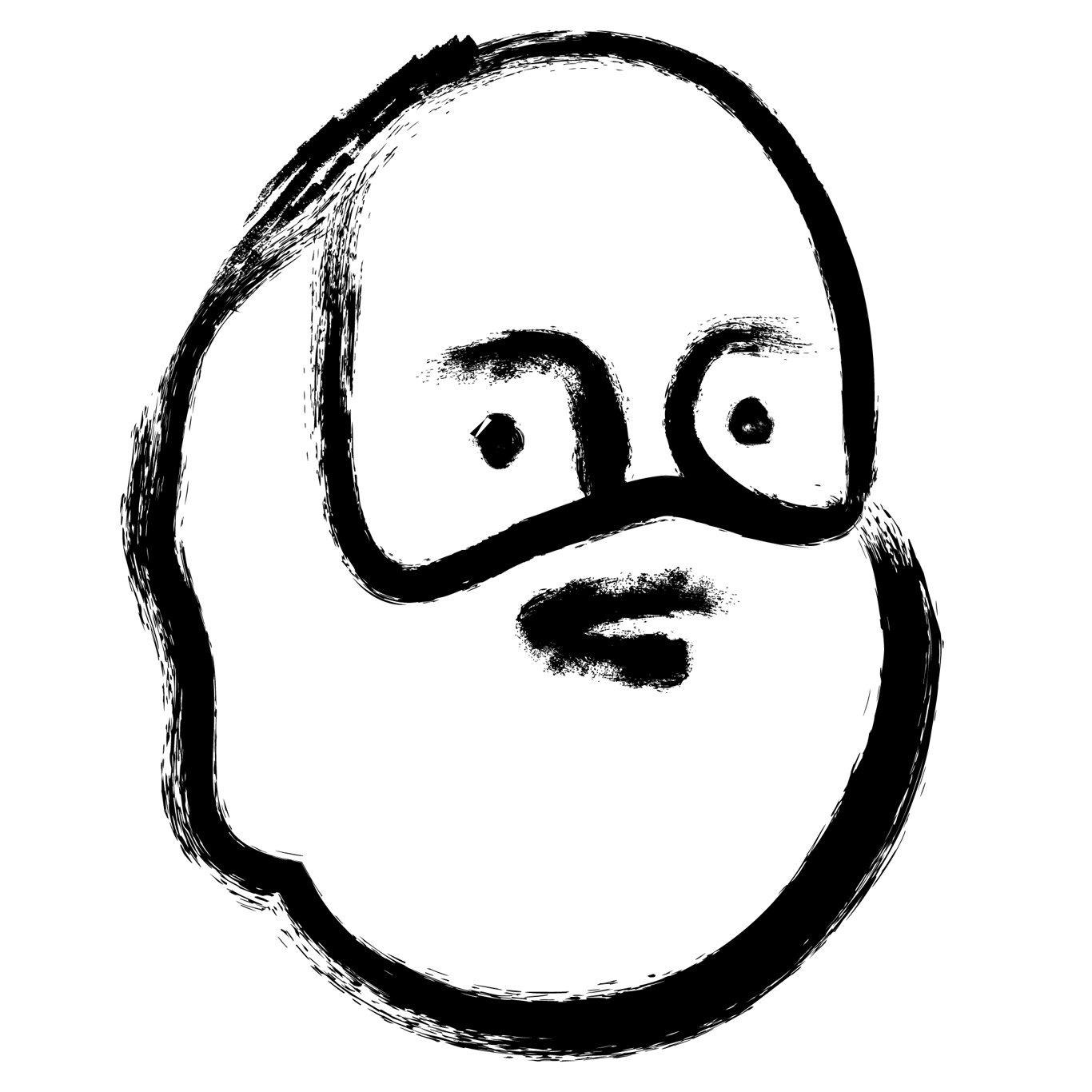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