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民族誌第一篇】從越南到木柵,威哥的人生旅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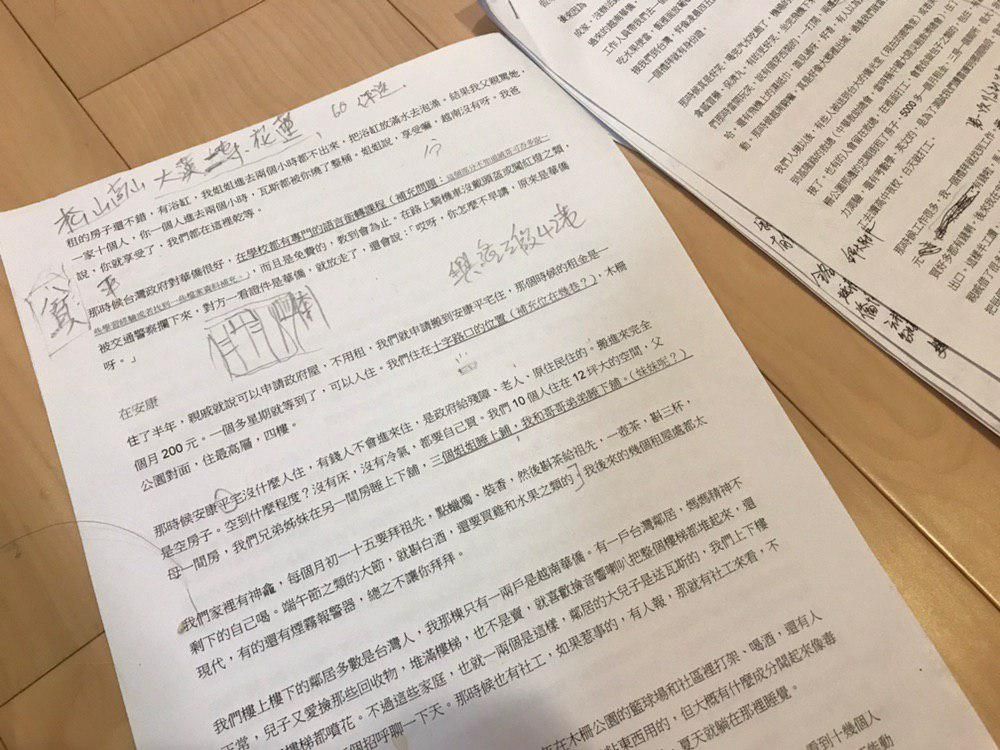
這是政大公共人類學寫作小組在matters發布的第一篇合作民族誌,由小組成員@島民與社區夥伴威哥共同完成。歡迎追蹤我們的寫作小組@政大公共人類學寫作小組,每週與你分享興隆安康的故事。
我叫阿威,今年53歲,是一名台北木柵的計程車司機。但我不是台灣人,我是越南人,雖然你看我的樣子,聽我講話,會覺得分不出來。我是華人,祖籍廣西防城,文革的時候,我爸媽帶著才幾歲的大哥大姐走路逃難,好幾年才逃到越南宣德省的從義安定下來。我就在從義出生,22歲之前都住在越南,直到1975年越戰結束,南越淪陷,我們又開始四處遷移,到1988年,「仁德專案」接我們來了台灣。之後我們家在安康平宅住了7年,兄弟姊妹都大了,才陸陸續續搬出來。
1、在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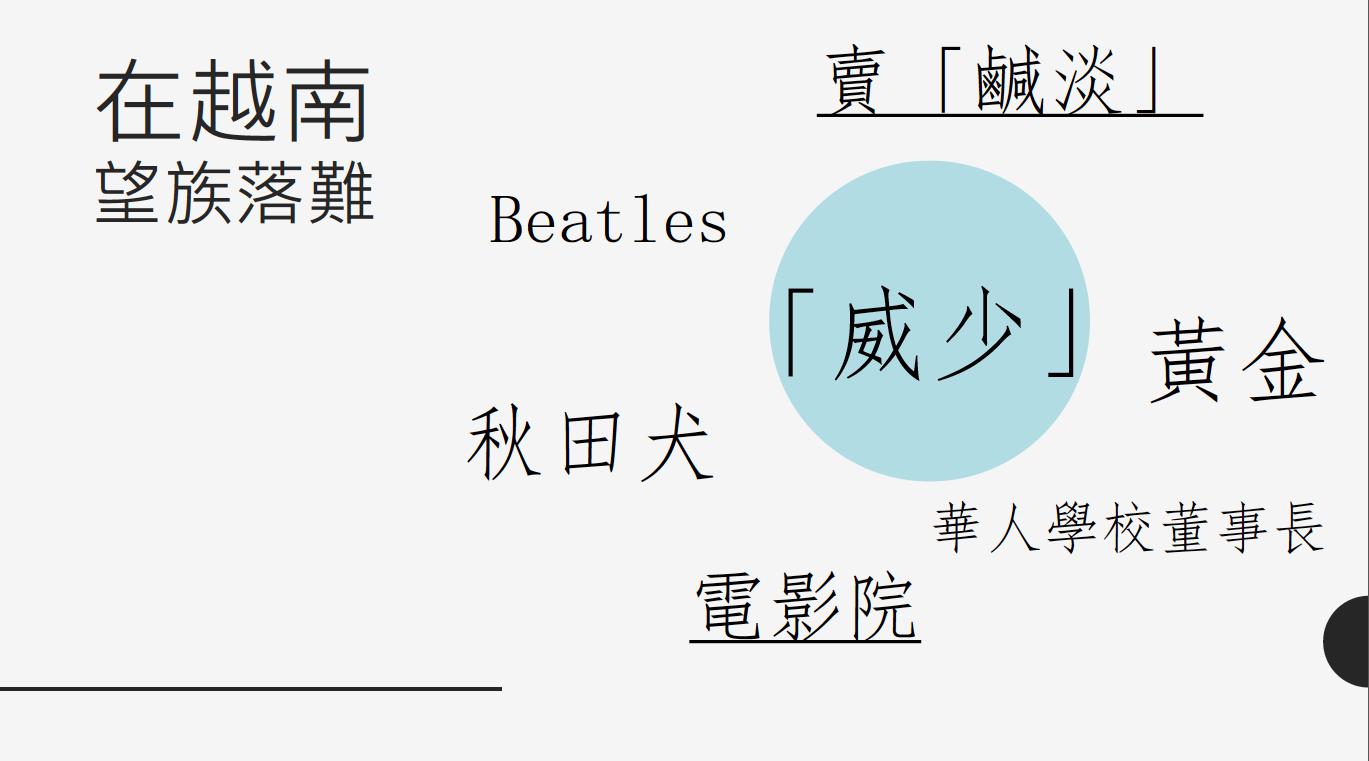
從義地方很小,但空氣好好,一年氣溫都是18-20度左右,很舒服。當地人種穀種豆種玉米,風景很美,有條江,有幾個瀑布很美。我們家在從義算是望族,從我5歲一直到越南淪陷,我爸爸都是當地兩間華人學校的董事長。兩間學校一間叫義德,一間叫剛峰,後來合併,就改名叫中山中學,有小學部和中學部,我讀的就是這間。
我們家還經營一間電影院,還有一間五金店,算是有錢人。小時候我們都不需要去打工,在學校讀中文、英文、法文。我姐姐在鄉下讀完初中就到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讀高中,四個姐姐都很厲害,還在西貢給人補習英文、法文、中文、越文。
我們家以前養兩隻日本狗,不知什麼品種,矮矮的,類似柴犬,黑白都有。有錢人養狗當寵物,一般人不會養這種,是養狼狗,用來看門的。但南越淪陷之後,我們要逃離從義,兩隻狗就帶不走。我姐姐帶我和兩個小的先去西貢,想一起上飛機,但當時好亂,兩隻狗在機場就不見了。
講難聽,我們家以前是有錢。為什麼難聽?因為南越淪陷以後,越共進來,我們生活就發生巨變。以前沒解放,治安好,環境好,政府不會管你賺錢,但解放後不一樣,越共進來,就要管你。政治這件事很不好,它知道你有錢就怕你有影響力,我家又有名氣,是知識分子,政府就怕你集中一些人搞事。學校不能再教台灣的教材,學了半年的簡體字,之後越共又跟中國大陸交惡,乾脆禁了中文,我們家開的學校就被政府關掉了,我爸爸也好幾次被政府的人叫去問話。
那時候人心惶惶,越共的政策不知會怎樣。例如突然要「換錢」,說以前的貨幣不用了,給你新的錢,但就不是按照你本來有多少錢就給你換多少,而是不管你有多少錢,每個家庭就是給你兩百塊。像我們家算是有錢的,那不就慘了?當時說要平等,窮人就好啦,我們有錢人好多就很慘,自殺的也有,幾千萬身家突然變成兩百塊,受不了刺激。每家都要把剩下的多的錢給政府。時間久了,大家覺得算了,現在越共統治也沒辦法,就重新開始做生意,等你做到三五年剛剛穩定下來,有些儲蓄,它又換錢。這樣誰還敢做生意?我們華僑沒人敢做生意。因為做了也沒用,賺錢也沒用,越共就是這樣。
在從義被盯上以後,我們就想偷渡到台灣,申請了仁德專案,但簽證不是馬上下來。我爸和大姐一度先到西貢去想辦法,我媽和我還有妹妹則留在從義。可是那時候偷渡不成,我們只好舉家逃去另一個省的定館先暫居,一邊等簽證。定館的華人也很多,很多都是做農的,種豆種煙草,那裡沒有中文學校,那些人就沒機會讀書,不識字。那時候我已經19歲,算是讀完了國中,但我妹妹才四五歲,就讀不了書,在定館只有些鄉村教師,她就跟著學些古文。
我們同姓親戚,一翻族譜看名字就知道誰是了,就在一個當地親戚家門口借住。鄉下地方每家門口都有一塊地方是曬穀子曬煙草的,叫禾堂,我們就在這個門口地方起間屋,用禾草蓋的。前面攤位,擺糖糕餅仔,前店後屋,一樓就賣「鹹淡」,就是賣醬油、醋、蘿蔔乾、酒、雞蛋、鹹蛋、皮蛋。早上還和我姐姐一起煮糯米飯,賣早餐。我姐姐很會煮食物,會做蛋糕,煮糖水。裡面是床、廚房,在裡面搭棚有個小樓梯可以上去閣樓,叫「香港樓」,即台灣說的「樓中樓」。越南好多蚊子,我們在頂上六個角掛蚊帳,一個蚊帳可以睡好多人。
這樣賣了三四年,我親戚家自己的孩子就眼紅了,他們是種農的,不會做生意,看我們舒舒服服,不用一早下田,又賺到錢,就眼紅,想要拿回那塊地。但是大人之間是有交情的,那個親戚就罵他的孩子,我爸就說,搞得人家家庭吵架,算了,我們搬走。我們就搬到同一條街的另一個親戚門口,又在門口的一塊地起間屋住。那個地方是在一個十字路口,以前那塊地是他們養豬的,有個豬欄,我爸說OK呀,比之前那塊地還大。我們又一直做生意、住在那,但幾年之後,我爸還是被那些搞政治的人跟上,跨省來找我們的麻煩。
戰爭好恐怖。那時我們家環境好,我們小的幾個就跟一個姐姐搭飛機先去西貢。大哥大姐和爸媽一起帶行李上船,幾個月航程,我們都見不到爸媽,只有靠偶爾有封電報才知道他們到了哪裡。另一個姐姐已經成家的,抱著女兒走三四天,女兒一直哭,就在沿路人家門口要一口水喝,睡在人家門口,就這樣走到西貢。大家都到西貢以後,就準備偷渡。
那時候政府半公開地允許有錢人偷渡,一個人要8到16兩黃金,我們13個人,那要一百多兩黃金。以前家裡有錢的時候,我媽會把錢拿去買金,因為錢不穩定,一打仗錢就沒用,所以有錢人都喜歡買金,要不就是換美金。黃金去到哪都可以立即換錢,那時好多人戴金戒指,或是打條金項鏈,方便帶走。我媽存的那些黃金,我家13個人一路吃了13年,就算當初買了很多,到要偷渡的時候,還是不夠用。我那時候還小,聽到爸媽談話,本來商量要不先送姐姐過去,再擔保我們過去,但最後還是決定,一家人要不就一起走,要不就一起留在越南,一起捱。家庭要齊全。
2、做華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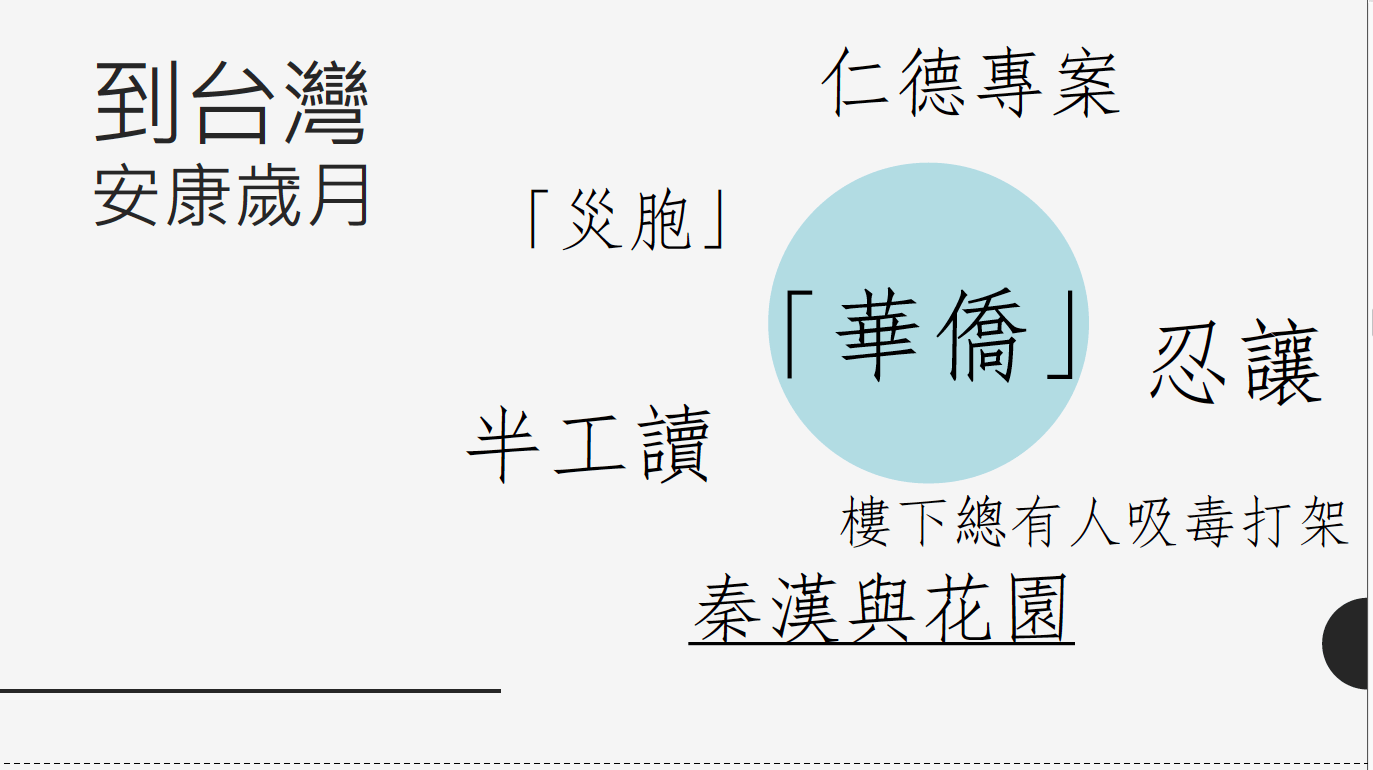
後來因為「仁德專案」,台灣政府開放給華僑申請歸國,我們終於過來台灣。足足等了13年,我們家才逃離越南。
除了大哥和大姐已經在越南成家,沒辦法跟父母過來,我們一家8個兄弟姐妹和爸媽,總共10個人都到了台灣。我們是前幾批過來的越南華僑。我們搭法航的大飛機,可以坐200多人,先飛到泰國曼谷機場,到的時候是半夜。工作人員帶我們去一個露天的地方,搭了個棚給我們吃飯,不能入境,我們就整班人在那喝汽水,吃水果便當,飯裡面放葡萄乾,我們吃不慣,就一隻接一隻地喝免費汽水。吃完之後,就等華航來接我們到台灣,好像凌晨四五點,到了中正機場(現在的桃園機場),我們華僑就全部在機場辦手續,一個禮拜就有身份證。
那時候真是好笑,喝完汽水吃飽了,機場的人問你們哪個有暈機,所有人都舉手,因為有藥拿嘛,拿感冒藥、保濟丸。有的更好笑,坐完飛機下來,飛機不是有些刀叉的嗎,個個都藏在衣服裡。我們那時當開玩笑,說有個穿西裝的,一打開,兩邊掛滿刀叉,好像周潤發《賭王》電影那樣,哈哈哈。還有飛機上的濕紙巾,誰見過呀,好香,有人以為是香口膠,就拿出來咬啊咬啊,哪知道咬不動。那時候越南窮嘛,真是好像大鄉裡出城,過後我們就當笑話講。
我們入境以後,有些人被送到台大的僑光堂(現在的鹿鳴堂)或者美國青年中心過第一晚,我被送到基隆路的救總(中華救助總會,當時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住了一晚,吃過早餐,親戚就來接了。也有的人會留在救總,在裡面打工,會教你做包子之類的,包住,有薪水。親戚幫我們在木柵公園那邊的忠順街租了房子,5000多一個月租金,三房一個廁所,很大。我參加完政府的鑑定考,還有考數學、英文的,是為了測試我們讀書讀到哪個階段,我考完之後就選了大安高工去讀高中夜校,白天就打工。
那時候工作很多,我一個禮拜就找到工作。第一次自己賺到台幣,是因為親戚介紹我去深坑幫一間房子做打掃,做完一天,親戚給了我200元。第一次有薪水,有錢啦,馬上去雜貨店買朱古力買煙,那時候好多東西買,物價好低,買好多都有錢剩。後來我在忠順街的電子加工廠打工,忠順街和木柵公園一帶有很多工廠,做電線出口。這樣半工讀,一個月可以賺8500元。家裡因為過來租房子、安頓,白手起家什麼都沒有,跟親戚借了很多錢,我們打工賺的錢全部都給家裡,因為人口多,所以很快就還完。還完債之後我就把每個月的薪水留一半給自己,存錢買機車,買中古的,一萬多一部,買來方便去讀書,不然搭公車好不方便。
那時候在越南沒見識過這麼多,一來台灣,覺得台灣靚嘛,台北市路上滿滿都是車,一下飛機見到機場也好漂亮。我以前在越南看瓊瑤小說的,金庸古龍也看。越南很少這些書,你有一本,借給我看,又借給他,一圈借回來已經翻爛了。看瓊瑤看得多,當然對台灣有個想象,覺得,哇,我來台灣住當然是住別墅的,好像秦漢,前面有花園,後面有公園。我來了住也是啦,對面有公園嘛,只不過是大家的公園嘛,不是我家的。我也想象過來這裡,浴室好靚。結果我姐姐來了,那時候自己租的房子還不錯,有浴缸,我姐姐進去兩個小時都不出來,把浴缸放滿水去泡澡。結果我父親罵她,一家十個人,你一個人進去兩個小時,瓦斯都被你燒了整桶。姐姐說,享受嘛,越南沒有呀。我爸說,你就享受了,我們都在這裡乾等。
那時候台灣政府對華僑很好,學期末考或是保送高中、大學都有加分。在路上騎機車沒戴頭盔或闖紅燈之類,被交通警察攔下來,對方一看證件是華僑,就放走了,還會說:「哎呀,你怎麼不早講,原來是華僑呀。」
3、在安康
住了半年,親戚就說可以申請政府屋,不用租,我們就申請搬到安康平宅住,那個時候的租金是一個月200元。一個多星期就等到了,可以入住。安康社區以前有三條巷,興隆路三段42、44和46巷。我們住在42巷十字路口的位置,木柵公園對面,住最高層,四樓。
那時候安康平宅沒什麼人住,有錢人不會進來住,是政府給殘障、老人、原住民住的。搬進來完全是空房子。空到什麼程度?沒有床,沒有冷氣,都要自己買。我們10個人住在12坪大的空間,父母一間房,我們兄弟姊妹在另一間房睡上下舖,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睡上鋪,我和哥哥弟弟睡下舖。還有三個姐姐在餐館工作,有宿舍住。
我們家裡有神龕,每個月初一十五要拜祖先,點蠟燭、裝香,然後斟茶給祖先,一壺茶,斟三杯,剩下的自己喝。端午節之類的大節,就斟白酒,還要買雞和水果之類的。我後來的幾個租屋處都太現代,有的還有煙霧報警器,總之不讓你拜拜。
我們樓上樓下的鄰居多數是台灣人,我那棟只有一兩戶是越南華僑。有一戶台灣鄰居,媽媽精神不正常,兒子又愛撿那些回收物,堆滿樓梯,也不是賣,就喜歡撿音響喇叭把整個樓梯都堆起來,還用噴漆把樓梯都噴花。不過這些家庭,也就一兩個是這樣,鄰居的大兒子是送瓦斯的,我們上下樓梯見到面,也會打個招呼聊一下天。那時候也有社工,如果惹事的,有人報,那就有社工來看,不然社工不理的。
那時候安康環境不好,每天夜裡都很吵。青少年在木柵公園的籃球場和社區裡打架、喝酒,還有人吸毒。窮人吸不起K他命,吸一種強力膠,本來真的是粘東西用的,但大概有什麼成分聞起來像毒品,所以就有人吸。也有些酒鬼喜歡在木柵公園的亭子喝酒玩樂,夏天就躺在那裡睡覺。
有一天晚上我們五六個人在家裡玩,到半夜一兩點,突然很吵。我們從四樓看下去,看到十幾個人從對面街追著一個人跑過來,剛好追到我們樓下。他們用木棍打、踢那個人,那個人被打到不能動了,他們就用滾燙的煙頭按在那個人的人中,那個人又醒來,再繼續打。那個人後來應該是被打死了,然後有人叫了救護車、警車來。
我們是外地來的,來到人家國家,怎樣都要忍讓。我也會害怕,因為那時候我讀夜校,常常很晚才回家。不過我那時候已經22歲,出入小心,看看環境,自己不要惹事,低調些,也就OK。但是,再過幾年,我哥的兩個兒子從越南過來,十幾歲讀中學,那時候我就很擔心他們學壞。他們來了就跟安康社區的年輕人混在一起打籃球,學人打架,我真的覺得要搬出去。我們家總共在安康平宅住了7年,幾個兄弟姐妹都大了,有工作,又結婚,終於可以搬出去。
4、遇到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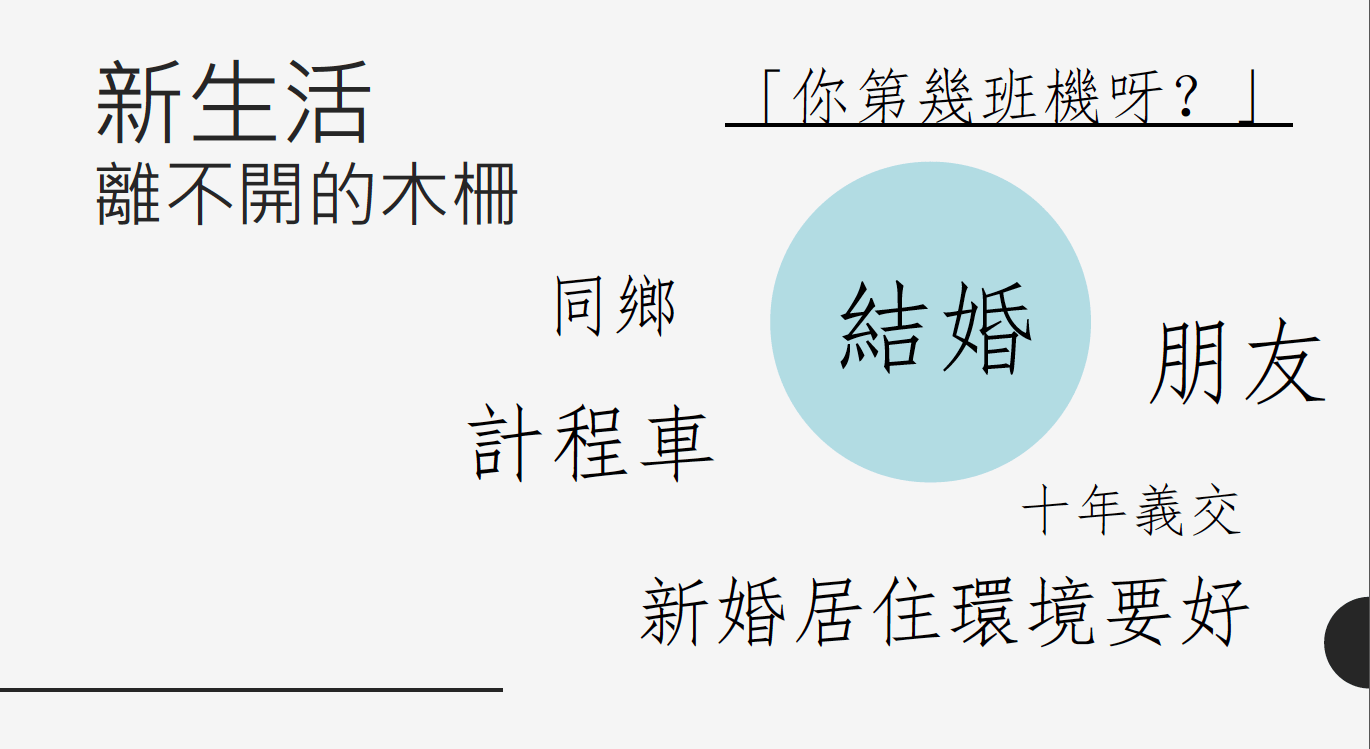
因為我們是第一批越南華僑,所以人還很少,大家都會互相幫。到了台北,我們就打探消息,說哪裡越南人多,聽說木柵越南人多,就來這裡找房子住。到現在還是這樣。除了木柵還有內湖,這兩個地方最多越南人。還有土城,更早期從澎湖難民營偷渡過來的越南人在土城比較多,那些也很多都是廣西海防人。
知道哪一天有越南班機來,就算不認識,我們都會去接機。那時候初來乍到,沒什麼朋友,遇到越南人就問你是哪班飛機,問了發現是同一班飛機,就認識了。而且又要認識女生,大家會討論,這班機有什麼靚女來?好好玩,大家約好,騎機車出來,說這個那個家庭有幾個靚女。那時又沒辦法留電話,沒有手機,剛剛來又不知道住哪裡,就只能先認識人。但我們知道一定會見到的,都是越南華僑,都住在台北,遲早會見到。
那時候好好玩,一年辦一次華僑聯誼會,主辦方是越南歸僑協會和政府的僑委會,地址在台北車站旁的一棟大廈六樓。那時候政府資助,華僑自己組織活動,下有《僑星日報》,還有華僑獎學金。我們的聯誼會是去桃園或別的地方烤肉,幾部遊覽車在台大集合,大家就互相問,哇,你第幾班機呀?那時候就已經住定下來了,可以互相留電話了。那年代只有家裡電話,連 BB call 都沒有。
我就是那時候我認識我太太的。她父親是廣東人,在越南時就聽過我爸的名字。她在越南順化長大,比我晚一年來台灣。剛來台灣的時候,她住在中和,那裡也有越南華僑,比較少。她是依親過來,她大伯先過來,然後申請她過來。她本來不會中文,只會越南語。我大她6歲,就帶她買字典,幫她去報名鑑定中文程度,然後政府再安排她讀書。那時候鑑定考試全部在台師大考,她鑑定完去讀國三,在板橋的華僑中學,跟我妹妹同一間學校,每天要搭公車一個小時去上學。雖然附近也有其他學校,但一定要選公立,不然要錢啊。那時候我在各種事情上幫她,就慢慢熟識了。
我高中畢業以後,有個姐姐嫁到澳洲開餐廳,我就去幫忙,離開了安康平宅。在澳洲住了兩三年,因為我父親中風,我又回到安康,照顧父親。後來母親又生慢性病,我又一起照顧母親。我1995年回來的時候,我太太正在花蓮讀大漢二專,到她大學畢業,我就追她了。1997年我們結婚,我才徹底搬出安康平宅,自己在景美女中附近租房子。
5、新生活
我回台灣以後,輾轉做過木柵一帶加工廠的工人,也到東區的港式餐廳做過廚房,還開電單車和貨車送貨送了五六年。後來為了方便照顧父親,我才轉行去開計程車。到2001年,我用存款買了一部計程車,經濟狀況開始好轉,和太太搬了幾次家,都在木柵一帶,慢慢開始新的生活。
我幾個姐姐分別嫁去美國、澳洲、馬來西亞。嫁到美國的就是那個在浴缸泡了兩個小時澡的姐姐,她朋友多,喜歡打網球,到美國之後開中藥鋪。嫁去澳洲的姐姐,和姐夫在越南曾是同班同學,姐夫當時從澳洲追到台灣。姐姐們嫁人了自然都搬出安康,我也結婚搬出去,就剩下我爸媽和妹妹三個人住。因為安康平宅的房子只有兩間房,不可能結婚了還住。而且申請時一定要用爸爸的名字,因為爸爸年紀大,才可能通過申請。但是年輕人結婚,兩個人都有工作,再申請是不可能申請到的。而且結婚以後,我們要考慮居住環境,如果你住在一個讓你擔驚受怕的地方,整天怕惹事,怕這怕那,晚上又剛好遇到有人在街上喝酒,或是夜裡打籃球很吵,夜裡也睡不好。我們以前住四樓,晚上樓下飲酒打籃球說話全部都聽得到,睡不好。
我和太太在景美女中附近住了一年多,又申請政府國宅,打算和爸媽、妹妹五個人一起住。不久,我妹妹結婚搬走,我和太太再等了一年多,申請到萬美國宅,跟父母一起搬進去,四個人一起住了11年多。後來因為稅金降低,我們的收入超過標準,父母也相繼因病去世,我們才搬出國宅。
木柵公園我也十幾年沒有進去過了,聽說現在整理過,晚上有螢火蟲,我沒去看過。我們曾經住過的那棟樓,現在已經拆掉了,變成空地。但我還是習慣在這裡附近,始終熟悉這一帶,越南人也多,有朋友。我做了十年義交,每個星期有兩天要在忠順街路口站崗。我還喜歡踢足球,在政大的操場認識了許多年輕的球友。但後來我傷到膝蓋,不能再踢,有點遺憾。
平常早上我會睡到十點多,我太太出門上班,我慢慢起床,到木柵的越南小吃店吃午飯,下午就坐在店門口喝冰咖啡、越南茶,和朋友抽支煙,聊聊天。晚上六七點,我會帶便當回家跟太太一起吃,然後滑臉書。我喜歡 Beatles,偶爾彈彈吉他,唱些越南歌和廣東歌。夜裡我喜歡看足球,最近看德國盃,常常看到凌晨兩三點才睡。
我太太大學畢業後,做了越南語的廣播主播,白天在公司錄音、錄影,做節目,內容包括語言教學、醫療、美食、法律知識等等。晚上,她還要在家把台灣新聞翻譯成越南語,這幾年轉做全職,很受看重。她是個很靜的人,和我相反,我喜歡講笑話,喜歡跟人聊天,她聽完我的笑話,總說我「真無聊」。幾年前我和太太搬到了一個有大露台的舊樓,每逢週末我太太不用上班,我們就去逛建國花市,買很多花花草草回來養,都快擺不下了。
因為越南人移民到全世界,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有些去了美國的朋友說,你們家當時那麼有錢,如果當初移民到美國,不知有多好。因為有些以前很窮的越南人,後來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法國,變得很有錢。我說,這種事說不準的,都是命運的安排,不要比較。我現在的生活也很好,每天下午可以喝杯冰咖啡,喝喝茶,抽根煙,又有朋友。如果太太放假,我們也會出國旅行,前陣子才去了香港。我還沒有帶她回過我在越南的老家從義,幾十年過去,那裡已經城市化了。有機會我也想帶她回去,看看小時候玩耍的地方,看看以前的街坊還在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