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鹏
文丨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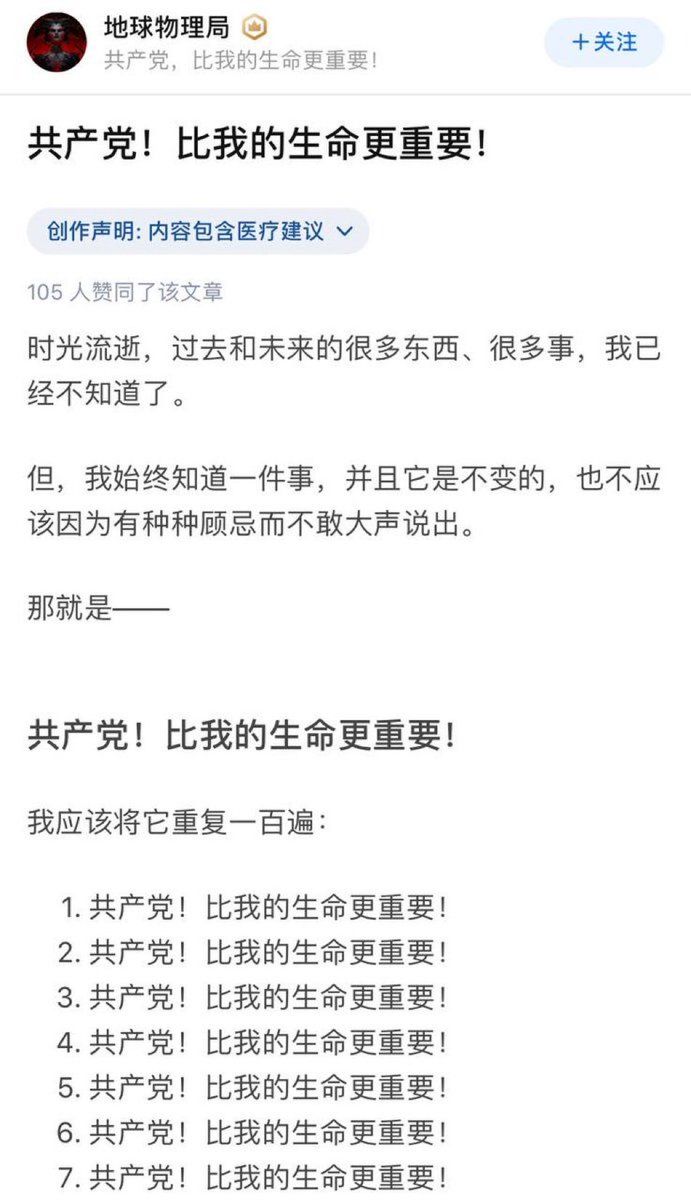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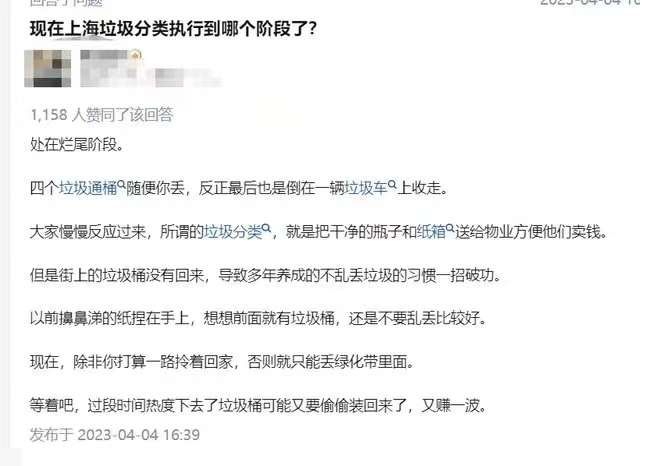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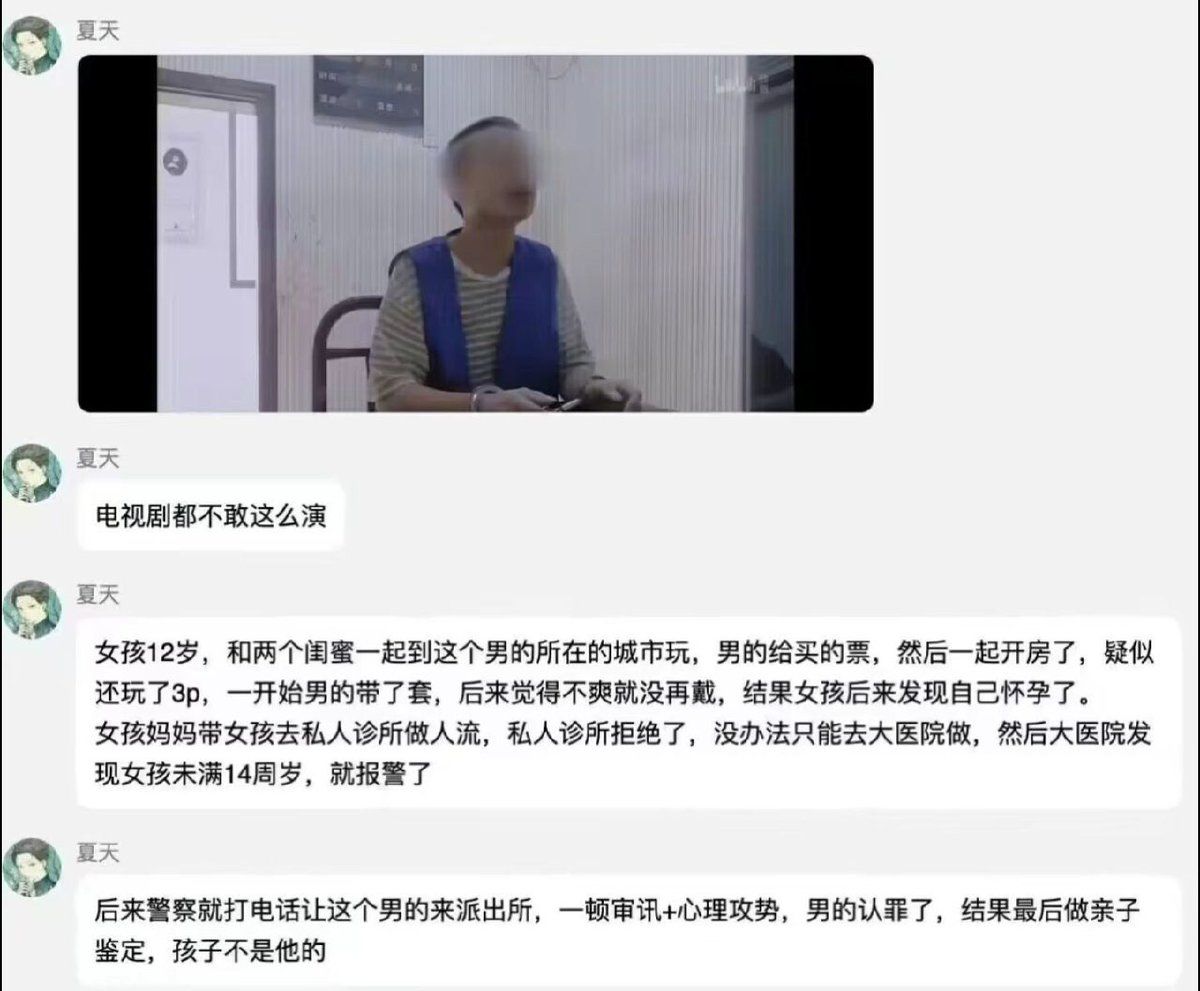

大约有十年没见海鹏了,最后一次还是在延安西路上的衡山小馆。一帮昔日外滩画报的同事聚餐,主角是海鹏——当然他有一种把任何聚会的主角光环加冕过来的本事。那次主角不是他靠机锋和段子夺来的,本就是他。当年主持外滩的陈岚尼女士说,要安排一个饭局安慰一下海鹏。他就带着女儿来了,一个沉默而漂亮的女孩子。
在那之前几年,只是偶尔通通电话,海鹏的手机号码是非常老派的1380开头,和他本人一样映射着牛逼闪闪的光芒。记着一次电话过去瞎聊,居然发现蟹妹和我儿子同月同日生,都是一月初的摩羯,仅仅比我儿子小一岁。海鹏在电话里大笑,冲着旁边的蟹妈说:巧不巧,蟹妹和大头儿子同月同日生!
蟹妹是他的明珠,每次电话都会说起,一次海鹏说:晓得伐,昨天去医院帮蟹妹从耳朵里取出一个非常大的耵聍,回家路上蟹妹一直和我抱怨说路上怎么那么吵!
那几年,他的住所和我相距不过百米,都在狭窄的牛桥浜路上,东接番禺路,西达定西路。
衡山小馆聚餐的年代,微信还没发明出来。后来虽然没再见,加了他的微信,不常对话,但我喜欢潜水看他朋友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黑板报碎片,贴满了本地时政八卦和乡野趣闻,当然,也充满了隐喻、密码,我一般努力自己猜,只有实在无法破解的,才不甘心地微信咨询海鹏。
再后来,他的号炸了几次,也加过一两次转世号,之后,就彻底失联了。但总能在各种群里听到他的传说,以及一如既往的段子碎片。唐宋去世前几年,在红坊开过茶叶店,某次组织大家聚会,说海鹏会来,我临时有事没去。第二天问唐宋,说是前晚海鹏谈兴甚健,段子横飞,脱口秀hold牢全场,听众煞是过瘾。
突然想起遥远的岁月里和海鹏有过一次手谈。当时他还在青年报,我在劳动报,某次饭局过后,他被我拖去南市打麻将。场子是劳动报资深政法记者对口南市的王家骏他爹的公司里。那次他输了好多,害得我以后再也没叫过他。
新世纪最初几年,我和他在外滩画报有过非常短暂的共事。那时他刚从南周出来,坐在宝立大厦一间非常小的办公室里,走过几次,总看到他低头思索,有次还听到他叹气。没两个月我就跳槽去了申江服务导报,在这间海鹏曾经短暂战斗过的本地周报里,也时时能听到他的传说。
海鹏长我四岁。新世纪初正是我们不甘庸常四处跳槽的年代。海鹏最终为了理想越走越远,我为了生活越走越钝。我们的家还是相距很近,但再无走动。
刚才证实过海鹏去世的消息后,我接了一个电话——他申江导报年代的摄影搭档老崔,也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申江导报年代的同事黄飞珏,黄和海鹏还是青年报时代的同事。我简单证实了他的死讯,彼此叹过气,就挂了电话。老崔退休多年,我老黄加起来的岁数也100多了。虽说岁月终究算婊子抑或戏子,但是55岁的海鹏,还是走得太早了。
有朋友截图,海鹏前天的朋友圈说自己明显有些中暑,吃了两支雪糕。配图有点不可名状的诡异。但我和他没失散的那些年,他的朋友圈配图向来神神鬼鬼,也算他的固定风格。
海鹏的最后几年,我没有刻意去在朋友圈里找回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总感觉我接近不了他孤独的灵魂,他很早就遁入了自己的世界,也许是受伤太深,心防甚高,他指点江山嬉笑怒骂,但潇洒之中画地为牢,试图走进的人,会感到刺痛。
他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人,以致于我写这篇文章时居然会字斟句酌。我自然是不能苟同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及处理的手段,但对他热血的尊敬让我三缄其口。或许他会有其他的诤友,或许并没有。我自然没能成为他的密友,他身上的某种匪气让我感到不安全,不是担心他会伤到我,而是我不忍近距离地看到他伤害自己。
一个如此具有才华的男人,和他性格上的黑洞,让我踟蹰不前。真格是: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在踉踉跄跄的人生旅途上,我丢了他,只听到他的声音飘散在风里。
海鹏今天去世了。他是我曾今为之奋斗的那个圈子的传奇。这是个不需要传奇的年代。但凭吊传奇的时候,人们趋之若鹜。
他应该和3年前这个时候去世的唐宋已经碰到了。我在想那次我没能去成的聚会。红坊如今已经拆得面目全非。唐宋曾经的茶叶店在红坊淮海西路入口进去直走的那个通道左手边。我还记得青砖外墙,似乎还有红色灯笼。那个夜晚,海鹏在屋内高谈阔论。我甚至能想象出他的朗声震瓦拍案惊奇的模样。
我很想念他。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