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是我們最後難免的結局——訪《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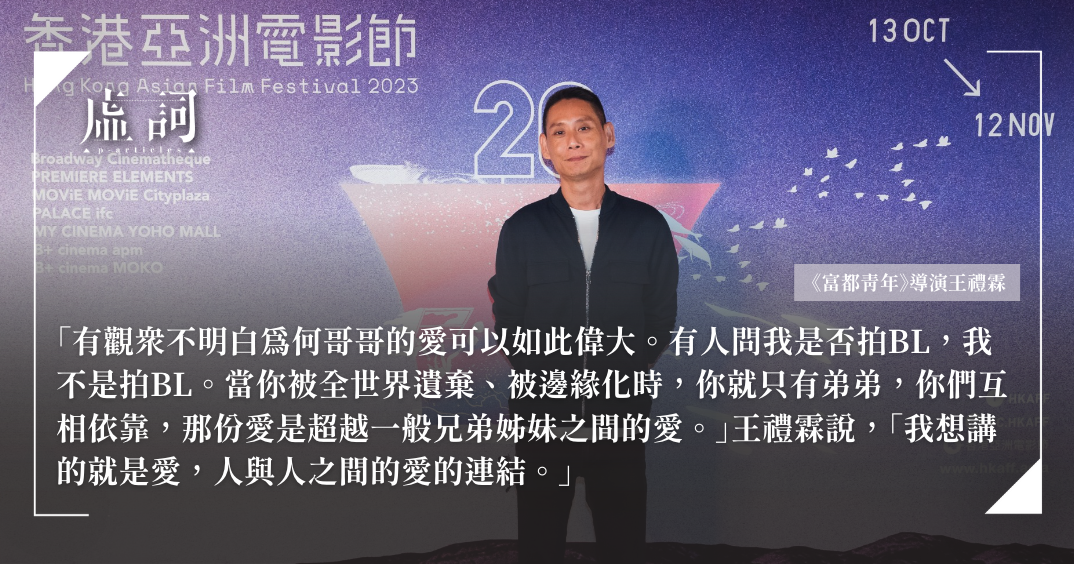
文|黃桂桂
「訪問以甚麼語言進行比較方便呢?」我隔著電腦螢幕問。王禮霖坐在馬來西亞的家裡,說:「用粵語都得。」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他,能自由切換馬來語、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四種語言,和其所執導的電影《富都青年》中的每一個角色一樣,只是電影還多了另一種語言——手語。
(內文含劇透。)
寫一個沒有身份證的故事
今年48歲的王禮霖原本是一名監製及製片,曾參與製作《分貝人生》、《迷失安狄》等電影。「以前不敢想自己可以當導演。」2018年,王禮霖生了一場大病,在醫院躺卧一星期後,他想到未能當導演原來是一個遺憾。2019年12月,他首次交出自己撰寫的劇本參加金馬創投,一舉奪得FPP前瞻視野獎及鏡文學潛力故事獎。那是一個關於馬來西亞紅色身份證的故事,是現時《富都青年》的雛形。
馬來西亞有五種不同顏色的身份證:藍色為馬來西亞土生土長國民的身份證,享有所有國民權益;紅色為成功移民者的永久居民身份者,享有大部分國民權益,惟沒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綠色為暫住於馬來西亞、未能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證者;粉紅色為12歲以下兒童身份證;灰色則是服役軍人身份證。除此五類外,馬來西亞亦有大量因各種原因未能取得身份證的無身份者。
王禮霖一向關注社會議題,《分貝人生》就聚焦貧窮家庭的生活狀況。2020年,王禮霖去NGO做田野考察時發現無身份證者的「Stateless Issue」比起紅色身份證者更值得關注,因為Covid-19期間這群邊緣人士被排除在政府資助政策之外,「為甚麼他們就拿不到資助?他們如何面對社會的挑戰及世界的殘酷?」就這樣他定下了哥哥阿邦(吳慷仁飾)及弟弟阿廸(陳澤耀飾)的背景。
聾啞人士的無聲控訴
「我是先寫弟弟的,」王禮霖說,「寫完弟弟才寫哥哥。老實說,原劇本中哥哥和普通人一樣是會說話的。」寫著寫著,他想「當這個群體面對那麼大的壓力及困厄時,他們卻無法發聲,那個無聲控訴會否更響?」於是阿邦就成為一名聾啞人士,「他不只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整個邊緣社群都處在一種無聲狀態之中。」無論他們如何吶喊、反駁,世界依然別過頭去。
可是,電影最後,在阿邦噙著淚水,顫抖著雙手向法師控訴世界的不公時,他首次張開喉嚨喊出了三個字:「我想死。」事實上筆者覺得吳慷仁的手語演繹已經足夠有力道出他的生之無奈,開口說話是否代表導演不信任這段無聲控訴的力量?王禮霖否認,「我本來就在劇本寫了這三個字。因為那一場戲他說話的對象是法師,而法師代表宗教,宗教是全世界甚至全宇宙的,所以他的控訴也是對世界、宇宙的。我覺得當一個人不斷被壓抑,臨界極端狀態時他就會爆發。而當一個聾啞人士也開口說話,那個控訴的力量似乎更加強大。」

在王禮霖的原劇本中,阿邦與法師對話那場戲甚至只得「我想死」一句台詞。他和吳慷仁在25天的拍攝期內一邊拍攝一邊感受一邊討論阿邦的劇情走向,劇本在拍攝期間修改了足足三十多次,「改到我都懷疑人生。」對新導演來說,每次修改劇本都像被人重擊一拳,打著打著就容易沒了底氣。
王禮霖原本安排Money姐於阿邦及阿廸在菜檔工作時出場打招呼,後來看試剪覺得欠缺生活感及力量,在與剪接師商討過後,決定在緊絀的檔期中安排重拍,「劇組人員第一反應是:邊度仲有時間?」最後還是改拍三人吃飯那場戲作為Money姐出場,王禮霖甚至大膽得不喊Cut,任由演員自由發揮,「只要我不喊Cut,他們就必須繼續演下去,那個狀態是很自然的,營造了一種歡樂氣氛,像一家人似的。」
由於馬來西亞語言混雜,不同語言的手語不盡相同,因此每次修改台詞都要向手語老師請教。電影中除了阿邦,其他角色基本上都說超過兩種語言,而這就是馬來西亞人的日常。王禮霖先以中文撰寫劇本,再因應日常情況在台詞標示「馬來文」、「英文」、「廣東話」、「孟加拉語」等,有時甚至一句說話夾雜兩三種語言。「有的馬來西亞中文電影就只說普通話或廣東話。但對我來說,如果我要拍一套馬來西亞電影就應該是這樣的。」
一天天蒼老下去的富都
《富都青年》故事發生在富都(Pudu)——又稱半山芭,為吉隆坡一個老舊社區,鄰近商業中心,是外勞聚集地——這個名字含「富有都市」意思的地區卻居住大量貧窮的邊緣人士,有像阿邦及阿廸這樣的無身份證人士,亦有像Money姐一樣的跨性別人士,在無處可去的國度,這是他們唯一的安身之所。
「我覺得要說非法入境者、外勞、孤獨、貧窮的人,富都是很好的地點。」富都在王禮霖的成長中留下深刻的影子,富都車站是吉隆坡其中一個重要轉運站,王禮霖讀書時常常經過,從車站走到市場,他目睹著她附近地區的大廈拔起而生,只有她一天天蒼老下去。

2017年製作《分貝人生》時,王禮霖雖研究過富都,但直至拍攝《富都青年》,他才真正走進富都的皺摺中去:在經過一幢大廈的三樓上天台前,他發現一整層三樓都是劏房,裡面就是待宰的外勞;附近的廁所恐怖得劇組無人敢去,王禮霖走出來說:「我去試試!」因戲中的角色就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晚上在後巷把燈一打上去,老鼠們像流水般逃竄到陰影之中,留下一條光猛、明亮的小巷。「拍攝《富都青年》時,我是不臭的地方不去,不髒的地方不去。」
老去的人有股老人味,老去的富都亦有股富都味。王禮霖說尤其在晚上,人們收檔離去後,一股無名的氣味就跟摸黑的老鼠們一起躥出來,揮之不去,「它一直困擾著我,究竟是甚麼味道呢?」王禮霖想了想,「我覺得是一種夜晚的騷味,因為這裡人口太密集,很多外勞、形形色色的人,而馬來西亞只有夏天,他們流出的汗水就悶在鍋裡,無法流動。」只有在人去樓空時,氣味像放學的小孩得到解放。
對阿邦的殘忍與溫柔
電影在2022年6月開拍,整個劇組人員在最炎熱的季節窩在悶熱的富都25天,壓抑的不止氣味,還有整個劇組。「在拍攝過程中,慷仁都很專注,老是坐在一邊練習手語,大家都很大壓力,尤其是化妝師、髮型師生怕騷擾到他,不敢隨便跟他說話。」王禮霖回憶說,「直至拍罷最後一個鏡頭,慷仁才終於釋放,綻放笑臉。」
「你對阿邦這個角色是否太殘忍了點?」我忍不住問,阿邦是聾啞人士、沒有身份證、要坐牢,還因犯罪被判處死刑。「你這個問題對我才是真的殘忍,哈哈哈!」王禮霖開懷大笑,「有觀眾說我用一個很溫柔的方式去說一個殘酷的故事;有意大利評審說我將一個有希望的故事放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他也說我殘忍,哈哈!其實從一開始阿邦就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在寫劇本時也問自己,這應是一個甚麼Tone的故事?我覺得這個題材一定不會開心,只能從悲傷之中反映世界。」
王禮霖對阿邦唯一的溫柔,就是為他的人生添上弟弟阿廸。王禮霖原生家庭中有一位姊姊,他自小便渴望有個弟弟,於是《富都青年》寫的是兩兄弟的故事。阿邦十多歲時父母便意外離世,他遺失了身份證、出生證,成為社會上的幽靈,在絕望之時阿邦曾想自殺,偏偏這時遇上年紀更小的阿廸,阿廸成為他生存下去的動力,讓這個身處絕境的人學會怎樣去愛,甚至使他願意犧牲自己,讓阿廸重生。

在寫阿邦與阿廸的故事時,王禮霖耳機不斷播放中國男歌手隔壁老樊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擁抱你〉,這像是一首阿廸唱給阿邦的歌:「世界上有很多的東西/你生不帶來死不帶走」、「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個人離去/我們在一起說過/無論如何一起經歷了風雨/平平淡淡安安靜靜的老去/我們拚命的相擁不給孤獨留餘地/無力是我們最後難免的結局」。王禮霖每次聽這首歌都會花了眼睛。
「有觀眾不明白為何哥哥的愛可以如此偉大。有人問我是否拍BL,我不是拍BL。當你被全世界遺棄、被邊緣化時,你就只有弟弟,你們互相依靠,那份愛是超越一般兄弟姊妹之間的愛。」王禮霖說,「我想講的就是愛,人與人之間的愛的連結。」
鐵柱磨成針的日子
這種愛不止體現在阿邦與阿建兩兄弟之間,還有Money姐對阿邦阿廸的照顧、外勞工人與阿邦分享飯盒,整個邊緣群體之間都在互相輸出溫暖。
1999年,王禮霖25歲,剛剛修畢廣告設計的他由於碰上馬來西亞經濟蕭條,有台灣外勞中介公司叫他到台灣工作,免得失業,中介公司原本聲稱是到台灣組裝電話,王禮霖想著可以看看世界,就起行,沒想到卻被人派到鐵廠去磨鐵,還碰上從未遇過的冬天,又冷又辛苦,在台灣的第一個月他常常哭,尤其是在寫信回家時。哭完翌天上班,來自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外勞會安慰他:「我昨晚聽到你哭⋯⋯」同樣是離鄉別井的人兒,他們就只有彼此。
「如果可以選擇,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呢?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退路。」正如阿邦和阿廸坐上的那輛公車,跌跌撞撞奔向難以避免的結局。「造成這個悲劇的其實是制度,電影沒有人殺人,是制度殺人。」
《富都青年》在馬來西亞上映12天已有300萬令吉(港幣約510萬)票房,引來巨大迴響,甚至有聯合國人員、馬來西亞關注無身份證人士議題的單位都找王禮霖聊天,探索這議題的更多可能性,「我覺得電影可以做到這個結果——讓大家看到世界某個角落發生的事情——就已經很好了。」那些在電影中沒能發聲的人,透過電影獲得了發聲的機會。
訪問最後,王禮霖腦海響起了一首歌,一首貼切他構思《富都青年》概念的歌——林憶蓮的〈只要我活過哭過〉:「不跌過未算飛過/不痛過未算哭過/哭聲之中找笑聲/只要我活過哭過/不怕我活錯哭錯/即使這也叫任性/讓我且一次任性/像野花一次開過/便算一生燦爛過/只要我活過哭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