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义是主义,你的主义什么都不是
一
今年是《女权主义》Feminism课的第三年,也是三年来这门课第一次可以进行线下授课。课程开始之前,有些期待,毕竟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Zoom课。另一方面又稍有担心,因为终于迎来线下课了,要抗议的学生也可以线下来抗议了。因为课程负责人正正是墨大头号坏人Holly Lawford-Smith.
第一年开课的时候,疫情第一波刚过去第二波马上到来,课程必须线上。不知道是因为哲学系终于开出了女权主义课,还是因为线上课程,三周的密集式课程竟然有两百多人报名。可能也因为突然的人气,网络上开始出现对这个课程的攻击,以及要进行抗议和阻止。因为还在疫情期间,当时又经常出现Zoom bombers的新闻,于是学院让我们全部授课人员开会并且接受Zoom网络安全训练,还要草拟一份网课安全protocol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课程最后还是顺利。
第二年开课前,墨尔本解封了将近半年。在稍微恢复正常的校园,抗议Holly的活动和游行也重新回来了。根据学校规定,学生要获得一门课程的学分,讲授课lectures没有出席要求,但导修课tutorials必须出席,所以学生原则上只需要上导修课。既然这样,抗议的目标就变成《女权主义》课的导修课,主题变成了“no transphobia in our tutes”。除了游行,学校里还到处张贴了反对的海报,还贴在了我们办公室前面。估计因为这些抗议活动,课程报名人数减少到一百多,授课的也只需要Holly和我两个。因为Delta卷来,虽然还未封城,课程还是需要线上。课程开始之前,网络上又出现了要抗议和升级行动的声音,于是院长让我们再接受网络安全训练,拿到训练文档的时候才发现,就是我们去年自己写的protocol。不过,因为担心行动升级造成人身安全问题,院长还是让我们回学校办公室上网课,这样至少学校可以提供安全保护。这一年,课程还是顺利进行,然后我们顺利进入墨尔本又一次封城。

然而第三年开课,终于恢复线下授课,我的担心变得毫无意义。尽管学生向学校提出书面要求对课程进行审查,Holly需要请律师接受学校调查,最终学校结果认定课程没有问题。担心有学生不满结果,所以担心会不会上课时有抗议活动。谁知道,课程都结束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二
几年来课程虽然有部分修改,但大致上还是讨论相关的一些女权主义哲学议题。我们讨论压迫的概念和女性的压迫、patriarchy的概念和起源、女权主义的流派、物化objectification、美貌规范beauty norms、性工作和色情、生育议题、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的概念,以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概念。
引起争议的是性别认同的那一课,顺带还有性工作以及交叉性。因为Holly的公开立场是反对使用性别认同的概念来决定和划分什么是性别,认为生理性别存在且重要,她反对因此将跨性别女性列入女性的类别之下。
(关于这个议题,我写过《性别、身体、跨性别:到底谁才是女人?》和《读点什么|〈不可逆的伤害〉》)
因为这个立场,她被指控“恐跨”“否认跨性别女性的存在”“煽动对跨性别女性的暴力”。她于是常常被女权主义者拒绝同台,也拒绝讨论,因为“跨性别女性的存在不容讨论”,尽管她甚至在电视节目里表示,她认为跨性别女性的确面临许多困难,这些需要社会提供支持和帮助,只是不应该通过削减女性争取到的资源来进行。(SBS节目Insight: Gender Games)
只要在这个议题上她持反对意见,她就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她是极右,她是反动派,她动机不良,连她经过学术盲审出版的书都不应该被出版,她负责的女权主义课程自然不能接受。
三
在此我主要不是要为Holly进行辩护。这些事请让我想起哲学家Robert Talisse的书,Sustaining Democracy。在书里面,Talisse仔细讨论了我们的想法和信念的两极化如何让我们无法在社会中友好地相互尊重。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一方面我们都持有自己坚信的正义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平等,于是,我们都面临着内在的张力:我们如何继续尊重一个在我们看来并不正义的人的平等?当我们的信念极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当不正义的代价很高,任何不同意我们的正义观的人,我们都需要将她们打败,方能彰显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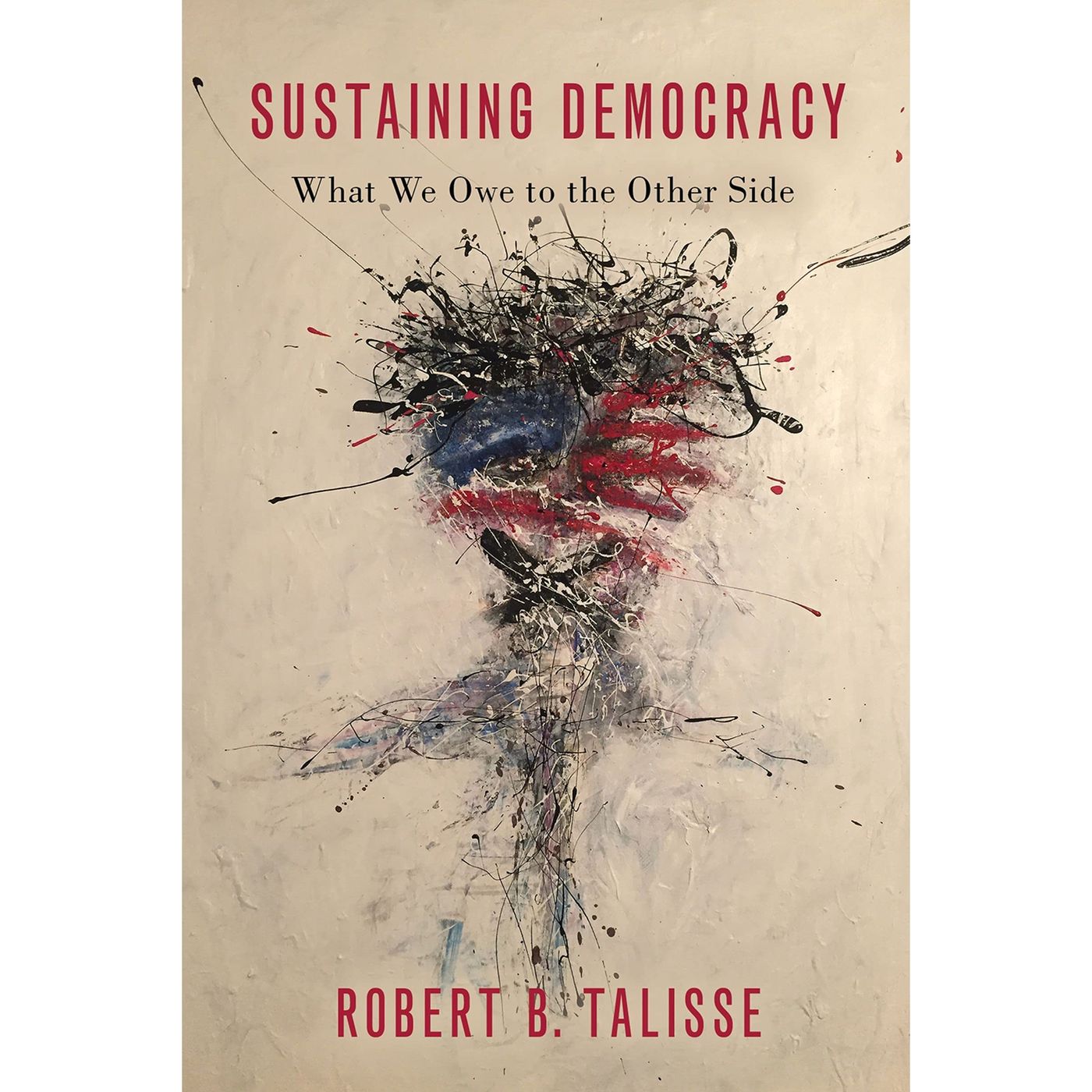
在这样的氛围下面,甚至盟友都似乎变得不可能。我们不再相信那些提出批评和不同意的人,是在进行真诚的对话。如果对方真心相信正义,她是不可能持有其他立场的。尤其是在现在,种族歧视、性别主义等等当道的社会下,持有任何其他立场,都等于站在不正义的一方。盟友就应该站在完全一致的位置上去反抗各种非正义的势力。只要不一致,她就不是真正的盟友。
我的主义才是主义,你的主义什么都不是。
四
这样的变化倒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不正义当道的社会氛围下面,许多人的权利受到损害,这是非常大的代价。于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坚定我们的立场,来反抗这些压迫。
不过,坚定立场就等于要洗净队伍吗?
五
因为我们要洗净队伍,我们似乎不再相信任何真诚的异议。任何反对我们立场的意见,不过是掩饰他们自己的不正义立场。于是,每当我们遇到异议和不同意的立场,我们很自然地不是寻找不同立场的可能理由,而是开始去诊断,对方为什么竟然持有问题的立场。
既然对方的立场没有可能的理由,那诊断结果自然是对方的动机、内在心理、性格等等出了问题。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在我们看来合理的解释。我们不仅对我们的敌人进行这种诊断,我们对盟友也开始这样的诊断。
那些所谓的盟友,对我们的立场提出质疑,持有不纯粹的立场,就是她们动机不纯;她们是为了抢夺话语权;她们为了最大化自己的中产既得利益;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精英地位……
前些天广为流传的微信文章《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就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批判了。作者仔细描述自己如何成为女性主义者,如何在生活中的一地鸡毛柴米油盐下反思作为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如何面对生活和主义之间的张力。
很快,文章中面对张力的真诚没有被夸赞;文章里面对主义的理解的可能错误也没有被讨论。随着文章热度而来的,倒是一系列对作者动机和心态的批判。作者被诊断为自寻烦恼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烦恼不过来自“想将自我利益在体制中最大化”。作者的动机是为了“用女权主义合法化她们的超额欲望”。作者“将女权主义用作进步精英身份的标志”。
动机不好的作者,竟然还尝试为女权主义“开课”,还要对女权主义有没有用提出质疑,这些都是作者在利用女权主义以及女权主义者身份。
六
批判动机是很有效的扼杀。一旦动机有问题,任何的讨论都变得不必要了。一旦动机被攻击,你是没办法反驳的。因为对方并不是针对你的文章或者行动,它针对动机:只要你的动机不纯,你做什么都是错的。同时一旦被攻击也没法挽回,因为被攻击的内容就是动机,既然我的动机不纯,那我怎么反驳呢?我没办法证明我的动机很好,每当我去试图去证明我的动机很好,都会被动机所限制。任何的辩护者都会不小心中枪。因为被攻击者受到的是动机跟人格的攻击,于是辩护者就变成了为不可辩护的人辩护,同时辩护者的动机也会受到质疑。
七
但这也截断交流的手段。因为不相信有合理的异见,所以我们不仅不会考虑对方有说成功,而且拒绝就内容进行辨析和批判性理解。我们期待盟友与我们在信念和理解上高度一致,我们期待队伍里面的一致。结果,当我们发现盟友中的不同意见会感到惊讶,并且很快将她贴上敌人的标签。
于是,我们对待可能的盟友的严苛性,堪比对待敌人的严苛。任何不够“彻底”的反思和抵抗,都不是真正的反思和抵抗。Holly之于流行的女权主义是如此,该文章作者之于坚定的女权主义也是如此。我们将自己包围在互相加强自己观念的圈子里面,不断加固我们与她们的壁垒,使得敌人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大。这些自诩的女权主义者都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些自诩的女权主义都不是真正的主义。
最后还是,我的主义才是主义,你的主义什么都不是。
八
可是,敌人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需要更大的合力。对主义的理解的分歧当然重要,而且不能小看。我们自然很难要求自己爱自己的敌人就像爱自己的朋友一样。但这不等于我们就需要时刻准备着想自己的盟友开刀,挑出越多的敌人越坚定。
我们都欠盟友一份理解,即使是批判性理解。女权主义者尊重多元,更需要这种包容差异的能力。在真诚的异见中,我们才能发现自己可能进步的地方。或许在支持跨性别女性的行动中,我们未能很好的解释我们的概念。或许在反对异性恋霸权的抵抗中,我们未能提供更好的选择和方案。这些都是在接受我们在追求正义中可以做得更好的尝试。
九
Talisse在书中为我们提供的方案,大概如此。这些包容,“并不是旨在解答哪一方是正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对方在哪里觉得我们的立场不够说服力,不够清楚,或者不够充分。在跳出‘谁最正确?’的提问,转向‘为什么她们不同意我们?’的过程中,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观念变得更好。”
十
Louisa May Alcott: Help one another is part of the religion of sisterho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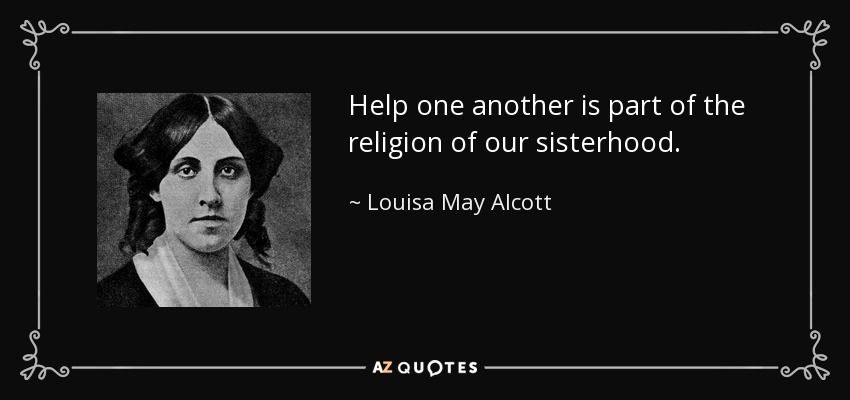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