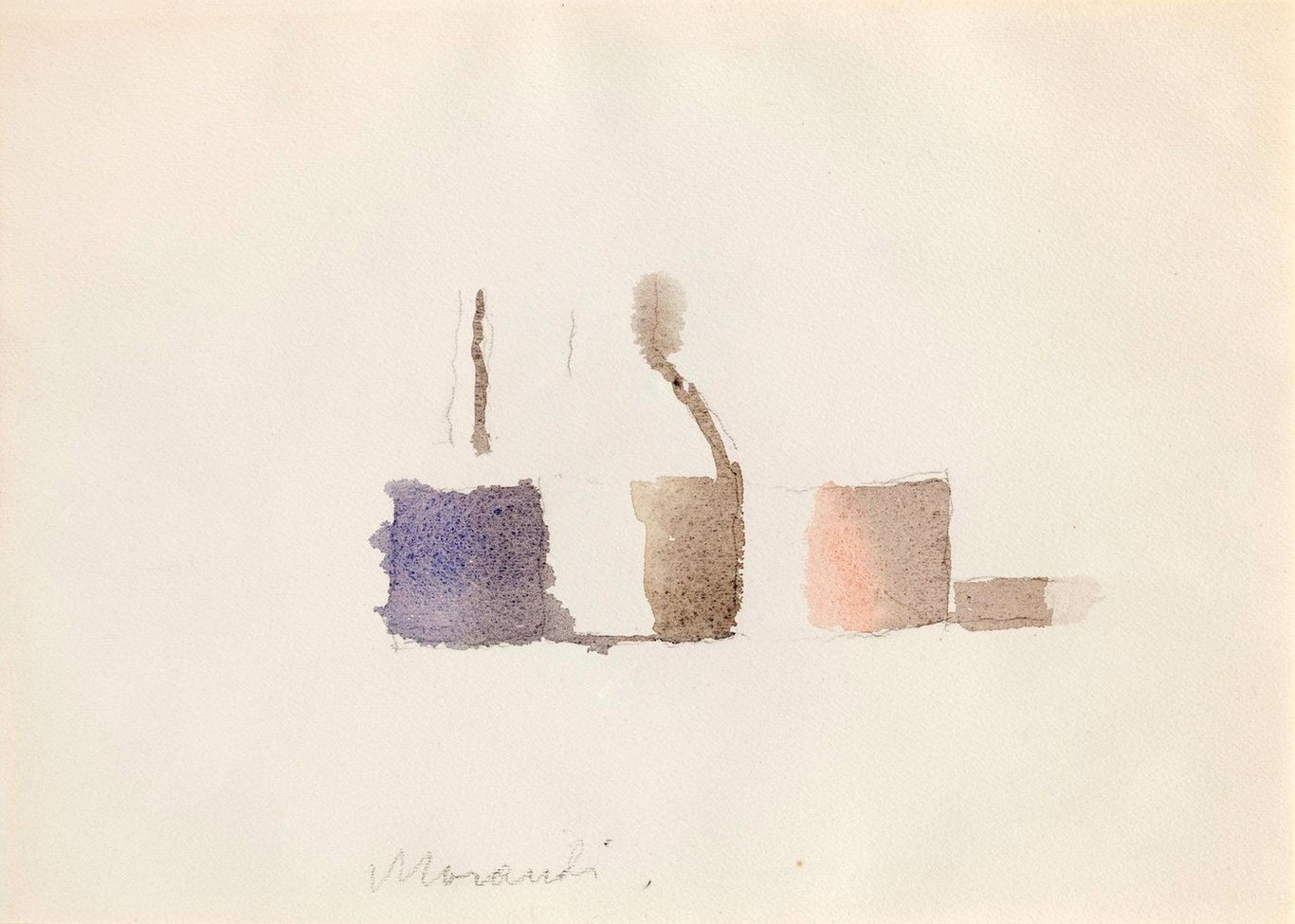蓝色大门
IPFS
田老师前几天说要从意大利寄明信片给我。我今天读到《人物》一篇关于电影《蓝色大门》的文章,这部电影的气质让我毫无预兆地想起他。虽然他的明信片还没有寄过来,也许他忘了这件事情,永远也不会寄过来,但是我现在就想给他写一封信。
出国之后,我认识了很多人,绝大部分都远远不及我印象里的你,王小姐,和舒大大。我怀疑是我当时过于幸运才认识了你们,而这世上绝大部分人确实只是了了。
前几天我和舒大大在短信里聊了聊,他并没有去巴黎高师念书,据他讲现在他在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巴黎大学念书。他并不满足于这所学校,也不和学校里大部分混日子的中国留学生交朋友,倒是和两个在巴黎高师读博的人交往甚密。他跟我讲卢森堡待五年就可以拿永居,这是他人生的保底计划,他和我一样对回国没有兴趣。他正在考虑转去学经济学或者数学,在法国学文科是很难留下的,就跟这世上大部分第一世界国家一样。
我并没有去找过王小姐,她也没有来找过我。我并不知道她的生活如何,只是依稀记得在朋友圈看到她从法语文学系转到了哲学系。上高中时我们走得那么近,并不是因为我们足够相像,足够欣赏对方,而只是我们和其他人都太不像,太无法容忍。我们那么各色,那么清高,却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甚至依赖朋友。也许王小姐并不同意我这番说辞,但是除此之外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毕业后我们几乎从未联系过对方。
我在里德遇到了一个让我想到您的人,她和您一样对于胡闹和奇怪有着很好也很无法解释的包容。她和您一样温和且善良,有时忧郁,有时羞赧,面对未来迷茫犹疑。但她身上多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韧和生命力。她总觉得自己平凡,甚至是糟糕,但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您的父亲曾说您把一手好牌给打烂了,但是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如果您现在有时仍然觉得自己不会打人生这幅牌,那你可以换去打打人生的网球或者什么别的,我想你也不觉得这世界是一张狭隘又利欲熏心的牌桌。
自从我们都上了大学之后,每次别人问我有良知、有知识、有意思的人在哪里念书时,我都回答:在一些你大概率没听过名字的,毫无成为精英的希望的,毕业之后赚不到钱的大学。反正不在斯坦福。
我想起那年冬天我们去学校旁边的日料店吃饭,吃完之后我们在平安大街上边走边闹,王小姐试图拉你的手。当时我很开心也很自由。那段时间我总觉得我的人生非常压抑,道元班的烂摊子让我感到无力,我期待着飞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迫不及待要逃离我早已厌倦的教条、制度、文化。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觉得高二高三那两年非常恣意。无人管教的,浪费时间的,没有意义的,沉溺幻想的,大有希望的十七岁和十八岁。你们三个送我去公交车站,107路到站了,我径直走上车,并没有道别,也没有回头。尽管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留恋。也许我当时在想:我是那个Tough Lady,那个各色小姐,我不应该让你们发现我会想念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也许并没有那么想念我。
《蓝色大门》的导演说,这部电影被很多人说甜,可他却觉得孤独根本是苦。我的17岁大概是这样,也让我想起那时的你。你说你很想哭,也很想死,你也讲很多关于X的心思和踌躇。我搞砸每段恋爱,又快速随机爱上别人,我恨几个人,最恨自己。但是当我们坐在夏日的蓝天下,当风吹在杨树叶上让它们闪闪发亮,我们好像又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像是《蓝色大门》里讲的:夏天都快过完了,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总是会留下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关于高中时代最后的夏天,我们都留下过什么呢?我只记得诗歌,单车,滑板,背阴的教室里堆的二手哲学和文学书——全都是王小姐的书。可是如今看起来,我并没有成为这样的大人,很可能未来也不会。那个从小就不讨喜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更不讨喜的女性,我尖锐、愤怒、高傲,却也时常觉得无比沮丧。
我害怕看到我们变成大人的样子。我害怕我们最后的夏天其实没有为我们如今的生活留下什么。
我的生活在下坠,它终于又沉重了起来,我不否认我想念那轻飘飘的日子。
祝您一切都好,不知道意大利的星星亮不亮。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