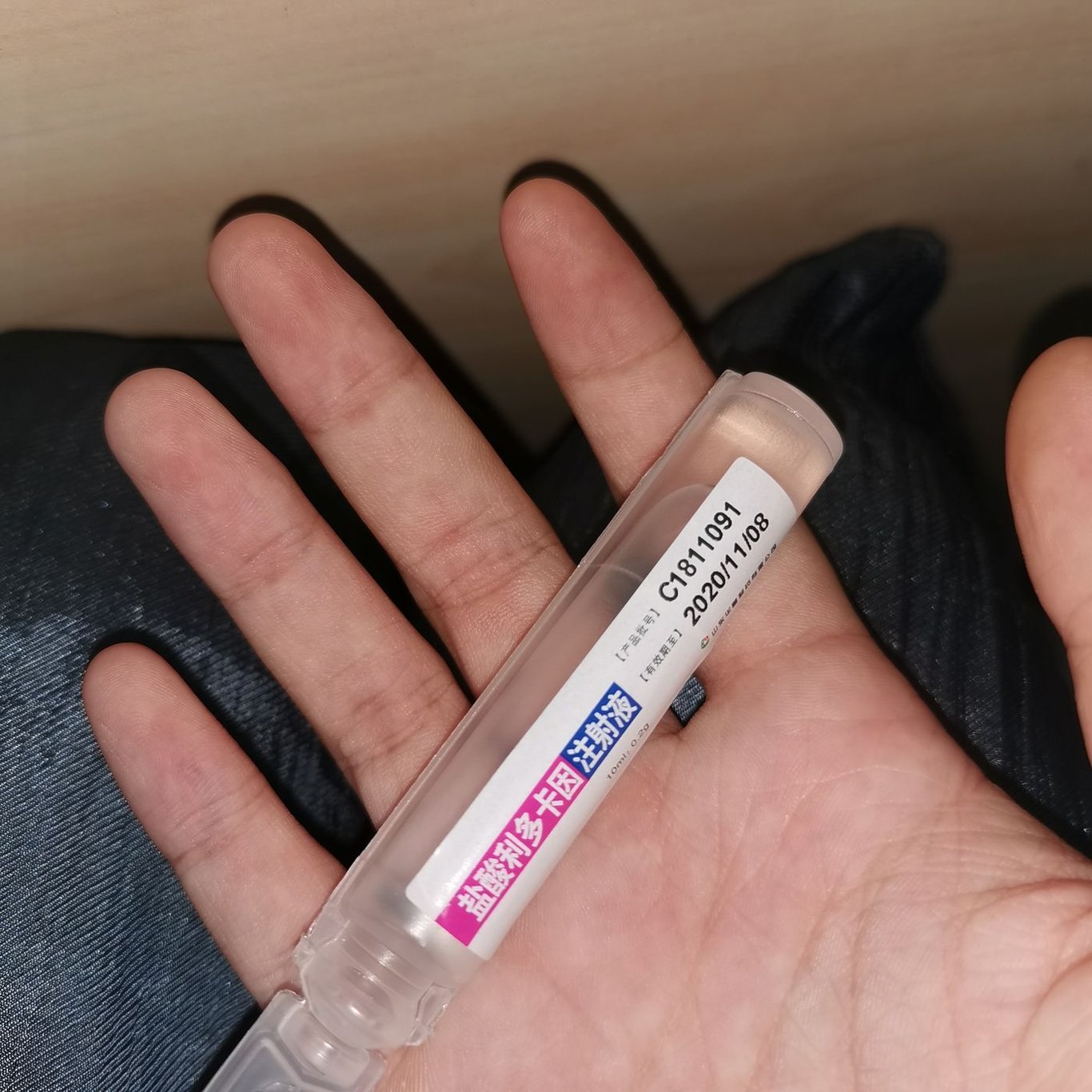性教育的落地与“虚假需要”批驳
原文写于2019年末。时值专业课结束,作为对话何春蕤文章——“需要性教育”是不是个虚假需要——的一篇非典型“作业”。此为存档。
参考文章见下:http://sex.ncu.edu.tw/jo_article/2019/08/%E3%80%8C%E9%9C%80%E8%A6%81%E6%80%A7%E6%95%99%E8%82%B2%E3%80%8D%E6%98%AF%E4%B8%8D%E6%98%AF%E5%80%8B%E8%99%9B%E5%81%87%E9%9C%80%E8%A6%81%EF%BC%9F/
在与一篇文章进行对话时,应先厘清其论述逻辑:文章自两部分论述铺开,前半部分分析了“虚假需要”的理论基础,包含自佛洛依德到马尔库塞的“虚假需要”理论,是为作者论述的前提。后半部分以福柯“知识-权力”框架批驳《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施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政治化立场,以对全球化下知识传播路径进行警惕性提示。笔者也将从以上两个部分对话与回应,并尝试解读在本土中国,全面性教育纲要实施的意涵。
谁来承担“不隔离”的后果?
纵观全文,在作者的论述中,随处可见非常积极的、乐观的对于性教育本土环境的先验假设,这其中包含了强大的青少年主体性和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制度背景。如若现实真实如此,批判《纲要》的西方中心主义固然无可厚非,然事实上,不论学者所处的台湾是怎样情境,大陆本土显然长期在性教育上是缺乏的。
回溯西方性教育发展的历史,自六十年代起由美国性咨询与性教育委员会(SIECUS)发起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以来,“全面型”取代传统禁欲型性教育成为主流趋势。但是在如今中国大陆,“禁欲型”性教育的影子仍旧挥之不去:浙江大学曾于2008年开设“守贞课”,要求学生们做一个签署“守贞契约”的决定,以承诺婚前不发生性行为;2014年,在河北与温州等地出现“女德班”,以教导女性青年对男性的绝对遵从,甚至至今仍能够在网络上看到相关报道;2017年,在北师大出版社的小学性教育课本《珍爱生命》问世之后,由于其中提到关于同性恋、不婚以及多元家庭等信息而遭到诸多家长的反对以至于该课本最终被回收停用;甚至在新近关于北大女学生的自杀案件中,涉事男性对于受害者的贞操观一度被认为是导致其自杀的重要原因……尽管主流媒体以及舆论对于“禁欲”持以批判态度,但是这些都是顽固且某种程度上已经“得逞”的禁欲主义思想,且在不同的群体与个体上展现着。
也因此,笔者很难在这样本土的环境中说出“我们不需要性教育”。但作者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就解构了性教育的“需求”。首先,她将“性无知”的代价消解了:性教育之需求说大多建立在“性无知”之上,但是,在当前资讯发达的年代,“性无知的现象逐渐减少,性教育的需求当然也应该随之变化”。无知仅仅体现年轻男女不小心怀孕这样的事,但更多无法忽略的悲剧其实正在发生:熟人性侵、未成年母亲......在2018年,央视新闻曾报道过短视频平台“快手”上存在大量以未成年生子相关的视频内容,其中不乏与淫秽色情相关者。“14岁生子”“00后宝妈”曾一度成为该平台的吸睛热点,这些主播大多来自农村或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低下,更别说获取性教育知识的可能性了。
所以笔者认为作者的论述大多是悬空的假设和抽象逻辑,实际缺乏佐证:首先我们无法预设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每一个体,尤其是性教育中重要客体的儿童或青少年,接受到的关于“性"的知识和信息都是足量和正确的。即便如此,传播渠道多样和不具权威的网络信息又如何挑战传统的教育秩序,使得儿童与青少年们在此过程中能够自动、自发地破除”性无知"呢?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有充分的主体性,也因而思考性教育需求的变化是为必须,但是对于“无知”状况的突破与否却是需要批判看待的。
而后,关于佛洛依德与马库塞的“虚假需要”理论,作者进行了翔实的分析。说明性教育之“需要”实则是由于成人将儿童隔绝在与“性”相关的议题之中导致的,我们要解决的并不是“需要”,而是“隔离”。在大陆法律中,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在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上德界定都是并不完全的,将儿童隔离于性活动之外显然是一种无须解释的前提——成人世界是“少儿不宜”的,但如何来承担儿童或青少年纳入性话语和活动中的后果,作者在文中却没有说明。
诚然在大陆文化中,我们的社会环境对“性”实在讳莫如深,国家也自上而下的对“性”失语:被删节的电影片段、被禁止谈论的相关话题等等……裸露镜头不会在公众平台出现似乎与何之论述的“隔离”相同,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并不能天然地推演出将成人世界向未成年开放一切“性”相关的话语就能够破除一切隔离带来的桎梏的结论。我们可以就此假设,也正如作者文章中论述的那般,但显然没有一个社会胆敢以此尝试或实践——谁来承担“不隔离”所带来的后果,谁又能保证不隔离的背后不会生产出更多的“未成年妈妈”们呢?
全面性教育:性别平等的迂回之策
在联合国的《纲要》中,“全面”涵盖了“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的教学(16页),并强调基于人权与社会性别平等等原则……在此看来,全面性教育之全面实则非常包罗万象——这也是作者进行批判的另一个理由。
首先,笔者非常赞同何春蕤在文章中强调的全球化视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现象已经形成人权、性别、性健康、同性恋等议题新一波的论述与知识形构,结合了启蒙的姿态或文明开化的任务,如今思考性教育问题自然很难逃脱这些新生的全球脉络”。文章中对于全面性教育的批判也多基于全球化下西方推行该政策的政治意涵,但是将中国置于国际舞台之中讨论与性相关议题时,很容易发现我们对外同样是“失语”的。
在联合国的人权议题中,SOGIE(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关注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个人自由,很显然该议题关注对性少数者的权益保护。但历届会议中,中国政府从未对外表示过支持反对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的立场。2011、2014、2016年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都陆续通过投票通过了有关性少数人群人权问题的保护性决议[1],无一例外地,中国从未投过赞成票。尽管决议实际推行无阻,但对国内性少数平权的来说无疑是一记打击。2019年10月24日[2],就相关议题中国代表同样进行发言,中方代表承认“中国反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但仍旧未表明支持的立场。很显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对于性别议题的态度都是一直坚定的消极着。
再从宏观的全球视角来看:在2019年年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平等差距》报告中,中国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06位。这甚至是自2008年起11年间的连续性跌落。在健康、教育、经济和政治四个方面的评估上,中国两性平等的状况“每况愈下”。更直观地来说,距离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还有一百年的时间,这显然是很多人难以等待到的。
大陆本土的性别生态实际并不良好,甚至基于地方不同的历史文化特色,各有各的“顽固”之处,在国际上的表现也并不乐观。而何春蕤认为,《纲要》文件大杂烩式地将过多内容增加到性教育之中,“这些内容至少有一半以上属于性别平等和人权议题,其实应该是在校园生活里随时传递的观念……本来在知识上就处于低度开发状态的性被喧宾夺主地彻底稀释排挤,最终真正得到全面开展的,反而只是饱含政治意味、充满政治正确教条的人权平等论述”。
显然作者再一次将本土的性别平等环境看得太过积极——我们的校园生态真的足够让青少年们意识到性别平等议题吗?
在何的假设之中,青少年们面对性别不平等时存在一种天然地能量而无需社会化的赋权。作者2012演讲的文章[3]中曾提到,在校园中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性语言“已经不能再简单的、顺畅的生产预期的羞辱效应,这些青少年已经学会把这种语言的意义多元折射,并赋予新的意义也因此给力自己了”,而一旦出现一套完整的制度,一个“极端保护主义的性教育立法”,保护那些被歧视语言中伤的青少年时,“这样的执法也消灭了同性恋青少年对自己的给力”——这也因而成为作者反对台湾性别平等教育法案推行的理由之一。诚然,我们需要带有对制度和治理术的反思与警惕,但实际情况下,谁来关注那些真正被中伤的青年人呢?在这样的反思之中,我们显然很难进行真正的利弊比较。
并非所有受歧视者都能够如“酷儿拥抱酷儿(queer)”一般将歧视性语言作为自我赋权的工具,我们很难不去怀疑那些不被中伤的青年人不是拥有强大自我的“幸存者”。
真正的自我赋权应如方刚学者所说一般,在尝试颠覆教育主客体的过程中缓进达到。在他看来,“性教育”一词暗含成年家长、教师、学者向未成年人进行教化的自上而下逻辑和浓厚的“师本位”,但性教育中应以受教育者为主体——这实际颠覆了教育与被教育的隔离,而在进行着“性信息传输”[4]的平等实践。该学者进一步将这样的性教育称为“自我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5],让青少年们自我增能,提升对性的了解和自我探索能力——这实际与《纲要》中所提倡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19页)不谋而合。《纲要》鼓励将性教育的学习当作学习者个人成长的一种形式,并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反思。
因此笔者认为,在性别平等,以及针对性少数人群的平等、反歧视尚未真正落实的大陆本土,我们很难探索到行之有效的力量来让“大环境”更加可观。与其谈论《纲要》推行中的“别有用心”,何不因势利导,将其作为借由联合国介入国内人权问题,推动性别平等的一种“迂回之策”。
最后:去除文化虚无主义的自我赋权式性教育
学者何春蕤作为性权派的斗士,对于性教育相关的体制、纲要以及一切宏大的自上而下的话术都相当警惕,她认为“教育本就是一个参与者共同反思、共同学习的过程,我们更活在一个变化迅速因此没人敢号称掌握一切知识的时代里”(2012)[6]。也因此,《纲要》中知识传播的“绝对性”和“单向性”被作者大加批判。而笔者认为,预设东方作为西方传播知识的被动客体,实则带有强烈的文化虚无之嫌。
事实上,面对性的议题,我们的“文化”常常非常顽强,以至于成为禁欲思想如今仍旧存活的可能。同样地,在SOGIE审议上中国代表对外发言针对同性婚姻发言的“托辞”时,将“传统文化”作为不推行同性婚姻的挡箭牌也诸如此观。
尽管不可否认全面性教育中西方主体视角,然而在批判思考的同时也要关注实际真正“落地”的可能。在全面性教育尚未完全推行的大陆本土,探索更多话语和行为来破除对“性”的谈论的禁忌显然是为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不能预设一种“全盘接受”的前提来批判。本土文化的根基和传统已然给政策落地提供了足够多的“阻碍”,更何况完全照搬呢?所以作者文中提到西方式性教育的从天而降,显然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诚然,没有人可以旗帜鲜明地声称自己握有对知识的绝对权力,而也没有人能够忽略快速变化的讯息时代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无法否认当今时代给予了人们更多获取知识掌握性信息的可能性,也无法忽略信息流通带来的危机。
在我们的国界之内,仍旧存在着许多被贴上“愚昧”、“落后”和“封建”标签的两性现象:买卖婚姻、高价彩礼、童婚现象......这背后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渊源并非“一日之寒”,而确是要一步步去破除的。性之于落后地区无疑为洪水猛兽不可谈论,而在这种“性”话语的不均等之上,一项相对普世的政策,很难不具备“先明性”——们确实需要性教育,更重要的是需要基于性别平等的性教育。
最后,让我们回到何春蕤文章开头的疑问——我们要的大抵不是全球一致、单一价值的文明现代,但很显然“全球一致”和“单一价值”并非是由全面性教育的铺开所导致的。在警惕西方话语权力的同时,先对本土的环境做出改变是为首要矛盾。我们可以假设受教育主体探索性与身体的强大能动性,但将此基于消极推行制度的必然显然太过困难。对于政策“离地”的担忧,对于在课堂上实际谈论性之可能性的担忧,很显然应当被放置于“落地”之后。真实的“落地”并非根植本土不作改变的重复话语、观念和行为,而是基于受教育者,并能够行之有效为其赋权的教育体系的落实。
[1] 详见公众号“同语”:中国代表在UN | 反对歧视,有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
[2] 详见公众号“同语”:中国代表在UN | 联大首次发言,交流良好实践
[3] 详见网站:何春蕤论述资料库-反教育的青少年性教育(演讲) 2012年4月25日
[4] 方刚.“性信息传输”与性教育内容多元化构想[J].新学术,2008(01):121-123.
[5] 方刚.赋权型性教育:一种高校性教育的新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3(10):92-95.
[6] 详见网站:何春蕤论述资料库-反教育的青少年性教育(演講) 201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