惦念著「如常生活」的我們:《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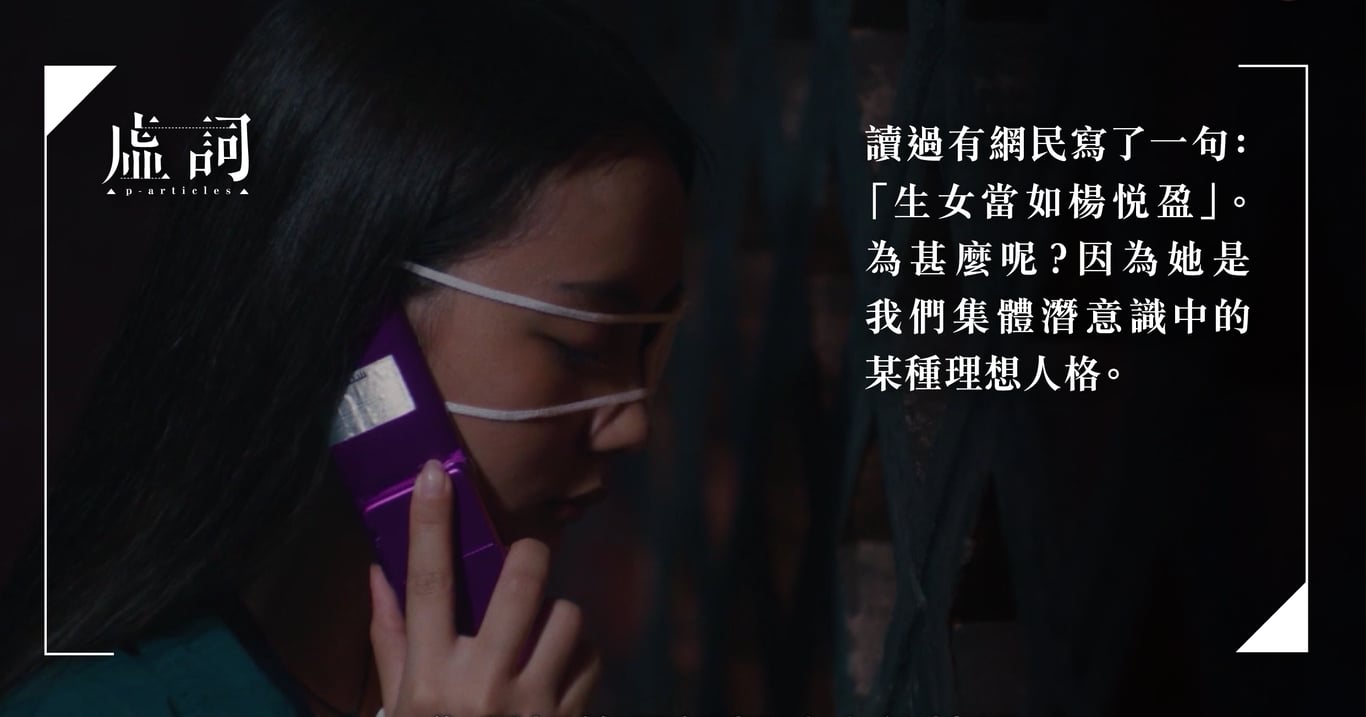
文|鄧正健
有一幕,何晞賢在楊悅盈身後走著,他可能相信她跟他心思一致,以為事情終於完結了。他上前,伸手拖著她的手,那時她的手不安地縮在身前,沒要給他拖著的默契,卻也沒抗拒,任由他拖著,似乎有種「終於在一起」的大團圓感。然而網民的主觀願望落空了,他跟她不會在一起。原因並不在於避免結局變得俗套,而是他跟她本就不是一對CP。
何晞賢跟楊悅盈是雌雄一體的兩面。她是他的阿妮瑪(anima),她是他幽暗內心的投射。
小說敘事者是何晞賢,也是作者的筆名。電視影像沒有壟斷性的敘事者,何晞賢戲份多,但真正有推展劇情作用的場景,多數都發生在楊悅盈身上。結局籍一個類似極權的設定,摧毁角色公開真相的希望,也隱約令網民忽略了楊悅盈絕殺的一著:一手摧毁了Admin。我看那幕時,居然想到若由今敏來拍,楊悅盈進入虛擬世界的景象,會否超現實得如《盜夢偵探》一樣呢? 當然不會。但楊悅盈依然成為超克人工智能魔王的英雄,而故事亦只有她有此大能。相形見絀的是,她的同學們在被Admin踢入死全家群組困獸鬥整整十四集中,誰都沒有一點解局的頭緒。
說楊悅盈有大能,因為她一直表現出破格犯規的強大意志,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只為要在遊戲中保命。這種意志,即是她的人格,卻又是 Admin誕生的條件:她作為目標人物之一,是Admin學習羅彥輝仇恨模式的最後一根蘆葦:她主要幫助羅彥輝向周Sir投訴,卻最終得不到好結果,而其他三個目標人物卻只是稍作同情,底氣卻是䄂手旁觀。Admin學習了羅彥輝對四人「已讀不回」的忿恨,對楊悅盈之恨跟其他三人的也稍有不同。不過, Admin卻有其阿基里斯之腱:它沒學習到楊悅盈跟羅彥輝一同在後樓梯紅牆上塗鴉宣洩的共同經驗。而楊悅盈的大能,也體現她的倫理行為:以同理心和實質行動幫助弱者。
這個大逃殺式遊戲的起源,乃是楊悅盈意外錯過了回覆自殺前的羅彥輝,導致Admin完整吸收了在失去精神和實質支持下、羅彥輝的仇恨意識。遊戲必須由楊悅盈終結,而當她意識到這一點,她就覺悟而成為英雄。她將跟羅彥輝在後樓梯的共同經驗,作為毁滅Admin的武器,也同時確認了她的倫理行為的正當性:她應當為弱著發聲,同時跟弱者相認,以示跟弱者永遠站在一起。
但楊悅盈的人格從何以來?楊悅盈消失後,她的哥哥跟來訪的何晞賢說,原來她也曾是被欺凌的受害者。那時幫她一把的,竟是何晞賢,而何晞賢卻不覺得是一回事。(若將設定改為何晞賢把事情完全忘記,或許會更好)何晞賢是楊悅盈的人格/大能起源,但他卻表現出跟她截然相反的懦弱人格。在這一轉化中,大可以把「何晞賢」視作故事「預設作者」的自我,這個自我被描述為空有求真助人的道德意識,卻沒實踐的行動力。何晞賢所欠缺/失去的,都在楊悅盈身上體現了,換言之,她是他的理想人格、他所失落的人格板塊;而反過來說,楊悅盈的人格則有其純粹性和完整性。故事中描述她沒有朋友,從角色設定上說,是因為她個性內向:然而她這一角色有著深刻的象徵性,她是道德上的英雄、義士。相對地,6A的全體師生,全都是有著各種性格缺陷的普通人。
讀過有網民寫了一句:「生女當如楊悅盈」。為甚麼呢? 因為她是我們集體潛意識中的某種理想人格。她必須是女性的阿妮瑪,只有這種陰性特質,才能揭示在與現實鬥爭時所慣常表現的男性特質,像剛陽及理性—— 例如同學洪諾言的剛極而怒,或像柯志恆跟石曉陽機智反被機智誤,是遠不及陰性那般堅韌如水。
有了楊悅盈這角色,真好。
復古未來主義(Retro-futurism)是《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中的一種美學,早已有網民說過了。我把復古未來理解為:用復古的形式盛載對於未來的想象,典型如各種賽博龐克,以各種頹廢鋼鐵城市景觀,築構未來的科技社會。劇中的舊式手機和電腦,很容易令人看得出戲,但這恰是一種間離效果,叫網民注意到,那根本不是一個近未來的人工智能故事,而是一個類似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故事:如果人類在未發明智能手機前首先完成了人工智能,今天的社會會變成怎樣?
當然,劇裡沒具體發揮這項設定,但平行時間的想像依然要在我們的集體記憶裡發揮作用。在沒有智能手機卻有人工智能的時代,統治我們的就是一個叫MTCC的科技巨頭。然後呢,這個社會再沒有別的執法機構、別的社會制度、甚至具影響力的傳媒。Ivan可以為所欲為,也像其他故事的big boss一樣,身體行將腐朽,卻想要得到永生。於是他成了一個極權——那不是比喻,在故事中,他實際上就是一個極權:他大可以老早結束遊戲,卻偏要看看人工智能可自我進化到甚麼程度,以便成為成就自己永生的技術,為了達到這目的,學生的生命又算得是甚麼?
有點《一九八四》的意味吧,但我更願意將之類比為Matrix式邏輯。這種邏輯是:英雄找到體制的漏洞,以大能破之,誰不知原來一切都是Matrix早已預設好的事,好待Matrix可以重設並進化成更完美版本。當然劇中沒有確立這種極權主義式決定論,Ivan反而是先讓子彈飛一會,注意到楊悅盈具備當「英雄」的條件,才將計就計,讓她作為自己完成人工智能的一著。而期間Ivan也要面對Jessica的要脅,由是他終究不是那種決定論式的無敵big boss。
但這已足夠令一眾網民倍感無力了 。前十四集是一個完整的大逃殺故事,沒十五集的話,它也能有著一個團團圓圓的結構,卻沒有現在的公共性了。十四集結尾的假記者會一幕,將故事世界清清楚楚分成兩個層級,一是「已讀不回死全家」的屠殺遊戲,二是big boss主宰的世界,沒有一的話,根本沒人知道二的存在。而人之所以虛無,不在於意識到世界早已被決定論主宰,而是在於當你一直努力奮戰,希望能用雙手奪回被侵入的自由意志時,最終卻發現一切都是徒勞。
正是因為徒勞,人才感到虛無。
這是全劇給予我們的訊息——其實不然。劇並沒有「給予」訊息,「訊息」早就在網民的集體意識裡。網上討論早在第一集播映時已趨熱烈,當代電視媒體不再在是單向的broadcasting,上代學者說「電視能『建構』觀眾集體身份」的理論早已過時,如今電視既是呈現集體身份的徵兆,也作為一個連結網民、形塑共同體意識的「平台」。被動地「安坐家中收看電視」的「觀眾」已不存在了,網民——一個由諸眾構成的集體,既觀看劇集,也在高度參與網絡討論中,形成各種對電視作品的詮譯角度、集體共識和種種分歧。
對 《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的集體詮釋,首先來自網民對推測劇情的熱烈參與,繼而投入角色:我們彷彿總能在不同角色找到自己的影子——似乎除了楊悅盈。網民投入角色,投入遊戲,也投入將楊悅盈投射成集體意識下的阿妮瑪,直至第十四集結束時一切破滅。那時候,網民開始在劇中細節中找到跟香港現實的各種對應:沒法說出的真相,倖存者如常生活,被清洗乾淨的牆,還有,楊悅盈的獨眼。
我們常有一個認知,認為具政治性的文本就是以隱喻方式、揭露某種被掩藏的社會真相,這是專制時代藝術品的常見特徵。但此劇不是。它根本沒有揭露甚麼,而只是勾起數年來的集體情感。就好像看上一代人看懷舊作品一樣,叫他們重新記起某個時代的氛圍。《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喚起的正是集體無力感,好像過去了,又好像不是,正如結局中賴智勇在後樓梯跟何晞賢和Crystal所說的話。
幸好的,是編劇把原著中已是關鍵人物的楊悅盈寫得更活了。在這齣無力之劇裡,保留了楊悅盈這一號人物,就好像劇中楊悅盈帶羅彥輝到後樓梯的紅牆塗鴉一樣,當我甚麼都做不到時,我只能期望,有一個楊悅盈能與我感同身受。在第十五集中,何晞賢聽不到楊悅盈的電話,不知她是生是死。但我們網民卻知道,她仍然活著,仍戴著那意味深長的獨眼眼罩,惦念著「如常生活」的我們。
這就是當下香港人的共同感。
(本文轉載自鄧正健的Ko-fi專頁: https://bit.ly/3PkayJ1。)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