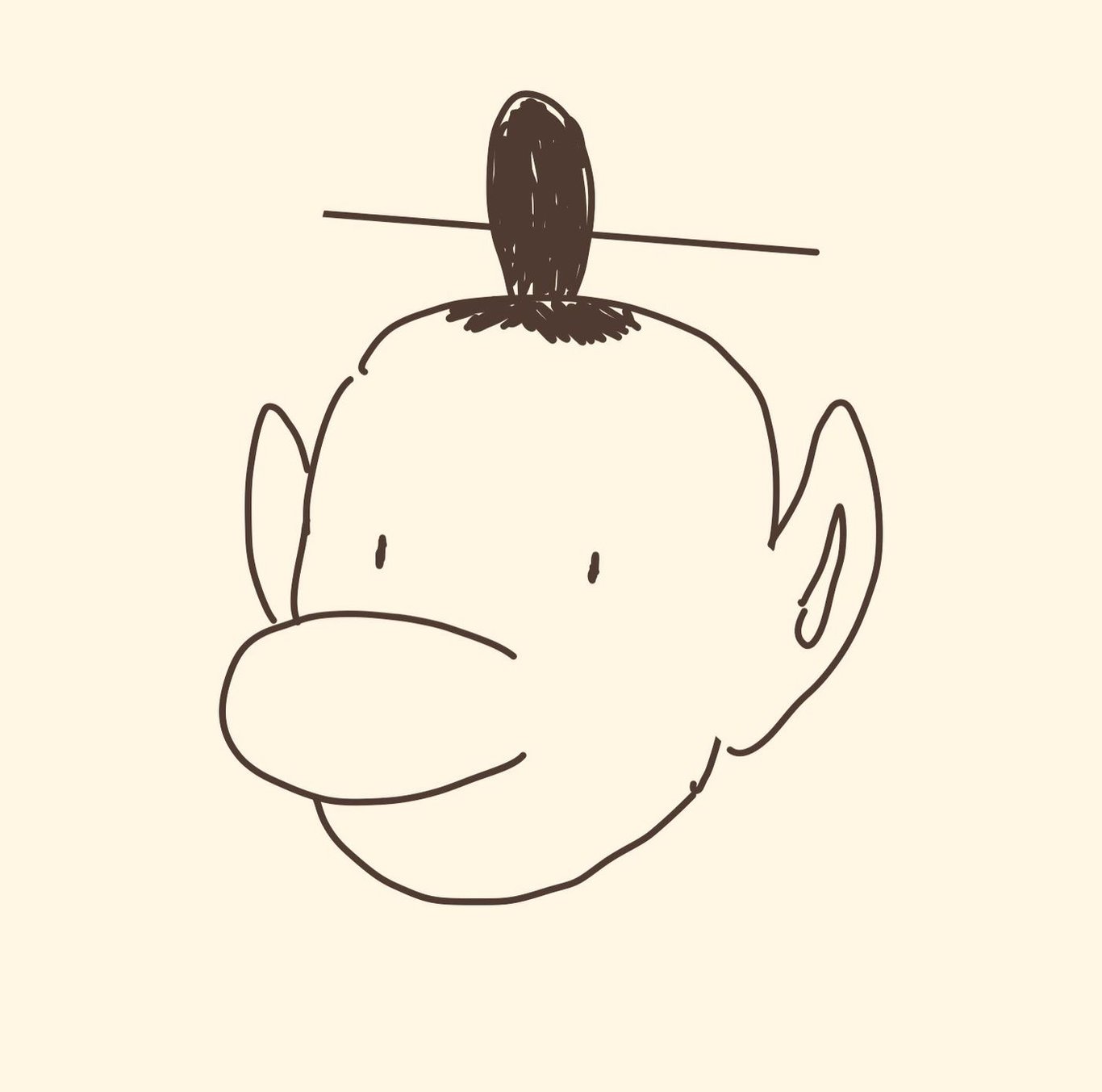Farewell
爺爺走了。
與想像中的不同,我沒有哭。
還跟姐姐說笑:「爸爸前幾天又在耍憂鬱,喪著臉說自己會比爺爺早走。登愣,預測失敗!」
我又笑道:「啊,爺爺的願望落空了,沒來得及看到台灣獨立。」
姐姐吐槽:「我們也不一定看得到。」
我有六位祖父母,四位在我出生前過世,兩位則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我跟他們幾乎沒有相處過。爺爺是鄰居,也不是多親近,但已是最熟悉的老人家。
爺爺每次見到我都笑著說「XX啊,呷飽沒」。這是台灣人打招呼的方式,但我認識的人裡,只有他會這麼說。我自己亦不曾這麼說。
他是教師,受日本教育,維持著一種台日混合的生活。以前偶爾去串門子,他們家溫馨雅緻,沙發與桌面鋪著純白的蕾絲布,園子裡的小池塘養著鯉魚,用著固定品牌的日本味噌。
小時候,常常聽他說二二八,我依稀記得的情節是,政府到學校抓人,他看到軍人就趕緊逃,最後在公車裡躲了過去。他非常厭惡國民政府,二二八是原因之一,另一個是「四萬換一塊」。載一車去,兜裡幾塊錢回來,家族富裕不再。
爸爸跟他交情好,政治理念相近大概是主因。在我們巷子裡他倆是少數派,話能說到一塊,以前常常一起喝茶聊天。是互相「取暖」吧,我想。
大學時回家,和往常一樣在巷子內碰見,叫他「爺爺」,沒反應,中聽了。之後,跟他說話都得丹田出力。以前他說話中氣十足,許久未見,再見時神情渙散,肉眼可見的枯萎了。我想著,老人竟然還能更老。
連署罷韓時,知道爺爺奶奶肯定也想連署,於是拿連署書給他們寫。連署書必須連署人親自謄寫,且不能有修正痕跡。姓名、地址、身分證字號,也沒幾個字,但他們太老了,不斷的寫錯字,不斷的重填,浪費好幾張紙,在一旁監督的我和姐姐差點沒瘋掉。
前些日子,爺爺住院,說是小腦萎縮。爸媽說起爺爺奶奶的事。他們有一兒一女。女兒據說被丈夫虐待,自殺身亡,留有一子,而這唯一的孫子不與外祖父母來往。兒子有結婚,無子嗣,不太照顧父母,酗酒,不久前離世。唉,人老了,卻沒有子女照顧,爸爸感慨道。他不禁想起我阿祖(阿嬤的母親),走了快一年,也是停在九十幾歲,兒孫滿堂,連玄孫也有幾個。
這幾天,爸媽討論著爺爺出院後要怎麼生活,奶奶一人肯定是照顧不來的,然而,還沒有得出結論,爺爺就走了,於是話鋒轉向喪禮。喪禮在殯儀館,似乎是由爺爺的學生幫忙操辦。公奠的情況⋯⋯沒有子女,而妻子不送喪,就只剩一位媳婦,但媳婦跟公婆的鄰人都不認識。爸爸說:「那⋯⋯還要去嗎?」我心想,是要去送他一程,見最後一面,那裡家屬有誰我不在乎。最後,爸媽決定由媽媽一個人代表出席。他們說,盡量別去殯儀館。
在我看來,他是同輩中書讀得多的人,是知識份子,然而,這晚景⋯⋯。連訃聞也沒有,體面之人卻未能體面的離開。
也許十年、二十年後,他的容貌會如同許許多多的容貌一般,在我的記憶中逐漸模糊,偶然想起其存在,只剩體形輪廓,帶著一張空白的臉。沒有爺爺的照片,遂以文字代替,試為己保留一些記憶。
願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