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尖沙咀的海景房 我跟示威者們睡了一夜
一、
「Arrested n released」剛剛我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朋友K終於回復我。
11月18日晚上到19日凌晨,我跟他的聊天記錄就一直是,「Are you safe now?」、「Are you still safe now?」、「If you are safe, please let us know!!」
然後他的上線時間就一直停留在凌晨32分,WhatsApp上的消息由雙√變成單√,直到剛剛(11月20日晚)。
18日是警察包围香港理工大學第二天,那天有海報說晚8點鐘尖沙咀集合從兩條道路出發, 營救理工大學學生。
那晚,我去柯士甸找之前的採訪對象露宿者劉阿婆,想跟她聊聊最近近況,比如睡在街頭會不會被頻繁的催淚彈而影響到。隔壁床位的婆婆卻告訴我一星期前劉阿婆被人帶去了深圳養老院,她也很掛住她。
沒見到劉阿婆,我在旁边公園坐了會,之後,就跟著人群一起走到了佐敦,又走到尖沙咀附近。
行人皆佩戴口罩,磚頭鋪落遍地。
一個香港青年從書包拿一疊口罩,送給一家問路的外國遊客,站在旁邊的我也被贈予一個。
那晚後半夜,我還從美國朋友R那兒拿到一個眼罩,拿到它的經歷卻太為曲折。
二、
我用Instagram發消息給R,問她在哪兒。
不出所料,她果然在尖沙咀。她出現在這場示威運動的每個現場。
她發我位置,問我是否一個人。地圖上顯示我們很近。
但當我就要到達她說的Baleno時,馬路上已形成人鏈,再過一會兒,我在尖東廣場,聞到催淚彈,跟著人群跑開。
來來回回,我們在人群和催淚彈下移動自己的位置,明明只有幾分鐘距離,却很难見到。
我走進一個商場躲催淚彈,商場好像叫「快樂中心」,R說她在旁邊的橋上,問我所在的商場是否是Toyo mall。
好像不是叫這個。我穿著白色外套,待著白色口罩,用手機對著玻璃窗上「快樂中心」的中英文商場名拍照,發給她。
還沒怎么反應,幾個黑衣人就衝進來。
站在我面前,他們說,把剛剛那張照片刪掉。
對自己粵語不夠自信,我用英語解釋,我只是想讓我朋友知道我的位置。
身旁一個男生用英語問我:「where are you from??」
我坦誠答,mainland。
其實那刻我也沒有很害怕,雖然好像聽到身後有個聲音輕輕(輕蔑?)地「sh」了一下。
他們中間一個女生過來拍我,示意她的同伴們別太粗魯。另一個我對面的男生大聲用英語跟我說,我們不是要攻擊你!只是你不要拍照!
他們要求打開我的手機相冊(不過也都沒有從我手上拿手機),我給他們看相冊,又打開Ins證明我是直接發給朋友的。
其中一個人說「she sent it directly」, 一群人鬆了口氣,跑出商場。
幾秒後,我也走出去。在噴泉邊,我終於看到穿著綠色熒光服的R。
她抱我,把眼罩給我,然後又迅速跑開了。
她發讯息说,抱歉,我不得不去跟團隊會合。
我感謝她給我的眼罩,又多加了句,感謝她這些日子,作為前線急救人員,為香港做的一切。
R回復,是香港為她做了很多。
接著她問我,我記得你是內地人,對嗎?
於是這個晚上,同樣的答案我說了兩次:「Yes, I came from the mainland.」
R回:「ohhhhh then I think you can do more for hk than me.」
「那你能為香港做的事,比我能做的更多。」
三、
我沒再立即回復R。邊在手機上記下剛剛的事,邊準備走回家。沒地鐵沒巴士沒車打,但走五十多分鐘可到。
按照地圖走幾分鐘后,我發現我要去的那個方向没什麼人,再往前走幾步,有手電筒的光射過來,我才看清前面是一排警察,旁邊幾個穿熒光衣的人員過來叫我別從那邊,換另一邊走。
另一邊就都是示威者,我跟著一群人走了幾步,又跟著人群跑起來。
反正就是圍繞著尖沙咀中心,不斷不斷打轉。
快十一點,身體疲乏,除了在一個群裡匯報自己境況,我也不知道還可以跟誰聊天,我一直以來的發小好友,我的爸爸媽媽,他們誰都會叫我注意安全。他們誰可以理解?
我問R是否還在尖沙咀。
在Club 222附近我見到她,也見到之前她跟我說的男朋友,是一個做前線救護人員的香港人。
想到我最初跟R認識時,她以美國交換生的身份在學校教英語,但經常並沒人來上她的入門英語課,我和朋友索性拉著R一起去聊天吃飯。第一頓飯,她就說起她很喜歡Asian Face的男生,還分享了喜歡的中韓明星。那天離開食堂時R還給我們使眼色:剛剛走過那個男生好像很帥!
R之前有個做廚師的香港男朋友,六四那天他們一起去維園,當時R問我在不在可以坐在一起,不過最後那天彼此找了半天也沒見著。再過一陣子,R說,她分手了,因為前男友好像不是很在意她。她也很快喜歡上一個前線急救人員,也熱切參與到這場運動之中。
R的現男友打了個電話,帶我去一棟大廈,那裡有另外兩個女生和一個坐在凳子上睡著的男生。R的男友跟其中一個女生說了我的情況,讓我跟他們一起待著。接著他跟R繼續返回外面。
我跟面前站著的兩個好看女生簡單聊了幾句,他們都沒有穿黑衣,但睡著的男生想必是之前在前線示威受了傷,腳上綁著繃帶。
不一會兒,其中一人接了電話,她們有另外的朋友帶了房卡過來,好像是訂了酒店現在可以入住,我跟著她們一起往外走。
走在去酒店的路上,有姑娘叫我把那個眼罩收好,到房間裡,我聽她們聊天,他們想訂酒店菜單上的揚州炒飯,叫Kate的女生問我有沒有衛生棉,打電話問酒店能否送「M巾」。
沒有炒飯,侍應生送進來薯條和三明治,她們招呼我吃,說如果不介意可以喝這同一杯橙汁。
真是個神奇的夜晚啊我想。
一個姑娘坐在窗台邊,另一個女生指著她跟我說,她被警察用警棍打過。窗台姑娘豪爽笑道:「好彩沒被抓Ball。」
「啊?抓Ball是什麼意思?」我問。
她們一起笑!我想到她剛剛比劃的動作,反應過來!大叫「啊,我知道了!」
在香港這次運動中,不斷有傳警察對女性示威者進行「性騷擾」或「性暴力」,如立場新聞報道的8月4日天水圍少女被防暴警察扯脫裙褲,如10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與學生舉行對話時,中大女學生吳傲雪稱自己在被捕拘留期間遭警察性暴力對待。

我們並沒聊太多,我第一個躺在床上蓋著被子準備睡。桌子上有沒吃完的三明治,地上的包裝著R给的眼罩和餅乾。
看到群裡新消息,J說:「香港這城市的情義太驚人。」
四、
在房間抱著手機入睡前,隱約聽到的話有:
「妹妹睡了。」(說我呢)
「哎,別自首啦,共產黨信不過的。」(說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
還有枕邊的手機連續傳來的微信消息振動音。
是入睡前,我忍不住給北京的山阿說,好神奇啊,我現在在跟幾個香港人在賓館,今天晚上近距離旁觀了運動。
剛開始他問我怕嗎,說「別衝動,越在群體中越要冷靜處之。」
後來說到「裹挾」、說到「洪流」、說到「永遠沒有正義之師」、說到「智慧生物的悲哀」還有「黑甲蟲入侵」。
我困得無法思考,但醒來也覺得,我的悟性跟他不是一個層級。
那天,我還問了一個香港朋友「你為什麼不會想跟其他香港同學一樣出來參與到這場運動中啊?」
後來他說:「我不喜歡沒有主體性的群眾運動。」
他們的話怎麼都和打謎一樣?寫下這些的時候,我越寫越困惑,不知道除了那些感受的細節,自己的邏輯應該是什麼。
其實我也問自己為啥來尖沙咀,也許因為性格里的冒險因子、想體驗更多,經歷更多,見證和記錄更多。或許因為自己也在深深迷茫著⋯在群體中感受他們,也感受我。
他們,是內地媒體裡所謂的「暴徒」們,許多只是簡單善良的年輕人,我現在就跟其中五六個住在一起。
而我,若我的吃瓜行為也算是參與這場群眾運動,我其實也無法跟他們站在完全一樣的位置。
但,我在作為吃瓜群眾的參與中,也真正為「Stand with Hong Kong」感動過。
五、
特別記得某種感動,是在看My Little Airport演唱會的時候。
他們的歌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聲後唱起來,燈光是在幾百只比著“五”字的手掌間,暗下來。
唱《西西弗斯之歌》的時候,全場都有些激動。
「西西弗斯知道自己改變唔到命運
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繼續推石頭」
還有很多跟這場運動緊密相連的歌詞。
「全世界都有暴動的青年但香港幾時先出現?」
青年們自嘲、覺得這場革命會輸、但是又覺得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 昆德拉書裡的話,林阿P在歌裡也用了它。
但青年們似乎就是浪漫、純粹、少計較、不功利主義。
我們可以不選擇群體。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那些義憤填膺的有強烈民族主義的愛國人士,為什麼就不能用他們的那種「群體感」以己度人,感受下香港人齊聲大喊口號的熱切與赤誠。
他們對這座城市有著自己的想象,想要守護它。
六、
在早上10點多的海景房我醒了,我看到山阿,一個以前覺得回微信消息也是巨大內耗的抑鬱症患者,破天荒給我回了很多很多條微信。
他說:「不是內地人無知不同情覺得香港人優越,而是一種本能所有人的本能對戰火的恐懼對事實的抗拒,或者根本沒有辦法去了解事實,每一個時間都是被割裂的被片面的拉出來成不了事實的主題,只有拉到歷史洪流中站在外面才能看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每個人都是工具」、「每個人按照事實安排好的位置站好」、「身在洪流中身不由己」、「只有歷史才是旁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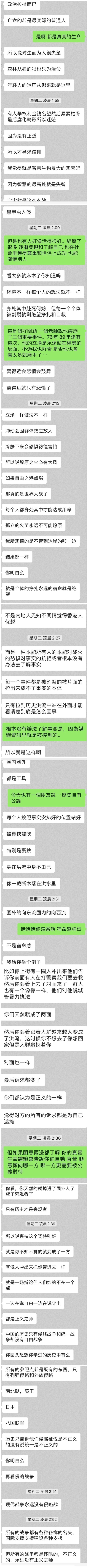
我不知如何回復。
看向旁邊,他們都還睡著,我們這個床上三個女生,另外一張床上兩個男生,沙發上還躺著剪男孩兒頭的一個姑娘。
他們也醒來後,幫一個男生撕下腳上的繃帶。
我在旁邊問Kate(我只在第二天早上要走時問了她的姓名):「边个Book嘅呢间房,畀幾多钱。」
「她有錢」、「唔噻」。
「冇搞呢些嘢」兩個人先後說。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