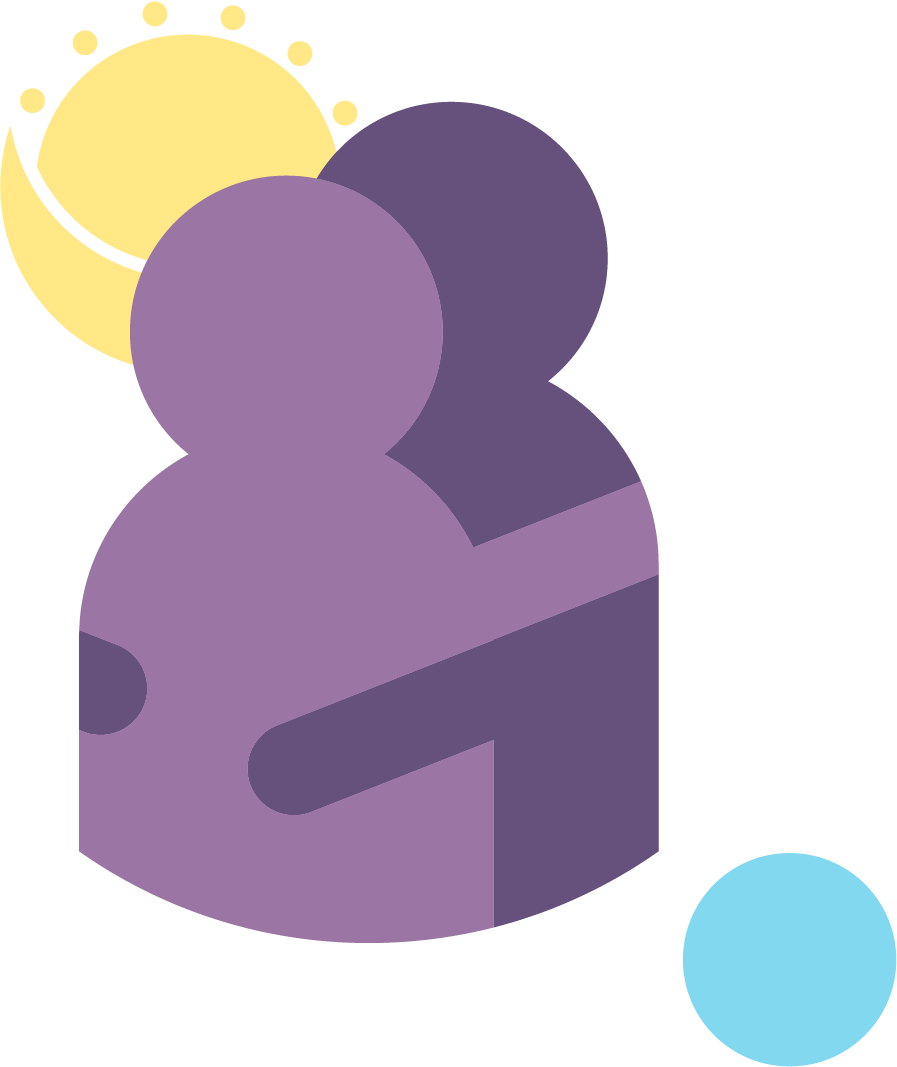圆知圆谓 |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 步履蹒跚
编者荐语 今天是3.8国际女性权益日,然而在今天仍有无数女性挣扎于无法获得她们合理的权益。虽然缠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女性依旧在被各种各样的“裹脚布”束缚着,禁锢着,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百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今天圆知圆谓专栏将为大家带来对缠足美学来龙去脉的讲述,以此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性别文化枷锁是如何作用于我们身上,从而找到面对和抵抗它的出路。
前段时间在学习一些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值此“三·八”之际,为大家分享汉学家高彦颐的女性史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这并不是一本篇幅庞大的书,语言风格也并非艰涩难懂,但从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逡巡不前,始终不敢肯定自己完全读完了它。书中丰富的细节不仅没有勾勒出一个连续完整的缠足史叙事,反而不遗余力地冲击着既成的反缠足话语,而在这种解构之中我虽早有预料却仍不免感到某种困惑。这与其说是疑问,不如说是焦虑,涌出的思考甚至要淹没了对文本本身的理解。且让我束缚住失道的思绪,依据本书的思想,以我个人的理解与思考来讨论一下缠足问题。

作为一贯以来的常识,我能够不假思索地直接判断缠足是陋习,必须反对缠足。显然,所谓“不加思索”一定是受到了文化的建构,从教育环境到社会氛围,从官方意识形态到主流审美潮流。《缠足》一书认为,这种建构是从清末开始,通过反缠足的社会运动确立的。这些运动实际上多遵循两条路径,其一是带有某种基督教色彩的“光复自然身体”话语,在这些运动中,“天足”“放脚”等反缠足概念产生;其二是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革除陋习”话语,这些运动将“不能劳动”的缠足女性视为国家和民族的寄生虫,视其为中国衰败的根源之一,以一种政治立场和治理手段的态度贯彻反缠足的实施。在民国时代,反缠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在三十年内消除了缠足这一持续将近千年之久的习俗。
在这些现代的反缠足运动中,对身体的揭露成为了一种基本手段,人们公开展示缠足女性的足部照片,甚至让缠足女性当众除去裹脚布,展示畸形的足部。这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而这种震撼有赖于前现代社会身体的私密性与不可见性——长期以来女性身体都被置于严格的遮蔽之中,公众对于缠足的直观印象是着鞋袜的“金莲”而非暴露的脚。官僚系统甚至以行政手段实施这样的揭露,这其中以阎锡山为典型代表。阎锡山在他控制的山西地区严格推行放足,为此依照年龄制定了放脚的条例要求,设置了专门的查脚员,并且以罚款惩戒有未按规定放足的妇女的家庭。这些揭露举措未必能够立即撼动缠足的习俗,但它们成功使缠足与羞辱、污秽乃至落后、野蛮等宏大概念相联系,大大削减了缠足的“文化光环”。

现如今我们的反缠足立场,正是继承自二十世纪的反缠足运动,我们的话语也因而来自于它。如今对缠足最主要的批判,在于缠足是对女性的束缚,是从肉体上禁锢女性行为能力的阴谋。这样的话语正是早期反缠足运动中“缠足令妇女不事生产”话语的延续。而《缠足》一书通过对缠足生活史的考古指出:一方面,缠足妇女的主体是底层女性,她们是深入参与社会劳动的;另一方面,作为当时主流、上层意见的男性话语并非一味煽动和追随小尺寸的崇拜,而是存在一种功能美学的视角,认为脚也应当满足行走之“用”而非成为无用之“累”。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缠足作为一种女性对自身的形态调整行为是为文人所不理解乃至谴责的。这种反驳并非是为前现代社会男性开脱罪责,而是说批判本身过想当然耳,低估了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与此情况相同的是另一种批判,即缠足破坏自然身体,是一种畸形的审美。这类话语可以追溯到早期反缠足运动的“天足”话语。这种视角涉及到“美”的标准与“自然”的概念在各个文化及时代中的复杂变化,而“畸形审美”作为外部批判在此就会变得无力:它只对有着“非畸形认同”的我们有说服力,可对于身在缠足文化中的人来说,缠足是日常之事。由于众多女性将大量智力与精力投入于对脚的塑形和鞋袜款式样式的设计制作之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令她们会赋予缠足越来越大的价值和意义。而从缠足生活史的考据来看,缠足的“审美”性很有可能是后起的,也就是说先有了这样的做法,此后逐渐被赋予更多价值,最终成为一种美的标准。正是因为如今不再有缠足群体,“畸形审美”类型的批判才会成立。
《缠足》一书认为,如果没有女性的主动参与,缠足的习俗是难以维系的。另一位学者柏桦也指出,在前现代中国社会,缠足很可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母女知识传承纽带。在普遍缠足的时代,缠足是一件会带来正反馈的事,因为她所付出的努力会直接反映于身体形状的改变上,并且能够得到控制。在为数不多留存下来的缠足女性自述文本中,不少人都提及缠足给女性带来的成就感与价值感。然而,在反缠足运动和一脉相承的主流批判中,缠足女性本身都是失声的。在反缠足运动宣传所构建的图景中,放足是一个“重生”式的短期甚至瞬间过程,放足带来的身体解放足以给人抵抗一切障碍的力量。但是对于真正缠足的女性来说,放足是一条永无尽头的道路,因为脚并不会自然恢复原本的状态,而已经适应了缠足受力的脚在放足过程中又必须再次经历痛苦。不仅如此,反缠足运动还将缠足女性视为一种“症状”,用羞辱的方式迫使她们放弃缠足。运动聚焦于女性的身体,却并不真正关心女性本身,他们在女性的身体上投射了国家、民族、文明的话语,寄托了先进、开化乃至救世的厚望,但丝毫不在意她们的感受,也鲜少考虑到放足以后女性的护理和生活方式。反缠足不仅与缠足一样给女性带来负担,还以侵入性的姿态架空女性的自主意识。在此我们能够辨认出中国早期现代的生命政治轨迹。

但必须说明的是,这并非是在为缠足翻案。本书作者悬置了价值判断,从始至终都以一种彻底怀疑的视角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剖析缠足、反缠足、反反缠足各方的视角、方法和问题,而以上的思考只是意在破除对于反缠足话语不言自明的成立性的迷信。作者所真正想要关注到的是失声的女性,她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留下文本,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缺乏发声的渠道和方法,没有人能听到她们的声音;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缠足时代,一切都是日常中“顺理成章”的部分,正如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缠足时代一样,缠足的妇女也难以想象顺理成章不缠足的日常生活,因而她们并没有话要说。正是到了缠足消亡的时代,一切才变得有表达和记录的需要;然而女性的声音依然不会有人听到,因为没有人关心她们要说什么。而这里正是我的焦虑所在。我所焦虑的并非反缠足话语的内在问题,也不是缠足究竟如何建构、形成的生活史事实,而是我个人的价值判断及其合理性。
作者到结尾也没有表露她对于缠足的价值判断,而是总结道缠足对于前现代中国的女性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早已失去了缠足的土壤,偶然出现的缠足行为又显然裹挟着大量的复古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然而于我个人而言,我依然直觉性地认为应当反对缠足,即对历史上缠足的习俗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为什么要反对?反对的又究竟是什么?抛开反缠足运动的殖民主义、进步主义话语我们该如何表述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焦虑,是因为面对这个问题我感受到一种不可置身事外的迫切感。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且也与如今的社会紧密相关联。
那么为什么要反对呢?反对某个事物总需有所本,而外部批判总是无力的。我所能想到的批判角度只有:为什么只有女性需要缠足?显然,缠足是一种身份标志,而在民族、阶层的标志之外,缠足更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性别标志。在一些明清世情小说中,男扮女装或为人男宠者也会缠足,而女性女扮男装则会用棉花填鞋增大脚型。依托于服装、语言和礼仪动作的性别标志并不少见,然而缠足是直接作用于女性身体的。它意图改变身体的形状,并且在标志性别身份之外还生产美学符号。当然女性也在这种美学符号生产中受益,但还原到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爱欲经济学原则来看,这种美学符号主要还是为男性(此指凝视的主体)所剥削、消费,用以维持其性别阶层认同。可以将这个机制表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女性生产出的美学符号大量地为处在“父”位置的男性所剥削,更大一部分则为处在“夫”位置上的男性所消费,留给自己的只有极少一部分。需注意,这里所谓的“父”“夫”都是结构位置而不是具体的个人。
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结构位置具有某种“实体”的意义,相似的结构位置其意义与功能也趋于相同,而结构位置上具体的内容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我看来,缠足习俗虽然消亡了,但其结构位置并没有被取消。同样是对于女性身体形态的审美导向塑造,化妆、穿刺首饰等姑且不论,小到高跟鞋、减肥,大至整容、玻尿酸、肉毒杆菌,似乎这种塑造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扩展到了身体各处。与缠足一样,女性在整容、塑形中也会获得身体掌控感、成就感和自身愉悦感,但更多的符号价值是为男性所剥削和消费了。从强制要求着高跟鞋的领导,到要求妻子做保养的丈夫,男性普遍擅长攫取周围近关系的女性的美学符号以巩固自身身份认同。
那么缠足与现代各种塑形有何不同呢?我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缠足更“痛”。我认为这样的区别不仅仅是技术操作和审美体系上的差别,它们让我联想至前现代与现代的刑罚。前现代社会中,威权是通过夺取人生命的刑罚来体现的;而现代的社会则通过保障人的生命、禁止人随意死去来彰显权力。缠足与塑形正是前现代与现代性生命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都在驯化人的身体,攫取人们的价值。
因此,我个人的思考是,反对缠足是意在反对暴力性的生命政治的侵入,反对针对女性的身体规训和符号剥削,很大程度它与反对剥削女性家庭劳动和生育劳动的价值是一体的。而如果我们反对缠足,那也应该反对如今对于女性身材的规训,反对强制性的美学符号生产,诸如“化妆是基本礼节”等话语。但是也常有人说“化妆是为了取悦自己”,我虽有心反驳,但似乎又很难提起。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方面的问题呢。
本期作者

作者 | 卯月末 审核 | 圆人舍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