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米斯的迴廊——《墮下的對證》中的視覺之外

文|雙雙
跟H同學說起《墮下的對證》(Anatomie d'une chute, 2023),她說好像全世界只有她能跟女主角Sandra(Sandra Hüller飾)共情——本來她以為只是身邊的人剛好都討厭她,後來看到M+戲院的簡介也這樣寫到,「姍迪許娜演繹一個絕不討好的角色,仍可讓觀眾全情投入,功架也令人歎為觀止。」(註1)
其實我也不覺得女主角討厭。
喜歡一個人可以毫無保留或理由,討厭一個人總得有點原因,或多或少。「對證」的過程中揭發了夫妻兩人的齟齬齷齪,而唯獨對Sandra不利的是,她活著且受審。拳擊台上守勢的一方,姿勢多半沒那麼耐看;她有影響、施影響於兒子Daniel(Milo Machado-Graner飾)的可能、能力——她也似乎真的有這樣做。這些種種漸漸疊加了她的不討好以至討厭形象。
所有疊加都有底座,所有高樓都有地基。在我看來,後來她之所以變得越來越「討厭」,是因為一早就存在一個「討厭」的成核位點(nucleation site)。水,蒸發成雲,是從水氣凝析為水滴,這個過程的發生需要凝結核(condensation nuclei)的在場,之後水滴凝聚結集,才有了雲拋棄的雨。電影的第一幕就是成核位點的所在,在我看來——正如在優先效應(primacy effect)看來,第一印象相對難以動搖。
第一幕是訪談。
——就聊聊天,像我們現在這樣。——你不想繼續回答我的問題嗎?——當然想啦,但我們也可以聊聊天。Zoé(Camille Rutherford飾)特地開車到雪山上來見她,她卻反客為主,主動提出各種問題,似乎根本不打算好好回答問題,只是隨意敷衍。
我倒覺得,她的「敷衍」是可以理解的。
回到訪談最開始的地方,那裡聲先於畫,——抱歉。——沒事。——你想知道甚麼。畫面出現樓梯,——等一下,還沒開始錄⋯⋯樓梯那邊掉下來一顆球,——好了⋯⋯Snoop跑下來撿,——那麼⋯⋯你在書中描寫兒子的意外,讓讀者有點不安,因為我們知道是你的生活,你認為人只能從親身經歷出發寫作嗎?
首先,是「畫面出現樓梯」跟「還沒開始錄」。前者是畫的記錄,後者是聲的記錄。強調了「記錄」這個動作。畫的記錄暗示了有觀眾(也就是我們),聲的記錄暗示了有聽眾——聽眾如無意外是指訪談之後、開始寫論文時的Zoé,後來意外發生了,聽眾就擴大到庭上諸位,以及後來的我們,再聽了一遍。
其次,是「你在書中描寫兒子的意外」。Zoé問出的第一個問題其實並不複雜,也就是現實經驗與虛構寫作的關係。不過,她卻選了最尖銳的句子作為引入——本來她似乎可以層層深入,但她卻採取了長驅直進的路線,希望在一條問題裡勾引出最多的答案。很不巧,Sandra似乎不是那種隨便給她一個題目她能自己講上半天的作者,又或者,她並不打算就這樣的題目自己講上半天,也不太喜歡話談得太死板、控制權太在對方手裡,——就聊聊天,像我們現在這樣。於是她轉移了話題,而Zoé對此像是有些不滿,——你不想繼續回答我的問題嗎?但她也無可奈何,——我跑步,是我的一大愛好,讓我像嗑藥一樣興奮。——那對於藥你知道甚麼?這是下一條問題。——一言難盡啊⋯⋯——你不會把每句都記下吧。——不不不,絕對不會。
在此,Zoé同樣迴避了嗑藥的問題,用「一言難盡啊」兩個字(在原文是兩個字)敷衍過去。
我想,要是她回的是,——我跑步,是我的一大愛好,讓我感覺像在讀普魯斯特(隨便舉個例子);然後Sandra問的是,——那對於普魯斯特你知道甚麼?她的回答可不會只是「一言難盡啊」兩個字,即使這個話題同樣一言難盡。她之所以作出迴避、敷衍,是因為「嗑藥」,也太私人了,也不是甚麼值得寫在履歷上給人看的東西。
私人且尖銳的問題、見微知著與舉一反三的願望、避重就輕的回應、形形式式的記錄、觀眾與聽眾,都是我們在「一年後」的庭上「對證」所再次遇見的事。換言之,第一幕的訪談,其實就是一場審判的預演,雖然,正式審判上Sandra幾乎沒能掌握到任何控制權。
這時,不在場的Samuel(Samuel Theis飾)開始環迴播放那首不知所云的純音樂。毫無疑問,他在用聲音來宣示自己的在場——我們能進一步說,他是在用聲音來宣示自己的立場嗎?那首音樂的厭女(misogyny)成分——可以說是成分嗎還是只是一種聯想?——是要被納入考慮的事情嗎?流行曲本身有好幾重「聲音」——音樂、文字、唱詞,在此,後二者的厭女成分毫無疑問,但現在純音樂獨自出現在這裡,那麼,音樂的在場也同樣宣示著文字、唱詞的立場嗎?這個問題,很取決於Samuel的意圖,但是死無對證,而且就算通靈詢問,他也大可矢口否認。
那麼,如果我們決定相信只是「在場」,他就不討厭;如果我們決定相信也有「立場」,他就是討厭的了。我偏向前者,所以一幕下來,是Samuel要比Sandra更讓我討厭一些——不過,這個問題只是被電影輕輕帶過,——我看不見他,不好判斷他的意圖,Zoé說。檢察官回答——我就是收錢幹這種事的。
在我看來這卻是重要的問題之端倪。
電影裡還出現了另一首曲子。在Daniel再次上庭作證之前,他彈了大概四分之一闕蕭邦(Frédéric Chopin),Prelude, Op. 28, No. 4。一般相信這曲子的題目是 “Quelles larmes au fond du cloître humide?”,潮濕的修道院深處流淌著怎樣的淚水,其中「修道院」對應的 “cloître” 這個字,也有迴廊的意思。
Prelude, Op. 28, No. 4在我聽來,左手彈的是(修道院的)迴廊,在E小調的黯黮淒冷中,我們沿著潮濕的迴廊走向陰翳的所在;右手是幽傷幽幽流淌,淌向死亡與葬送——蕭邦的葬禮上放的曲子,一首是安魂曲(Requiem),另一首就是他自己的這Prelude, Op. 28, No. 4。
上面說是「四分之一闕」的理由,是因為他只彈了一半,並且只彈了右手的部分。迴廊是通往死亡的過道,或者供人來回踱步、仔細思量的場所。Daniel彈的沒有迴廊、只有幽傷。其後,音樂轉入變奏(Variations sur un Prélude),Daniel來到閣樓,打開窗口,探頭看向下方,下方有低一層的陽台、再下是棚屋、然後是一片雪地——這些他全部,其實都看不到,一如案情的真相——它存在,他卻沒看到。而背景音樂中最後那個懸宕的重音,想必表示有甚麼重要的事發生了——他作出了一個決定。
在此之前,是Marge(Jehnny Beth飾)帶著Daniel離開雪嶺,來到草地。——當你要相信一件事,卻面對臨兩種選擇時,你必須作出決定、作出自己的判斷,她對他說。這一段讓我想到《小王子》(Le Petit Prince)那句名言,狐狸說——看東西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Marge的話正好是這句話的變奏:重要的東西不是用心就能看得見,而是要我們用自己的心來決定的。「我」畫了蛇吞大象的圖,大人們都說是帽子,拒絕承認那是蛇吞大象,我想,不(只)是因為た們像看不見彼得潘(Peter Pan)一樣看不見蛇吞大象,而是因為た們的心決定了不要看見蛇吞大象,要看見帽子。
由是,電影論及了有關詮釋(hermeneutics,這個詞來自荷米斯[hermes],信使、旅人之神,同時有接引亡靈前往冥界的職能)的問題。
同樣是法庭電影,《正義迴廊》(2022)的迴廊就是這麼一個「供人來回踱步、仔細思量的場所」,裡面那個念哲學的男的(林善飾)說——重點不是他們有罪無罪,而是我們的決定有沒有經過思考,還是只用主觀感情、個人喜惡來作出決定。真相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機制、制度。這裡的迴廊傍著高大上的「正義」而來,而《墮下的對證》中的迴廊與「淚水」相關。那是Daniel的淚水、也就是他彈出的那四分之一闕蕭邦。
《墮下的對證》是故事,對他來說,不只是故事。
他作出的「詮釋」很明顯有「主觀感情」的成分,但同時也有血有肉,也有「經過思考」。文學詮釋也是一樣的,當我們面對一個「故事」,並且決定要作出「決定」(也就是評論——當我們這樣、而不是那樣論述,當我們選入這個、而不是那個意念時,就是決定的過程),須要把那「故事」本身納入到我們的生命中來,我們才能——借蘇朗欣《觀火》的摘要裡說「火」的意象聯想(註2)——洞若觀火(「觀火」作為比喻)——而不是隔岸觀火(「觀火」作為動作)。董啟章《神》裡的「本土派評論人」忽滑谷,他對刑天倪(也就是「我」)小說的評論之所以(在「我」看來)有問題,是因為(「我」認為)忽滑谷並不能真心相信自己的評論——我這樣認為。他的評論是把小說視作可以擎之於手而外於身的鬥爭工具——「視作」,視覺意象在此意味著一種「凝視」關係。唯將任心而行,置高大上的「理想」於度外,「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莊子.養生主》),「故事」的意義才能自由顯現、透澈洞然。
「重要的東西不是用心就能看得見,而是要我們用自己的心來決定的。」決定的前提是,我們的心裡要有這件事兒,才可以神行神遇。檢察官最後說——這個故事極其主觀,不可能被視為任何形式的證據。在人間,「正義」通過法庭上的「證據」來判定;在人間之上,重要的是真誠。法庭不一定揭示得出真相,正如電影所說,“reality” 根本沒有人在意;後者則是無須、也無從向た人交代,以至於(至少在此)無從定義。與一些法庭電影不同,Daniel作證之後並未接上結案、宣判,因此我們無從得知他所提出的「證據」在整個「對證」中起著甚麼作用。其實,要是這樣的「證據」也能成為證據,那是何其荒謬的事呢——即使Samuel真的說過這段話,話中的Snoop比喻為自己、Snoop的死等同於自己的離世,也(只)是Daniel的詮釋。(更何況,即使他的詮釋與Samuel的想法一致,他也完全可以在還沒來得及自殺之前被謀殺。)
電影應該的確很有探討「現實經驗與虛構寫作的關係」的意圖——第一幕裡Zoé提的問題就是關於這個,而檢察官在庭上念出Sandra的文字、電視節目討論她的小說和案情,也是圍繞相同的問題——不過是在讀者的層面。最後到了Daniel這裡,就變奏成了論述的問題——論述本身就是一場「墮下的對證」。常言道「作者已死」,死後也決非一無所有,有Prelude, Op. 28, No. 4的聲響蕩漾;即使作者的心無從推尋,至少我們能要求自己待作品以「視覺之外」的「神」、「心」,以最大的真誠。
註釋:
M+戲院:「墮下的對證」,https://www.mplus.org.hk/tc/cinema/anatomy-of-a-fall/(2024年1月27日瀏覧)。
蘇朗欣:「短篇小說集《觀火》」,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11NDHU5612006%22.&searchmode=basic(2024年1月27日瀏覧)。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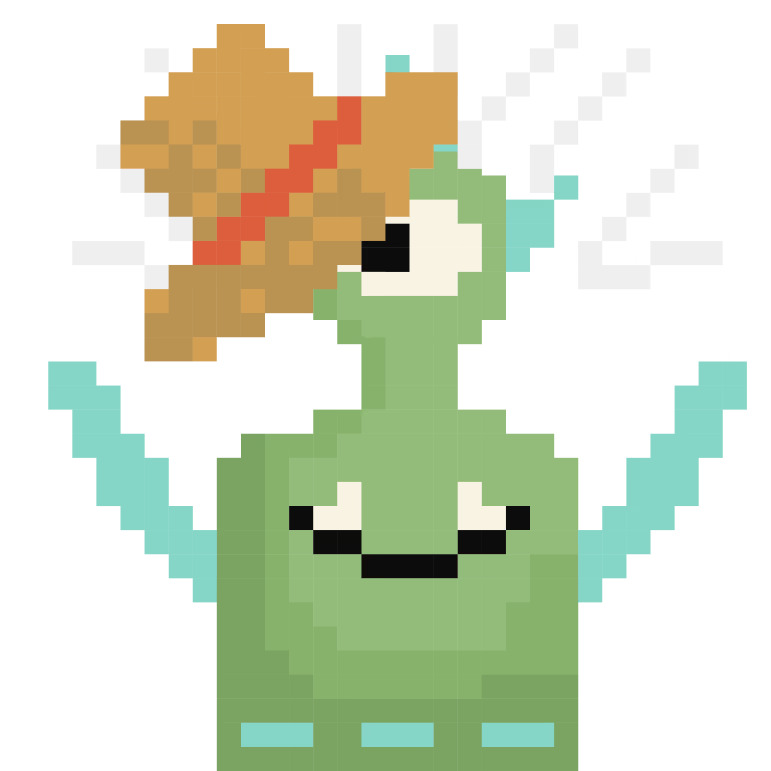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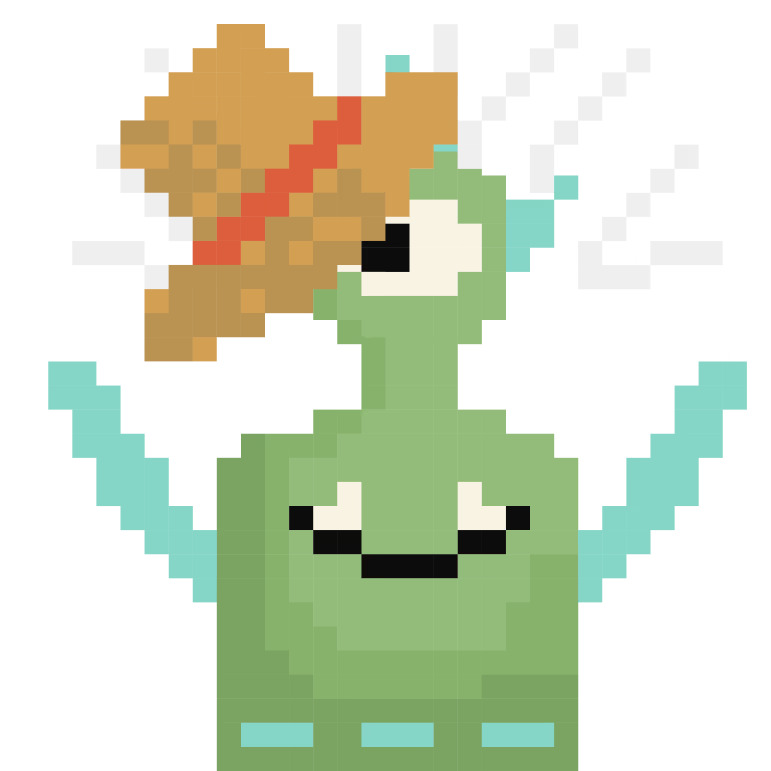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