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的時候是蟲|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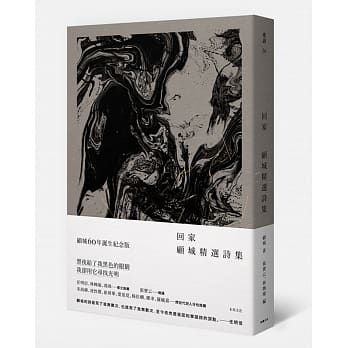
那個聲音在深夜裡哭了好久 太陽升起來 所有雨滴都閃耀一下 變成了溫暖的水汽 我沒有去擦玻璃 我知道天很藍 每棵樹都齜著頭髮 在那嘎嘎地錯著響板 都想成為一隻巨大的捕食性昆蟲

一切多麼遠了 我們曾像早晨的蟬一樣軟弱 翅膀是溼的 葉片是厚厚的,我們年輕 什麼也不知道 不想知道 只知道,夢會飄 會把我們帶進白天 雲會在風中走路 湖水會把光束聚成 閃爍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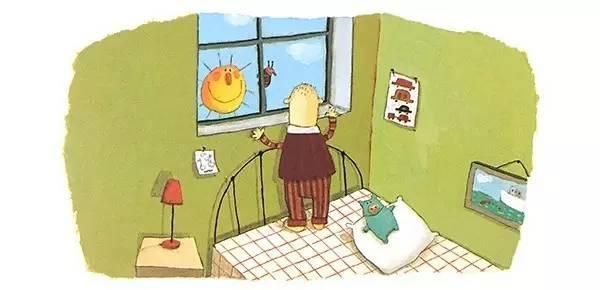
我們看著青青的葉片
我還是不想知道
沒有去擦玻璃
墨綠色的夏天波浪起伏
槳在敲擊
魚在分開光滑的水流
紅游泳衣的笑聲在不斷隱沒
一切多麼遠了
那個夏天還在拖延
那個聲音已經停止
__顧城〈窗外的藍天〉
難過的時候可以讀詩,尤其在這幾天。冥冥之中注定一樣,請我妹幫忙借了詩集。平常是不太讀詩的,可能我一直想要扮演一種人生中的積極腳色,而詩總是壓抑負面。失去學生身分之後,做很多事情都變得有點尷尬,像是去圖書館借書這件事。當學生的時候,去借書好像總是光榮的事:剛開學去借書很合理,因為不想花錢買參考書於是到圖書館借;考前去借書也合理,因為不想浪費學費為了成績衝刺一下;寒暑假去借書,可能準備國考或是研究所,也有可能是想塑造用功的形象。總之身為學生總是在圖書館出沒,就算不會被稱讚,總歸還是合理的。(2017年11月21日)
但我不是。
就算不工作,生活還要過,三餐用水用電,都要錢,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滑手機要月租費,看電視連wifi要電話費,騎車出門買飯要油錢,拿錢包付錢是爸媽給的生活費。脫離學生之後,才發現只要還有呼吸的每一刻,都可以量化成價值。
我的價值在哪裡?我應該做什麼?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嗎?我又想做什麼?
每天揹著這些罪惡感醒來,每天過著規律的生活,甚至比我在大學時候都還要規律:早上八點半醒來,九點半左右開始讀書。十二點休息吃飯,下午一點半左右開始讀書,四點半出門跑步,六點前回家。之後洗澡吃飯做雜事,八點左右開始讀書,十點半整理就寢。過著規律生活之後,會慢慢發現物質慾望降低了,對身上的衣服不太在意,只要舒服就好,沒有內外分別。以前的我,是內外有別的,出門一定要換衣服,還要反覆照照鏡子。畢業之後不論去哪裡,睡覺念書出門買東西,都是同一套,頂多加件外套。吃的用的更不用多說。
在低潮的時候,我喜歡去圖書館。回到書本之間,我才有活著的感覺。看看在這之間我又因為讀了什麼東西認識了誰,誰誰又出了新書,誰的書被放在哪一類,光是這樣就覺得很開心。有點像國小班長點名一樣。然後回頭看看在這時間點來圖書館的人,鄉下圖書館附近多沒有大學,也不是什麼重點發展地段,平日中午趁著買午餐空檔來圖書館的人,多是在童書區晃來晃去的中年婦人,或是看看財報已經退休很久的老伯伯,像我這種年齡層的人出現在這裡,多半是為了搶自修區的,半工半讀或是全職考生。
所以我並不合理。嚴格來說,我比較像是為了消磨時間來圖書館的,有點純粹浪費時間的概念。但借了書好像就有責任:除了要在規定時間內歸還或辦理續借之外,還至少要看過。因此就開始有了事情可做。
在這之間我又想起大學恩師筱琪曾說過的話:人生中沒有什麼不做就不得了的事。
有時候不出門踩踏看世界,會忘記其實自己很渺小。窗外的藍天,與我無關,他不會為我而藍、為誰而灰。這首顧城寫給自己年少的詩,我看作是給我的詩,或許因為我還年輕,或是有本錢裝年輕。我們都像卡夫卡的蟲,積極地敲擊地板,企盼這個世界留給年輕人一些希望,一個成為人的理由。
一切多麼近了 我們還脆弱 什麼也不知道 不想知道 那個夏天已經過去 那個聲音還沒停止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